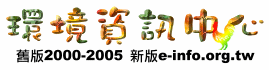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題-國際環境日] 更有尊嚴地生活─營造生態城市 作者:洪伃青 過去二、三十年來,愈來愈多相關領域的專業者將眼光投注在城市生態上。從早期的環保人士、環境工程師,以及從生態動力系統的角度觀照的生態學者。 所謂的生態動力系統包括信息的循環與物質的循環1。前者如侯鳥飛越了非常遠的距離,也順路把一個地方的種子帶至另一地,這個種子代表的一個遺傳基因,種子所包覆與候鳥所傳遞的就是遺傳信息2 ,這個過程就是生態動力系統。 不同生態動力範疇彼此互動 在微觀定義中,都市範圍裡的物質都屬於都市生態的循環體系,譬如雨水滲入土壤成為地下水或地表水,將土壤中的礦物質帶入河川與海洋;而土壤裡面的微生物又促使昆蟲、植物及動物系統整個循環,這都屬於都市生態的範疇。 於是,若要問「都市生態」到底是什麼,簡單說就是─都市生態是都市範圍裡所有不同生態動力範疇的互動結果。 這當中的生態系統牽涉到了許多專業領域,有氣象學、生物學、氣象學之下的水文學、生物學之下的動物學、植物學、微生物學,甚至於毒物學或環境毒物學。空間的規劃設計也成為關係中的一環。舉例來說,如果期望一條主要道路成為真正有效的綠色生態廊道,就不能只是慣常的景觀植物,更重要的是必須要能支撐都市的生態角色。因此安全島或綠廊、綠帶,應是能由下而上包含地被、灌木與喬木系統,營造更多元而有層次的生態環境。 眼前的都市綠地背離了生態 也因此,傳統公園的開發方式並不符合都市生態。良好的都市生態必須使公園連結到生態廊道,使其足跡沿著廊道貫串起來,讓人類活動與自然的、生態的各種元素能有更親近的互動與共存。於是乎每一塊綠地的操作方式,都必須以生態的觀點來思考。通常有植栽、有土壤,降雨可以入滲的綠地,卻往往施作得比馬路還高。都市水文管理的防洪概念裡,若是水能愈快排入水溝、導入海洋,就愈能避免回堵淹水。其實公園是很好的雨水入滲點,然而綠地高位的設計卻背離水往低處流的道理。 都會公園也常因居民的活動需求而承載極大的壓力。一般民眾打太極拳、跳土風舞或行走時,不希望步行在泥濘的草地上,因此就必須有非常多的鋪面產生。然而鋪面鋪面太多,公園就變成人造廣場。舉例來說,台北市的永康公園是與市民意識結合的有趣案例,使得公園的使用更具效益,卻不一定對生態有益。當地居民為小朋友鋪設了大比率面積的遊戲軟墊與廣場,因而排擠了自然棲地。在寸土寸金的都會裡,其實更為重要的是教育市民環境與生態觀念,將這些觀念帶進社區行動之中。環境生態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都市公園中有許多無意義的施作方式應該排除,比如圍牆的建造會危害昆蟲的往來與地下水微量離子的滲透。 都會綠洲已不是生態的倖存地 公園和小學,其實是都會區裡的重要綠洲,因此其中的水文管理、物種棲地與其生態路徑的保育,或更進一步的都市健康元素思維3 ,都應得到重視。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系主任黃志弘教授表示校園內常見的花台是最反生態的教育示範,它不但切割了物種與水的交換,也顛倒了水的流程,還侵犯了自然空間裡擁有的自然內在和邏輯或紋理。例如說溼地、水池與水塘應在低地,但是,噴水池往往施作在學校正門口最高處。這代表綠化與環境美化,僅被視作視覺景觀導向的建設手法。 大安森林公園中的人工水池也是失敗的例子。一來它並非週邊社區排水路徑過程裡的滯洪池,二來在雨天、雨季時,也不能自然吸納水分。一個真正的生態水池系統,它的水池水位跟雨季會互相影響,若是整個城市與綠地的排水系統能夠作更有機、更符合生態的施作,更多樣的可能物種即可能於此存活。 朝生態城市的理想前進 台北距離生態城市的理想,仍非常遙遠。一方面是因為地小人稠的緣故;但另一方面,也顯示台灣人在主觀的環境密度壓力之下,顯然還不能找到好的因應之道。有兩個比較直接的改善方式,第一是保存更多的自然棲地。都會區裡的自然棲地可能是綠帶、安全島、路邊的行道樹或公園的角隅,因此都市中每項建設開始之前,都應思考如何達成自然生態動力系統的保育。 第二是改善自然景觀的狀況。畢竟都會必須維持人類生活與商業活動的機能,因此應在滿足城市機能的空間上予以顧及自然景觀。譬如,行人在城市戶外所倚賴的行動空間:人行道和廣場,卻在都市計劃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裡被壓縮殆盡。若是建築退縮一段空間,甚至擁有一排植栽,都市景觀便會更不一樣,行人也重新獲取活動空間,並感受不與車輛爭道的行動尊嚴。 綠建築專章加入建設技術的規則裡,標示著一個劃時代、關鍵性的轉變。但未來所要討論的應是綠建築專章裡的指標,是否真正代表生態的指標,或是我們關注的人文指標多過於生態指標,重視視覺景觀多過物種保存,只在乎綠覆率的計算,卻忘了重新營造生態系統才更為重要。目前以台灣現有的綠建築規範而言,絕對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生態城市有賴社區、公部門、專業者三方攜手 生態城市的塑造,如果在社區裡能達成某個共識的話,顯然有很大的助益,但是在過程中,仍舊不能忽略公部門和專業者扮演的角色。如果有些社區要達成生態巷道來作為生態廊道或足跡的完成,其實要作的不僅是開開里民大會而已。社區對生態環境意識的形成,很可能需要耗費三、五年,乃至二十年時間,與之相輔的都市計劃、都市設計準則、土地使用分析管制規則等相關法規和法定計劃,更缺一不可。其中的規劃技術、法定計劃的訂定,立法技術等,尚得仰賴專業與學界,透過最終與社區民眾的合作、協商的方式完成規劃,使推展進行得較為快速與順暢。 所謂的新都市,只是在現今這個時間點,人類到達了這塊宿地或農業區如此而已,在這之前的千百年還有它的足跡、水文條件、地形條件,有其植栽、景觀、生態、物種,可能是千百萬年來切割的結果。舊有土地擁有自然紋理,它也是記憶的延伸,如果人類採取大力介入的方式,其實容易消耗人力物力。該學習的是如何依附、融合在環境裡,在各種物種間更謙卑地生存,這種生活方式與價值才能讓人類綿延。如此人文記憶得以伸展,而非競逐資本主義下拉斯維加式的華麗、浮誇式的量體。而在這樣的期待下,人類舊有專業性的傲慢,老式觀念中如人定勝天的概念,都該藉由專業媒介或平台被大力地針砭,唯有積累新世代的環境倫理,才能確保無可取代的生活品質與愉悅。(2005-06-0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