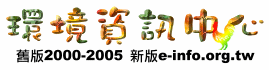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自然與倫理] 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土地倫理」的啟示(五) 作者: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 事實上,不只在「保育教育」這個名稱底下的教育活動才與保育有關,李奧波在這方面也有很重要的洞見:「要能夠對於土地的內涵有所領悟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要對生態學有所了解,……事實上,對於生態學的了解,並不一定要由標有生態字樣的學科開始,很可能它的標題是地理學、植物學、農藝學、歷史學或經濟學。」然而,他感受到:「很多高等教育似乎是故意避開生態觀念。」這不也是值得我們教育工作者深思的嗎? 除了教育之外,另一個必須挪走的主要障礙就是:「不要再認為土地使用的適當與否,純粹是經濟的問題而已。」於是,李奧波在「土地倫理」論述的最後,作出下面的結論:「我們必須從倫理學與美學的角度,來檢驗每個問題是否正確,同時也考慮它在經濟上是否合宜。一件事情如果傾向於保存生物社群的完整、穩定和美的話,它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1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反對以經濟作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考量,但他並沒有完全忽略經濟因素,不過他所強調的是「合宜的」經濟,而不是像現今市場經濟裡頭「無限成長」的經濟。這種經濟理論之下,市場外的每一樣事物稱為「外部性」(externality),可以不予考慮。例如,除非乾淨水稀少到在市場中足以顯示出其成本,否則我們可以一直不管水污染的問題。同樣的道理,只要整個經濟能夠蓬勃發展,我們可以完全不考慮受傷害的人民和遭破壞的環境。這種價值理論應用到公共政策時,藉著社會福利制度,把社會問題推給慈善團體去解決。事實上,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危機處理和資源分配,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包括一切在內的參與機會和權利分享:不但要去關心處於經濟市場外的社會邊緣人,也要去關心被摒除在市場之外的生態體系。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建立起符合生態運作法則的「生態經濟學」,而不是像現在這種與自然界對抗的「市場經濟學」。 (三)閱讀土地的歷史 李奧波在「土地倫理」中另一個重要的洞見,是他對人類歷史的解釋,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只從人類的企圖心來解釋歷史,其實,土地的特性以及人類與土地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和住在其上的人的特性一樣地,兩者都強有力的共同決定了歷史的事實。……植物演替(the plant succession)主導著歷史的方向,但很少人以這種觀點來看歷史,只有把土地視為社群(land as a community)的觀念,能夠融入我們的思想領域,並內化為我們的信念,我們才有可能學會這樣的觀點。」 我們以一個具體的研究案例來檢視李奧波的歷史觀:1938年,美國政府的水利專家羅得米克(W.C. Lowdermilk),奉美國農業部之命,考察幾個古老國家土地利用的情形,以供美國的農牧業者參考,目的在於了解如何能擁有持久的農業經營以及土地資源的保育。他的研究報告《土地利用七千年》中指出:「土地上記載著人類生活的史蹟,懂得土地語文的人,可以從殘留的痕跡中,讀出一個民族或是一種文化盛衰興亡的經過。」這樣的結論與李奧波的說法不謀而合。 該報告中提到,早在1922-1927年間,他就在中國大陸從事一項國際性防止災荒的工作,使他對水土沖蝕的嚴重性,首次得到極深刻的印象,他的結論是:「土壤沖蝕是一種危險的敵人,它在不知不覺之間破壞了文明。」而「人類佔用土地以後,無意中助長了土壤的崩潰,這就構成了今日華北衰落的原因。」因此,他稱黃河為「中國的憂患」。 半個世紀之後,一位捷克裔加拿大教授史凡拉(Vaclav Smil),在為世界銀行徵信資訊的研究計劃之下,親臨中國大陸,為中國的自然環境把脈,將共產黨統治下自然環境受人為破壞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於1984年出版《惡地──中國大陸環境的惡化》一書(金恆鑣翻譯,牛頓出版,已絕版),成為大自然向極權橫逆控訴的最大証據。九年之後,史凡拉於1993年再次將他後續的研究呈現給世人,並指出:「中國大陸的前程所面臨的限制,在於它本身天然環境的極限,以及在它以猛烈的態度追求遲來的/誤期的現代化之際所帶給環境的破壞。」 (四)留給後代的災難與危機 《土地利用七千年》中的結論指出:「土地不同於有經濟價值的其他商品。在任何情形之下,土地是構成國家的要素之一,……如果土地遭破壞,自由選擇的機會根本不存在,只是把災難與危機留給後代。」然而,在極度欠缺歷史感的台灣,有多少人會考量到後代可能遭遇的危機?其實,災難與危機早就不是「未來的、後代的」,它們已經天天在我們這個島上的每個角落腐蝕潰爛著:「繼森林砍伐之後,如今,茶、檳榔、高冷蔬菜、果園、芥茉、小木屋等違法濫墾的行為,形成台灣山坡地有史以來最鉅大的傷害,官僚與人民卻未曾察覺其嚴重性」、「台灣在近代文明發展史上,由於欠缺理性的國土規劃與資源永續利用之施業,因而在1991年以前,大抵將全台原始森林生態體系,摧毀了將近百分之76,嚴重挫傷全島集水區系以及維生系統,……迫使水、旱災變成今後台灣長年的最大限制,……台灣今後的產經困境,終將因水資源及其相關問題,產生難以估計的危機與損失。」 最後再以更具體的一個實例來測試我們的保育文化:淡水河在生物資源方面十分豐沛,稱冠全台。如今,除少數耐污染的魚類之外,整條淡水河可說是毫無生機。除了河水污染外,另一對淡水河中水族生靈的淪亡要負起很大的責任因素就是水壩/水庫的興建。從碧潭攔水壩往上游算起,還有青潭堰、直潭壩、屈尺壩,一直到翡翠水庫高達122.5公尺(約40層樓的高度)的超高壩體,任何逆流戰水能力特強的魚類,都要望壩興歎。值得一提的是,除屈尺壩是早在1898年日據時代所建,其餘四壩則分別築於近1、20年的現代。可是,也只有屈尺壩西側設有魚梯、魚道,以供水族往來,日本政府這種具「前瞻性」的建設,反映出在他們文化中的生態良知。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卻依然落伍到忘了、不知道要設魚梯、魚道,真是令人汗顏、扼腕! (待續)
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