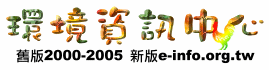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 �@ |
��[�۵M�Ѽg]�M�������L�u��ᤧ���@--�� �@�̡G��L �@�@�]���`���Щu�`�ʪ��Ӫ��A�ҥH�յ۱N�ثe���}�᪺�Ӫ���_�ӡA �@�@�W���@�Ӧ�{�A�a�����쪺�����@�_�h���F�`�Oı�o���@�w�n������s�B �@�@�����s�Υժe�A�u�n���ߡA�ͬ����Ҫ��P�D�A�B�B�O��C �@�@�j�q��p���j�ᵵ��������~�٦��x�W���B�j���s�V�B�д���B�c��Υդd�h�A �@�@�������j�ᵵ���ؤl�����@�������A0.5�����e�A�|�����ۼկ몺�L�۸��a�A �@�@�x�W���O�x�W��;�ءA�]�O�@�ɯŪ����[��ءA�O���ЦЪ��Ƹ����n���ơA �@�@��i�H�ǥѦo���O�W�u�W�d���v�ӻ���������Ӫ����[��O�Ψ��W�r���ߺD�F �@�@�д���O�ǻ������{�ȥ����ҹD����ɪ���ءA�L�u�������S�ʬO�䥦��ةҤ֨����A �@�@�ҥH�Ǧ��i�H��������s���u������v�A�o�����l�������������`�A �@�@�����]������Ӱ��w�A�o��دS�ʥ[�W�����@�ΡA�I���_�ӴN�|�o�X�S�����n�T�A �@�@�Ҧ��S���u�T��v���~���A�~����o�o�ӥ~���A�N�Ӥ@�}�L�����ҧڪ����k�F �@�@�դd�h���ڦ^�Q�_Ū�p�Ǯɥ��o����ַ�����������~���ơA �@�@�d�h����֤]�ϱo�o�����ڭ̰��ӥH�m���ɶD��������H�A �@�@�Ӧo�@������K�B�E�������B���|���K��}�X�Ӫ���ǡA�����F��~���~����l�A �@�@�ҥH�S�W�u�~��l��v�F�c�쪺�X�{�A��n���ڥΨӻP�p�B�ͪ��ӹ{�o�������C���A �@�@�]���o�������ܬ��B��٪��`�����A�ݰ_�ӴN���O�Ӧ۵M�ɪ������A �@�@�[�W���I���L�ƪ�����A�H�K���ֽ誺��A�@�I�N�K�W�h�F�C �@�@�ڭ̤@�s�H�N�o�˯��b�j�q��p����~���x�W���U�A �@�@�q�j�ᵵ������}�l�ʹӪ����غءF��U�����v����ɡA �@�@�N���K���л��v�o�@�DzΦX�|���S��A�����կ��𪺬��P��@�ΡA �@�@�]�����o�ˤ@�Ӥj��H�a���i��ij���U���E���A�A�����~���P����B �@�@�[�Ъ��~�ۤl�Υ|��W�F���}�X�|�ᶶ�ۻd��b�_�Ф������������_��A �@�@���W�¥x�@�u��A�k��ҫn���A�L�K���x�����u������D�A �@�@�q�s�x�@�u�����[���U�����Y���A�@�����Y�ӤU�A�N�|����T�����A �@�@�A���e���[�N�|�ݨ���ǰ����Ӫ��骺���ܵP�A�}�l�t�@�ӴӪ��Ѧa���y�C��{�C �@�@�Q�G�I���}�Ӫ���A�A¶��Y�N�����t��u�����æa�v�������W�A �@�@���ۥ��Ȫ��P�黡�æa�A�M�����������ظ��Ǫ�²�\���u��z�̬u�v�\�ԡA �@�@�o�˪�����{�w�ơA����F���I�����Y�檯�סA�Ӫ����u�O�ڪ��@�شC���A �@�@�z�L�Ӫ��A�گu���Q�ޥX���O�a���״I���H����v�B�a�z���һP�ͺA���[�A �@�@�z�L�\�Զ��K���вM�����������A�z�L�۶O�J��A �@�@����h���H�����|�@�_�ӧߴӤ@�y�p�H�Ӫ��骺��B�ڷQ�A �@�@�\�Ԥ��ڽ͵ۿ�z�|�u���Τ��g�O�����Ȫ��c�Q�K�K�A �@�@�]���ڪ��D�C�@�����u���ȡv�p�G�{�b���ȡA�N�ӴN�K�K�A �@�@���ۻ��ۡA��Mı�o�ۤv���I���b�s�u�p�H���g�Q���v�C(2002-07-12) ��[�Ѿ�§]��L�Шζ�����_�@--��
�@�@���_�g�`������𪺬����G��A������Ө��u�O�@�����H��ת����b�A�ӳ��_�G�ꤺ���H���ƪ��ؤl�A�g�ѳ�����B�ƿ�A�]�Ӧb�г����ɱ`�i�H���쳶�_�����v�A��������ͪ��O�ϥ����������`�����Ѿ��ءC �@�@�����Ѿ�U�������c�|���X�ئ����骺�W�ҡA12���ت�������15���ؼe����a�A�o�˪K���Z�K���Ѿ�A�ٱo�t�_���p�q�B���B�����d�j���C�����c�X�ا�����A���U���d�j�����Ѿ�]���F����~����ѭ��D���n�a��A�Ѿ�@���O�a�誺�ͬ����ߡA���E�ۦa��~�����������F�C �@�@�Q�n���X�o�ʦѳ��_�A��ij�z�g�Ѿ�L��V�e�Ӹg�L�a��j�����᪽���ζ���T�q�g�L�F�I�u�����x�_�j�ǹw�w�a�ᤣ���B����]�S�����㪺�ѹD���P�^�N�i��F�C
����K���i�Ѿ�§�Хx�_���öQ����j http://www.csnp.org.tw/ ��[�M��@�a]�����ت�����@--�� �@�̡G��֬� �@�@�T���ݤ��A��~�e�h�@�A���ɤ~66���C �@�@�ͦb��a���A�ͦb�@�ӳh�W���A��A���b��a���A���b�@�ӳh�W���A��A�����W�W�@���l�A�ӤF�S���F�A�O�e�F�@�Ӷ�A�٬O�����F�@�Ӱg�H����١H�Ӥ���O�u�����v�H �@�@7�Ӥ�e�A�ڦ^�h���L���ӡA�g�b���d�O�W���m�W�w�g���ǭ��ƤF�A����Q�B���O�o�ҽk�����A�O�����\���C �@�@�T�A�M�f�f���b�ڨ��ǡA�o����J�ڤ��n���A�ڧԵ۲\�A�ݵۤ@��諸�ȿ��Ƭ����u�A�b�i�����������@�ˤ������h�C �@�@�T���S�����A�ڪ��D�L���۫H�����A�]���۫H�ȿ��A�ӧ��٬O�۸۹��a��L���ܡA��s��F�S��A�L���w�ܰs�C �@�@1980�~�A�ڭ̤����34�~�Ĥ@�������A�b�C�q���@�a���]���A�ڭ̪��]�ﶼ�A�ܧ��F�@�~�T�x�A�L���o�ذs�u����b�W�~���A�T���M�ڤ��b�����٭��n�C �@�@�ڭ̦��ܦh�ܭn���A���ƿ����A�i�H�g�@�w���ѡA���ڭ̳������ܡA�K�F�]�����A���]�~�A���W���P���J�a�D�S���͡C �@�@�ڭ̤@�����j�A�b�G���j�Դ����A�L�F���~�C �@�@��T���̦����O�СA�O�@�Ӥj�~��@���U�ȡA�ڭ̳���F�s��n�A���b�Ф��Y����͡C �@�@�ڭ̨C�H�@�J�A�L�ܧ֦Y���F�A�ӧڪ��J�٬O�������A�L�i�D�ڡA�L�Ⲵ�����_�ӡA�ڴN���ͤ��e��L�L�إh�A��ӤS���ڭ�֤ӺC�A�L�N�����A���[�ڪ��J�]���F�A�ڭ̯��_�ө���A����n�A�y���j�\�i���C �@�@��өn�n���T���F�F�ڡA�ڹ�T�����A�L�o���A�o�����F�A�]���U�Ӧ~��@�A�L�i�H���ͤ��e��ڼL�ءC �@�@�줵�ѡA���٨S���v�A�H��ä]���٤F�A�ӧڭ̤����A�ä]�ˤ��M�O�֤��F�֡C �@�@�T����ڤj6���A�L�`�P�X��~�֬ۥ骺�Ĥl�b�@�_�A�ګD�`�r�}�A���`�O�i���F�L���B�Ͱ�A�u���ڭ̨�H�b�@�_���ɭԡA�L�~�a�ڪF�]��]�C �@�@���@�Ӭ�]�A�L��ڥh�����T������X�]�ëͱ^�^�ݰ��]�C�^���A���~�o�o�ݡA�S�����X�n�A�o�}�ä��h�ëͱ^�F�A���j���[�A�S��ۥL�A��ڥh�ݰ����C �@�@���~���۾��A�Ǿ�L�A�j�����A�������F�A�ڭ̮��L�����ˤ]���F�A�����s���C �@�@�ڭ̴����@�Ӵ������쪺�F���p��Ū�ѡA�C�{�饻�x�������A�ڭ̴N�|���k�`�A�饻�L�L��A�ǮդS��_�W�ҡC �@�@���@���A�����ӱo�ӿ�C�ڭ̾Ǯղ������ɭԡA�饻���M�L�M�B�L�w��F���ɡA�ڭ̨�H�^�^���}�C�b���~������]�C���b�^�a�ءA�襩�S�]�i�F��x���]���B�����n�B�I���n�M�s�s�P�P���j�n�C�w����ܱ�A�T����M���U�ӡA���a����ڪ��Y�G�u�ѥ|�A�ڭ̰��W����A�A�V�F�A�ڦV��A�p�G�ڳQ���A�ٯd�U�A�A�p�G�A�Q���A�ٯd�U�ڡA�k�X�ӡA�����^�a�C�v �@�@�L�ΤO�@���A��ڱ��˦b�@�������ءA�L���v�l�N��M�����F�C �@�@�צb�����ءA�ʤ]�����ʡA�̦��I�l�A��L���}�B�n�q���䨫�L�C �@�@���й��ӻ]Ţ�A�����p�B�A�ڪ���n��F�A�Y�v��F�A���U���F�g�ܦ��F�d�ڡA�f���p�I�A�B���B�ް��B�f�G�H�H���`�]�`���U�C �@�@�ڤw�}�l�P��t�w�A�ڪ��D�w�������Ӥ[�F �A�p�G�饻�L����ڱ����A�]�@�w�|�������C �@�@��L���B�n�������h�A�ڶ}�l�m�˪���A�b�@���ҽk���A�I��F�@����ʡA�������b���F�����l���A���@�Ӷ�ꪺ��⪺�ʡC �@�@�Τ�Τ����}�}�A�ʦײL����A�ʬ�եժ��A���Y�j�T�A�s��a�פ@�f��N�Y���F�A�����F�@�j�J�ŷŪ��B���������A��ڪ��R�q��������t�ԤF�^�ӡC �@�@�ѭ�¡A�ڴN��a�F�A�T���M���˳��b���ڡA�ڧi�D�F�L�̦�ʪ��G�ơA���˺O�ۧڡA�]�����ڨ��W���d�g��o��ż�F�A�o���G�u���Ħb�O���A�C�v �@�@���ˤw�f���A�S����͡A�u�Τ@�ǰ���Ӫv���C�C���Y�@�����¥����A�L�N�|�n�@�ǡC �@�@���@�]�A�کM�����˺Φb�@�_�A�a�g���A��ť��L�̪��ܡC �@�@���˻��G�u�A���|�����A�n�H���n���A���Ĥ@���b���U�ڭ̡A���M�A�ѤT�M�ѥ|���|���w���k�X�ӤF�O�H����A�N�|�h���غس��l�C�v �@�@��Ѥ���A���˴N���F�C �@�@�T�����X�N�b�����M�������X������A���ڭ̮a�u���X�����C �@�@�q�@���s�s���������g�p�D���ӡA�D�ǥͤF����A�@�G�G���СA�Ф�������C�X�P�X�Q�ʦ~�����շ��A�b�߭��ءA��������o�ݡC �@�@���~���گ}���F�A���~���ä�]�i�@�q���A66���O�Ѧ~�ܡH���@���s�s�������p�D�A���V���H ��[�}�h�g]�����B�c�����\���x�M�@--�� �@�@�@�ӥs���j�ê��k�H�A�b�ͤ�ɦ���@���x�M�A�o���w�������x�M�A�����A�ܮt�A�ٺ��fż�ܡA���O�|�H���ܡA�N�O�DzʸܡC �@�@�j�çV�O�Q���ܳ����A�סA���_�a��e���Ǧ�§�����r���A�X�����֡A�ϥ��Ҧ��L�Q��i�H���e�@�Ӧn�]�˪��欰�A�L�����F�C�����S����ΡC �@�@��O�A�L�}�l�ﳾ�q�F�_�ӡA���]�q�F�^�h�A�L�ΤO�n���x�M�A���G�u������ͮ�A�ӥB�ܱo��ʾ|�A�ש�b�L�i��������㤧�U�A�L�⳾���i�F�N���d�C �@�@�X������A�Lť�쳾���n�j�s�A��B�ý�A�٦y�s�F�_�ӡA�o�ߨ�N�w�R�U�ӡA�@���b�������A�L�S�Ať��b�I�n���C �@�@�j�óQ�~�ۤF�A�H���ۤv�i��`���F���A�K���W���}�N���d�����A�u���x�M�N�R�a�B�X�A��W�j�æ��X�����u�A���D�G�u�۫H�ڲʾ|�����ͩM�欰���w�_�ǤF�A�A�ڷ|�V�O��i�ڪ��欰�A�گu���ܩ�p�A�Ʊ�A�����̧ڡC�v �@�@�j�ù��A�ת����ܫܬO�岧�A���Q�n�ݳo�����@�ʪ��ܤƬO���F����t�G�ɡA�x�M�S���f���D�G�u�ڥi�H�ݤ@�U�A�̭������Q�����������F����ƶܡH�v �@�@��ӭ��H�ڪ��H���u�i�F IBM�C �@�@���q�H�ƥD�ު��D�o��ӳå�C�ѳ��n�Y�H�A��Oĵ�i�L�̡G�u�p�G�A���x���b���q�ئY�@�ӤH�A�A�̴N�|�ߧY�Q�����I�v �@�@��ӭ��H�ڰ߰��o�o�a�����A���ܵ����|�b���q�ئY�H�C �@�@��Ӥ�L�h�F�C���q�إ��w�L�ơC �@�@��M���@�ѡA���q�o�{�t�d�������q�åͪ��M��u�����F�C �@�@��O�H�ƥD�ޫD�`�A��Ө�ӭ��H�ګ㥸�A�÷��������F�L�̡C �@�@�X�F���q�j���A�@�ӭ��H�ڰ��W��t�@�ө��_�ӡG�u�ڤ@��ĵ�i�A���n�Y���b���ƪ��H�A�A�N�O��ť�I�ڭ̨�Ӥ�ӨC�ѦY�@�Ӹg�z�A�S�H�o�{�C�A�ݡA�{�b�Y�F�M��u�A�L�̰��W�N�o�{�F�I�A�u�O�ӽޡI�v �@�@�u��v��R�v�O�ڭ��~�u�۵M�Ѽg�v����A�b�g��}���@�ӱM��C �@�@�o�^�A�ڭ̴����ǥѡu�H�v�����D��v���u�ͺA��v�@�~��R�v�A��Ū�̶i�J��v�̩���ɪ��ͺA�[��{���P�ͺA���Ҥ����A��Ū�̱o�H��ͬ��ƪ��覡�A���״I�h�����ͺA�{�H�A�B�R�߷P��������Ҫ���ߧa�C �@�@�w��U�ɧ�Z�A�ýзf�t500-1000�r���k����Z�A�ԶD����ɪ��g��ͺA���һP�߱o�C �@�@�۵M�Ѽg�O�ڭ̦b�g��}���@�ӱM��A�Q�Ӥj�a�����P�۵M�۳B���g��Цw�R���B�I�窺�B���⪺�B�|�ߪ��B���ִr�����B�R���L�����Ǫ��A�L�O���Ѧa���y�y���P���λP�j�ƦP�@���ۦb�A��άO�R���L����_�P��ߪ��o�{...�����A�P�۵M�۳B���g��P�G�Ƨa�A�w��j�a����Z�C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