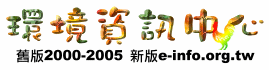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欄作家] 葬禮與落花 作者:賈福相 前幾天參加了一位學生父親的葬禮。死者是個工人,生在種田人家,卻不喜歡耕作,十六歲開始用小卡車送牛奶,後來學會了修理電器,經營一家電器修理店,生意好的時候,可以僱三個幫手,這期間,結了婚,有了一兒一女。十年前把修理店賣掉,開始去公家林地砍伐木柴,特別是最耐燒的樺樹,曬乾後綁成若干小綑,家家戶戶兜售壁爐火木,有時也託加油站代賣。 衍柴收入雖不及修理店,但他喜歡郊野,喜歡林地,喜歡村中的野花,他說他終於找到了自已最稱心的行業。
不久前他患了肝癌,很快就結束了61歲的生命。葬禮靈堂內有幾十張照片:背著書包的小學生,店鋪老闆,結婚,抱孩子,站在杯中,站在運柴車前……。 無論從歷史的任何角度看,她輝煌101歲,都可大寫特島。 二次大戰期間,她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花園,澆水拔草,她總是帶了綱盔和防毒器,也學會了手槍射擊,那時有人勸她去加拿大避難,她說:「不走,我的孩子不會走,國王不走,我不會走,國王是永也不會離開倫敦的。」 希特拉說她是「歐洲最危險的女人」。 我手邊報紙有八頁紀念她的生平,擠滿了照片:兒童期,少女期,王后期,母后期,她晚年的照片都戴帽子,每一頂帽子,都像一朵花。 一個61歲的加拿大工人,一個101歲的英國母后,都愛花,花開花落,過了一輩子。靈魂呢? 妻子畫室內有一筐落花,竹製的筐,長方形,像一口棺材。滿棺材的花有大有小,有各種顏色,各種形狀。木槿花只開一天就整整齊齊的捲起,像古巴的雪茄煙,落地有聲;水仙花死後沒有變形,只是蒼白了些,仍然是六枚外瓣,圍著杆狀的內瓣;冰島嬰粟花,蓓蕾期低著頭像少女,開花前亭亭玉立,開花時光華奪目像少婦,死後一瓣瓣凋零,花非花了;秋海棠盛開時,明艷照人,死時卻變成髒兮兮的棕黃;蝴蝶蘭永遠是那麼高貴,那麼純潔,一朵花可開四個月。 這些花,洗去鉛華,躺在筐中,是不是仍夢著無辜的蕾和盛開時的洞房火燭,還是完全忘記了自已歷史,要以看花人的記憶來完成? 工人的葬禮,母后的國殤,竹筐內簇簇的落花,都完成了生之旅,每種花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花像人?還是人像花?如此簡單,又如此複雜。(2005-05-1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