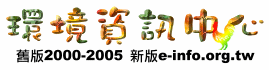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欄作家] 樹和人生的情趣(上) 作者:賈福相 夜十點半,有風有雨,天空隱得遠遠的,窗外是濃濃的深灰,十月的香港,秋已近了。 我穿好鞋子,找了把雨傘,問妻子要不要陪我出門,我告訴她要去校園東隅,看一棵樹。她抱怨我發神經,為甚麼走一里路看一棵樹,深更半夜,淋了兩會感冒的,但她還是陪我去了。 這是棵「大葉合歡」。許多有羽狀複葉的豆科植物,入夜,葉子就合攏起來,我不知道這棵大葉合歡會不會如此,不證明一下,會睡不好覺。 葉子真是密密的合併著,每根葉柄有八對複葉,每一對都緊緊地抱在一起,面對著面,把背讓給風和雨,在蒼黃的路燈下,這棵樹變了形,變了色。 大葉合歡又叫長舌婦樹 大葉合歡又叫長舌婦樹,我問妻子是否知道這個怪名字的來源,她說可能是因為葉子像舌頭,又那麼多。猜得雖然不對,也很有道理。原來大葉合歡是一種落葉樹,入冬,只留下光禿禿的樹幹,和一串串乾了的扁豆,快一尺長,扁豆無橫隔,空空的腹囊中,有七八棵自由流動的豆子,風吹過,豆于互相撞擊,發出怪怪的響聲,似人語,似風鈴,有講不完的話,一點點風,就會吵個不停。 妻子說這個名字一點也不好,很多男人的舌頭比女人更長。 中國南方的風俗,結婚時送一對杯子叫「合歡杯」,洞房花燭夜,新娘新郎,把臂飲酒,叫「合歡酒」,因為先有了這種風俗,葉子擁抱的樹才叫合歡樹呢,還是先有了合歡樹,洞房花燭,男女擁抱,杯子叫合歡杯,酒才叫合歡酒呢? 我在香港科大教一年級的「多樣性生物學」,今年有96個學生。我擔心他們只學到一些近代的生物理論,只學到一點點生物化學或遺傳工程,而忽略了生物就是自然,一草一木、一朵花、一隻靖蜒,都是生物,生物學就是研究生物的生活,由小至大,都要知道些,科學不分新舊,只要是好,只要是真,就值得學。很多學生怕記生物的名字,也有人認為分類學只是屬於博物館,我們只要「現代生物」。這是一種錯覺,生物的名字,是單字,不認字,怎麼可以讀?怎麼可以寫?不會讀不會寫,真是枉談詩詞,枉談「相如賦」,是非常不科學的。 我在校園裡,指定了31種樹,要求每個學生課餘作業,都要學會用滋洛爾(Thrower)的香港樹木檢索表,至少記得20種樹,中文名、英文名、拉丁學名及滋氏表上的用詞都要記。 樹多采多姿有各種風貌 樹多采多姿,有各種風貌,今天開花,明天結果,今天有新芽,明天有落葉,樹上有寄生植物、寄生蟲,有蝶、有鳥,樹不會跑掉,站在那裡,靜靜等候,大風大雨地不失約,世界各地千秋萬歲都有樹,認識一些樹,真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 若干年前,我去義大利開會,在一個濱海的小城,住的旅館和講演廳有一段距離,一次步行去講演,途中看到一個老婦人蹲在街旁找東西,我也蹲下來,她笑一笑,指了一下地上的松子,剝去殼,放在嘴裡,我也撿了一顆,剝去殼放在嘴裡,其香無比,我對她笑一笑走開了。仰頭一看,才知道走在一排松樹下,樹冠傘狀,樹幹曲中有區、蠟黃色的樹皮,亭亭而立,我想起在一本書上曾看到過這種樹,叫「傘松」,又叫「羅馬松」。那天下午,在街頭,一個朋友指了指那一排松,告訴我這種傘松,一千年前傳到英國,在英國叫羅馬松,我當時有種滿足的會心微笑。 還有一次在加州一位朋友家看到了一棵棗樹,在台中朋友家看到了一棵香樁,這兩種樹在我家鄉很普通,十萬里外,幾十年後,再相遇-各種似曾相識的溫暖。高適的「天下何人不識君」有了種新的境界。 樹也是好的科學研究對象,那棵「大葉合歡」為甚麼會把葉子合併起來?西山的落日對它講了些甚麼!它有沒有肌肉和骨骼!如果沒有感光的眼睛、神經、骨骼和肌肉,怎麼會合起來?又怎麼會伸開?這種伸伸合合有甚麼好處?如果沒有好處,為甚麼會規規矩矩的作一輩子而樂此不疲?其他的樹為甚麼不這樣做?如此等等的問題,有些孩子氣,但都需要科學證明的,何況,孩于式的好奇常常是科學研究的動機。世界上很多偉大的科學實驗,都來自「大膽」的假設,大膽可不是亂吹大氣,是由仔細觀察而來的,沒有一個科學家,不是一個好的觀察家。「仰觀俯察」一直是科學家的第一步。 我的「樹」題目,就是要學生們小心觀察,認真觀察,作紀錄、作報告、牢記於心。告訴他們,期末一定要把紀錄本繳交給我,紀錄本上的勾畫和草稿,像樹的年輪,也自會透露學生們學習的一些消息。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樹,最高的生物是樹,最古老的生物,4,600年了,也是樹,30年就可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讌賓客,眼看他樓塌了」,4,600年是30年的153倍,150年剛剛是香港作了殖民地的年齡。 4,600歲的年輪裡,鎖住了多少歷史?儲藏了多少智慧?比中國《詩經》老了1,000歲。 惆悵彩雲飛,碧落知何許 「惆帳彩雲飛,碧落知何許,不見合歡花,空依相思樹,總是別時情,那時分明語,判得最長夜,數盡厭厭雨。」這是納蘭容若的《生查子》,寫一個幽怨自苦的女人,有太多的相思和纏綿,這首詞並不太動人,也不是容若先生最好的詞,但他把合歡和相思兩樹的名字用得很靈巧。其實,這兩種樹生在亞熱帶和熱帶。兵馬勞碌的納蘭先生住在北京,而又常住關外,很可能從末見到這種樹,他卻自然的把樹名用在詞中,成了佳句。詩人真是敏感。 相思樹終年常青,原產地是台灣,也是香港最普通的樹了。長得快,但長不高,可以生在貧乏的土壤,可以拒蟲害,喜歡一簇簇的擠在一起,特別是山坡上,一座光禿禿的山,不幾年就全綠了,防風、防雨。 初夏花開,許多小花結成絨絨的黃球,成千成萬,耀眼明亮,不看是不行的,要避也避不開。喻麗清在柏克萊初見相思花,為了篇《靉靉黃雲相思海》,嚮往著台中東海大學校園的相思樹。是的,大度山上相思樹,要忘也忘不了。 三十多年前,我在東海作助教,26歲,仍少年。相思樹下相思夢,再歸來,人已老,山仍在,樹仍在,夢在遠山之外。 我突然懂了稼軒的長嘆:「自笑好山如好色,只今懷樹更懷人,閑愁閑恨一翻新。」(待續) (2005-08-2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