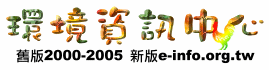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欄作家] 搖曳的紅毛草 作者:企鵝 在我平常閒晃的路線中,有一段沿著枋寮溪的堤防,兩旁是農田與果園,在枯水期時的枋寮溪連沒口溪都稱不上,河道裡的相思樹小苗,隱喻了這裡就算是豐水期,仍沒法動搖它們的生長,它們驕傲的拔地而生,有一人多之高,水牛、黃牛懶散的帶著一家子在河道中閒晃;這裡是一塊極棒的放牧地,除了沒有足夠的水源可供打滾之外。 傍晚時分,在這條堤防上騎車是一件很閒適的事,陽光襯著紅毛草發亮,它們就這麼沿著堤防一路生長,生長到沒有路的地方,仍然隨著風搖曳生姿。這是十分棒的畫面,特別是逆著光,更能彰顯出紅毛草的動人。我想起了以前老師說過的紅毛草採集故事,然後想到它們現在這麼隨處可見。在未發現之初,或許沒人能想像這種外來種植物,就這麼一路揮軍北上,廣泛生長。 相較於植物故事,我或許了解動物多一點。 在我以前曾經服務的單位,雖然名為特有生物研究,但外來種的入侵,卻也明顯地分散不少的研究人力,從鳥類到哺乳類,從爬蟲到魚類,從昆蟲到水生生物,外來種動物的足跡已經出乎我們所想像,而外來種植物的散布,也早已造成台灣山林的另一種困擾。 這都是可以歸類到競爭的故事裡,只是這種競爭多半是來自於人類有心或無心的栽秧,結局總會是殘酷的,不管外來種適應或否,都是一種生靈的浩劫。 小時候家裡有著一大片的稻田,或許不少人都有過拔起那紅紅成串一顆顆福壽螺卵塊,然後用力踩碎的經驗。後來,家裡的稻田隨著時間轉作,福壽螺似乎已經消失在我家農田裡,不過在南部某一塊溼地公園裡,他們仍然在進行著拔除與踩碎這種繁複且無聊的動作。福壽螺早已在一些水域裡生根,而原本是用來養殖食用的目的,早在九霄雲外。牠們就這麼吃掉多少台灣稻作,或者台灣原生水草?沒有人知道。 不過,或許琵琶鼠與美國螯蝦知道?或許牛蛙也知道?但是只有人類不知道。 同事曾經拿著釣竿示範著怎麼垂釣多線南蜥,我對於這種釣蜥蜴的技巧驚歎不已,不過同事卻對於牠們的散布驚歎不已。南二高沿路上的白尾八哥數量讓我驚訝不已,而牠們熟練的利用每一個可能繁殖的巢位、把握住可以擴張的生態區位,這或許是我另外更要咋舌的地方。 台灣究竟有多少種掠鳥科的鳥類?或者該這麼問,台灣原本有多少種,而現在又增加了多少種?台灣原本有沒有鸚鵡?而鳥店裡的一些怪鴿子怪文鳥究竟又有多少種?台灣鳥類名錄幾乎每隔幾年都要重新修訂,但增加的往往是一些原本不該出現在台灣,八竿子也打不著的。台北的某公園,已經被戲稱成逸鳥公園;而南部的某大學裡有著鸚鵡飛翔的奇景。 離鄉背井活在不是自己原生的土地上是什麼樣的感覺?那原本屬自己的空間被剝奪了又是什麼樣的感覺?我們總是在不知不覺間幹一些傻事,就像蔓澤蘭勒住了樹木,喜好新奇卻又毫不在乎的個性,把本地原生生物推進泥沼,也這麼謀殺了許多無謂犧牲的生命。 紅毛草隨著山風輕搖,在夕陽下閃著紅光,對於提倡致力於台灣多樣性研究的研究者來說,彷彿是一種美麗的訕笑。 這種快門,我按不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