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m�������i�B�n
��ƴ��ѡG���H��ƽs�賡
������Ĭ���Bù���B�����M�_���`�q����A���b�@�d�~���K�B�W�˸Ѫ��R�B�A�ӮJ�ΡB����o��B��W�L�T�d�~�H�b�m�������i�B�n�@�Ѥ��A�@�̶��ǡD�ܯS�]Ronald
Wright�^�H���׳ժ��Ǿi�����A�ξ���������B�u�p���g�T�M�Ͱʪ���ҡA�a��Ū�̹C���j�����Ӫ�����o�i�A�Ϭ١u�i�B�v�ҳy�N�����ܡC
�@�U�~�e�A�Jù�����H����F���v���E���O�U�A���F�{�N���H�������C�o�Ƿ�������N�Q���j�۵M������Ǥ��A�i��ҿסu����v������G���B�u��B�A�~�B�����B���ݡB���|���h�B�F����´�A���l�u�C �j�j�p�p������Q�j�}�Ӥ��Y�i��A�_���`�q�����פu���ޥ��A���H���N�q�W���̫�@�ʾ��ˡFĬ��������A�~��@�N�A�N���F���ΨU���W�a�O�ӺɡA�̫��Q�Ƭ����骺�F�z�F�b�j��v���⩤�Aù���Ұ�P��������U�ۮI�Y�W�F�A�H�۫Ұ�դO���X�i�ΤH�f�������A�U�o���^�۸}�U���g�a�A�̫�U�ۨB�W�I�Ѫ��D���C�o�ǥj�Ѥ������J�F�u�i�B�������v���C �u���v�C���t�@���A�N���N�W���@���C�v�a�y�W�Ĥ@�Ӥ��Ĭ���˸ѮɡA�u�v�T��50�U�H�F2�@��ù���Ұꪺ�������A�@�ɤH�f�Ƭ�2���H�A�Ұꪺ�I�`�h�v�T�F�W�d�U�H�F���ڬw�H�b1500�~�o�{���w�ɡA�@�ɤH�f��4���F��F2000�~�A�@�ɤH�f��60���Cù���Ұꤧ��A�@�ɤH�f��F13�ӥ@���~�A�K2���H�F�ӳ̪�s�K��2���H�A�O�b3�~���ϥͪ��C���Y�{�N��������A�N���ƤQ���H�a�ӵL�ɨa���C20�@�������A�@�ɤH�f�Ʀ����F4���A�g�٦����h�W�L40���A�o�˪��i�B�H�۹�ͺA�j�W�Ҫ��r�P�������N���C�b�o�������u�g�٨S�������v���C�����A�L�h����a�O�a�H�A�p�����骺�A�o�O�a�y�H�λ��U���͡C �@�̶��ǡD�ܯS�O�u�����p���ΫD�p�����ϧ@�a�A�����v�ۧ@�B�p���B�������C�����H���Ǯa�A�ܯS�{���H���Ǫ��I����g�@�Q�������U�A�u�v�ǩΤH���ǡA���ѤF���ۨ���ƪ��[�I�A�a��ڲ����ߥH���`���ߺD�A�i�Ӥϫ��Ƥ����O�q�B�ʳ��M�M���C�v�H���Ǯa��M���N�Ѩ�H�����o�i�A�u�ڭ̵o�i�X�A�~�A�ɭP�F�����Φ��ΤH�B�����F�ڭ̦b��������@���G���|���šB�F����´�B���Ӥj�H�A���j�ƤF�ڭ̦b�a�y�W���v�T�O�K�K �۵M�@���]�ۧڭ̦Ӥ��_�ܰʡA���H���������O�S���i�B���C�v 2004�~�A���ǡD�ܯS���ܬ��[���j�����褽�����y�]Massey Lectures�^�~�����̡A���t���e��Q�[���j�s�����q�s�@���s���`�ءA�æb�������m�������i�B�n�X����n�W�[���j�W�߮ѩ��Z�P�]�D�p�����Ĥ@�W�]�Y�����ѡ^�A���}�Y�¥D�D���H���U�s�n�S�s�y����O�L�H�C �ܯS�b�Ѥ����X�A�Y�Ϥ���H�۫H�ۤv�����M���{�欰���u��ҿת����Z�H�A�M��ù�����v���B�����S�J���m���B�v�Ъk�x�����D�B�Ǻ骺���`������A�@�����O���פ�����|���ǧ@�C��N20�@���A�ܤ֦�1���H����Ԫ��A���Z�H�]�L�k���{�o���V�C���b�j�v���M������j���e�A�ڭ̤��o�����N��������D�w�i�B�����Ҫ̡C ���ϧڭ̬����F�ͪ���ΨϤ��h�ơA�j�۵M�]�\�u�|�q�q�ӡA�ño�X�@�ӵ��סX�X���H��ާ@����Ǥ@�q�������M����A�o�רs�O���a�D�N�A�p�P�Ѥ��Ҩ��G�y���@�Y����H�A�O�ͦs�F�y��2�Y����H�A�O�i�B�F���y��200�Y����H�A�h�O�i�B�L�F�Y�C
|
|
|
|
|
|
�@�̡G���Z
�ڬO�p�����Z�A�ĽŪ��Ц�A�b�p�����ߡA����X���өʡA���æb�s�餧���C���Z���ڡA�өp�o�O�p���a�����Z�A��O�p���dz�¶�۲����\�h�A�s�s���Ʊ�l�ާA���`�N�A�p�o�u�O�����O�̭��h�A�o�@���ڳ��ݦb���̡C
�ڳ��w�H�H�a���H�b������A���M�ɱ`�涤�W�B�A��������G�̬y�۬O�s���ʪ��]�l�A��O�ڿ�ܤF�b������A�ݵۤj�a�C���ڭ̤@�_�즬�Ϋ᪺�_�и̴M��A�ҿ��\�l�ɡA�ک����٬O�̫�@�ӡA�Ϊ̦b�̥~���ӡC �[�F�A��O�ھi���F�[��ߺD�A��ߩ�h�ܪ��³��Ө��A�ڦ��G�ӨI�R�F�I�A�ӷ��I��p����A����o��[�R�q�C �L�̻��A�p�֦��@�����R���Ц�A�S�O�O�����n�B�����I�A�t�W���R����A²�����O���D�@��F�o�̬ݵ۳�¶�p��������s�A�Y���a���A�A���T�֦����R���Ц�H�Χ�������A���O�S�p��A�٤��O�u�O�@���³��Ӥv�C �ڭ̭쥻���u�O�³��Ӥv�A�o�̤]�O�A�L�̥�M�C ���G�]�u���ڭ̳³��ۤv�~���o�X�L�̻P�o�̡A���H���Ө��A�ڭ̥u�O�³��Ӥv�A�Y�Ϥ����Z�p�A�A���Z�p�ڡC �ڭ��`�O���Ϧb�T�w���Ϧa�̡A�`�O��¶�ۭ�������A�`�O���H�H�������E�A��O�s�̪��t�@�s�P�ڭ̬ۦ����P��A�٩I�ڭ̬��u�q�u��W���³��v�A�ӻ{���L�̦ۤv�~�O�u�����u�³��v�C �����O�³��ܡH�ڭ��`�O�b��X��}�l�s�s���A�ڭ��`�O���w�b�F�l�̥��u½��A�����]�|�w�w���A�~�h�Ф�W��ż���P�H���ΡC ���M�����|�̡A�ڭ̰��Ϫ��ܪ�A���o���O�p�����@�íx�èS���b����n�p�A��O�ڻ����a�����A���h�A�p�L�L���Y�A�ݤF�@�U�ڡC�ڰ��N�a�z�ۤv���Ф�A�߸̷Q�ۡA�ӫ��}�f�P�A�k�͡A�����ڶɤߩ�A�����R���Ф�H�Χ�������C �֪��A�A���}�f�F�C �p���A�p�Q���}�o�̡A�p���h�~�V�Ѹ̡A�p�b���O�̸I��F�Ӧۻ��誺����A�L�̨��P�ڭ̬ۥ�A�o�O�Ӧ۩�d�����~�A�A�ɤߩ��誺����A�H�αq���ѭ������v�C��O�p�߷Q�A�L�̳��i�H��V���v�e�ӡA�ۤv�S��������V���v��t�@�ӥ����h�L���a��C �ڨ̵M�R�q�A�]���ڵoı�p���G���n�h�ܷQ���A�b�p���R���ߤ������äF����R���ڷQ�A�ӥL�̱q���{�uť�L�A�o�̤]�����Q�nť�L�C �p���A�b��A�_�����@�ɡA���⩹�n��ӥh�A�p�۫H�n�観�a�A������A���Ū��ѪšC�p�Q�n�����@����V���v������A�Ӥ��Q�u�O�@���³��C�p�����_�a�y�z�ۤv���ڷQ�A��O�G�ڤ]�R�R�ať�ۡC ��M���A�p���U�F�A�ݧڡA�A�O�H �ڤ߷Q�A�ڤ]���Q���@���³��A�ڤ]���g���ۤv���ڷQ�A�Ϊ̻��ڤ��M���ۤv���ڷQ�C�ڤ]�}�l�C�C�a��p�Ͱ_�ڪ��ݦs���z�Q�ͬ��C�ڤ@�ϱ`�A�a�h�ܡA�өp�H�H�a�B�b�R�q�C �b�ܤ����A������H�A��v���n�A�ڤ����D�ڭ̦�ɭʰ��b�@�_�A�u�O�o�������S�y�����@��A�ڵoı�p�a�ۧںΥh�C��M���A�ڵo�{�ۤv�]���A���Z�A�]���o�{�F�A�u�ꪺ�����Z�A�]�o�{�F�ڭ����æb�p�p���ߤ������p�p�ڷQ�C �ڪ��D�p�ҵ{���ɶ��N��A�]�����������a���A�O���H�A�Ů��ƴ��ۤ@�رҵ{�����D�C�b�]�̡A�p�P�ڻ��A�p���v�K�ߩ����a�A�P���šA�רs�O�n���}���A���F���n�褧��A�p�����ڡA�b�U�@����A�_���ɭԡA�|�^�ӻP�ڶD�������誺�G�ơA�P�p���g���C�ڪ��D�ۤv�O�d���F�p���A�b�Y�@�Ѫ��M��A�ڥذe�۩p�ҵ{�A�߸̬O�ʨ������C �ڹ����B�Ҧ��a���b�A�Ъ��t�߬�W�A�ݵۥ_���a�Ӫ��@������A��[�a���s���~�A�V�O�a�����u�O�@���³�����V�e�i�C�ݵۦP��̧s�s���a���x�A�ڷQ�_�F�p�A�Q�_�F���@�]�A�Q�_�F�ڭ̳����Q�u���@���³��Ӥv�C �өp�h�M��A���n�褧��A�i�O�ѤF�ڦb�_�誺���ݡC �b���ɡA�ڦ��G�S���^��F�����Z���³��A�C�C�D�D�a�ۨ��ۻy��p���Q���C �m��O�n �³��AEurasian tree sparrow, Passer montanus, ���ΥءA�峾�쳾���A�߸s�~�P�H���ͬ����ұ���A�߲ߥж��V�V�A�H�����ί���A�s�x������U�a�C �e�O�ܱ`���������A���e���ԲӸ�ƫo���`���A�p�G��Google�Ӭd�ߡA�j�P�W�i�H�o�������Ĥ@�q���ҽk�y�z�A�Ӧb��~�h�b�]�H���v��V�~�h�A�x�W�ثe�]�Ȧ��b1986�~���ߤ@�@�g�Ӥh�פ崿�g�H�����D�D�C �ܱ`���A�`����X�G�O�H�|�ѰO�e�C ���³��ä��|�E�p�A�ϦӫܩT�w�a�|��ܯS�w�X�ӽd�������V���ϰ쬡�ʡA�ھ��G�����б����g���L����s���A���ʽd��j���O7,600���褽�ءA�ڬ۫H�o�ӽd��b�x�W�γ\�|��p�@�I�A�j���i�H�Y�p��2,000���褽�إ��k�C �P�O�����ت������̡A���������Q�������A�y�����d�A�K�|�~�P�C�夤���쪺�u���b�s�̦ۺ٬��³����³��v�A�o���O�����s�Q�ڪB�ͧi�D�ڪ��G�ơC���e���g��U�L�̾�z���a�����귽�A�H�ξ�z�@�Ǭ�����ơA����������U�A�C�@�س��b�Q�ڨ��̦U����N�q�C�s�³��A�K�O�ۺ٬��³����³��A���Q�ڪB�ͨӻ��A�H�e�O�S���³����A�b�L�̪��ͬ����u�s�³��v�~�O�³��A�ӥ��a�H�{�����³��A�ϦӬO�b�q��u�W�s���H���ӨӪ��~�ӳ����C��O�L�̺٩I�u�s�³��v���u�³��v�A�ӧڭ̪��³��A�b�Q�ڻy�̬O�u�q�u��W���³��v�C �Q�����f�A���L���a�H���]�N�L�̪��³��٤����u�s�³��v�C �ҥH���V���v�ӨӪ��P�髬�����A���O���ڳ̪�b����`�ݨ쪺���y鵐�C�I�@�q�bWiki�W�����СA������͵w�C It breeds in southern Siberia across to northern China and northern Japan. It is migratory, wintering in northeast India, southern China and northern southeast Asia. It is a very rare wanderer to western Europe. �j�P�W�ӻ��N�O�|���ܻ������C �E�p�A�ﳾ���Ө��A�O�Q���ӶO��q���ơA�S�O�O�p�������A�Ӥp�������b�~���]�`�`�|�ܦ��O�H�������A��M�I�ʬO�Q���a�����C�Ӧb�����̡A�]���@���髬�b�p�������A�o�i�H���e�髬�j�W�n�X���������@�˭��V�X�d�����A�q�c�ަa���V�a�C ���ѱo���g�Ĩe�̪����_�A�H�ηQ���e�̮Ȧ檺���{�C �夤�ҿת��u�a�A�v�P�u���šv�A������ӻ��N�O�@�ӥi�H���Ѧw�����ϩҡA�H�Ψ}�n�����ӷ����a��C�γ\�夤���³��A�e�Q�n���u�O�ݬݥt�@�ӨS�ݹL���a��A�ӧڬ۫H�Ȧ檺�L�{�|��Ȧ檺���G�ӱo���N�q�C �Ӧܩ�ҥ�B�Ҫ��I�q�³����͡A�N�ͺA�Ǫ��[�I�ӬݡA�ʤֹ��鬡�ʪ��}�������A�L�j����������~��A�_�A�ܮe���|�ܦ����G���ͪ����\�C �m��A�`�n �ک~�M�X�G�䤣��ۤv���g��L���³��ӡA�ݨӧڤ]�ܩ������C�o�O�b1998-2000���H�������ᱽ�y�᪺�Ӥ��C �m�����\Ū�n
����������ۧ@�̳�����Tracking
�g�_2007/01/24-25
|
|
|
|
|
|
��r����v�Gmunch
���ɭԡA�`�O�|�J�W�@�ǯ��H�q��A�b�۹��M�~�A�άO�۹��X�W���U�A���H�����@�ت��A�A�@�ط���쪺���A�A�i�H�ۿ��̯��A�i�H�����ۡA�Ʀܬݨ��u�����\���C
ť�D�F�M�~�q�ª��V�����~�A�o���w���H�q�⪺�۵M���n�A�γ\�ޥ����¼��A�γ\�S����s��סA�o�b²�檺���v�����u��U�A���H���~�N�H��²�몺�����X�{�F�I �°귽�A���H���֮a�A�ΦN�L�u�ۤ@���S�@�����������s���q�A�]�\�W�M�~�����R�ӽo�A���O�o���۱M�~�W���u���y�S�C �m���ۡC�����s�K�D�n�A��O�°귽�����ۦb�İ_������w�A�V�C�Ƚ����t�۫�A�N�@�~�����ۦ�X���F�b�ʥF��P�����U�A�H���ۤ覡�q�������s�İ_���v�P�����A�b�L�R���P�����q�n���A���O�M�᪺�S�]�A���۶������{���{ģ�C
�m���ۡC�����s�K�D�n�M�褤�A�Хܡi�İ_��g�j�A�H���оİ_�D�A����N���ण�`�N�b�M�褤�A�t�@�컡���v�B�ۺq�����q��A���O�H�ٳ��Ѯv�������v�A�L��İ_���v�p�Ʈa�áA�������ʾİ_��v�O�s�u�@�A�o���M�°귽�X�@�A�λ��۪��覡���оİ_���v�A�b�C�H���ڭ����A�N�O�h�F�@�f�����C
���|�٥L�̬����n���A��⤣�W��ı�t�q��A��CD���֥[�WDVD���v���A���د��H�q�����y�O�A�o�O���H����߫�H�R�Aťť�ݩ�����s�W�̯u�����n���C ���w�����\�h�q�⪺�Ĥ@�i�M��A�`ı�o���O��ĭ���A�Ҧ������P�R���䤤�A���즨�W����A�����n�B����O�B���M�~�V���s���A�ٱo�Q��b�m�R�A�o���h��쪺�߱��C ����A�G�������°귽���Ĥ@�i�M��A��ĭ���A�Ӧ۪����s�����H���֡C �� ��������ۧ@�̳�����u�}���E�q���v�g�_2007/2/7 |
|
|
|
|
|
�@�̡G��֬�
�������աA���ճ����C �F���Z�R�A�ڰ��k誡C �F�����^�A�ڰ��ȶ��C �F�����o�A�ڰ��Ȩo�C
���� �k�G�u�Ĩ��ը��A�Ĩ��աA�b�Ѥ]�Ĥ���@�L���C �k�G�u���W���y�ۤs�A�ڪ�����w�L�ġC �@�@ �u���W���y�p�s�^�A�ڪ�����w���ˡC �@�@ �u���W���y�p�g�s�A�ڪ�����h�����C Cocklebur Fu-Shiang Chia Woman: Man: �Ӫ����դ��W�u�a�աv�Ρu�ϱa�ӡv�A���@�~�͡A�Q�u��A���T�����Z�ΡA��9-20�����A��L�ߧΦ���I�ΡA�⭱�K�Q��F�`3�L���A���t�e���W�h�����ΡC�����Y���A���͡A�ƦC���o�ΡF��a�զ�C�۪�ǵť͡F���h�`�c�n���C�G�L�`�A�ѵw�ƪ��`�c�ҥ]�Q�A�����ΦܧZ�ΡA��1-1.8�����A�|0.5-1.2�����A�K�Q��A�ò��ͨ�_���c��A����2����C�첣��ڬw�ܪF�ȡA�{������j���j�����ٰϡA�x�W���q�C���ު��m�B�]�`���C �a�լ��j�ɭԪ�����A�ĥ��]�อ��厼�A���u�ƦӤ֨��v�A�����a�W�H�a���潭�A�Φ~���p���ɪ��ϯ��C�j�N���k�`�I�t�����]�פf���^�b���a�Ķ��A�Y�u�������աA���ճ����v���N�C �a�ժG�꺡���˹_��A�`�����~���֤�ΤH���窫�ǥH�Ǽ��C���M����줣���a�աA�����b�j�N�ɴN�g�Ѭ��b�R��ӶǤJ�A�Y�m�ժ��ӡn�Ҥ��G�u�������H�X�ϤJ���A�J�V�]�Y�a�ա^�l�h��A�H��Ϥ�A�E�ܤ���C�v���Y�a�դS�١u�ϱa�ӡv���ѨӡC �a���c�ޤO�ξA���O�j�A���סu�n�_�E�L�A�s�C�Q�A�A�d�g��ۡA���a�h���v�A�{�w���ͤ���U�a�C�A��|��ͤl�A�G�Ϊ��p�j�N���k����չ��]�]���h�^�A�]���S�W�u���h��v�C�ؤl�����L����A�h�ֿi�ѡA�i�N���N��λ]�����ΡA�O�j�N�`�έ����C �a�դS�١u߭�v�A�p�q���̡r�u���w߭�H�իǤ��v�C�u���v����ԡA��̺ؤl������A���Q�����c��A�ΥH���p�H�F�P���B�����ΥH��g�l������ۤϡC�]���q�Ӫ��ѻ���r�K���۪L�~����Ҽ�I�T��s���ۧ@�m�ָg�Ӫ���Ų�n�^ |
|
|
|
|
|
|
|
���Ϊk�H�x�W���Ҹ�T��|�E���ҫH�U����|(�w)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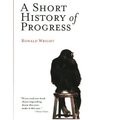 �@�U�~�e�A�Jù�����H����F���v���E���O�U�A���F�{�N���H�������C�o�Ƿ�������N�Q���j�۵M������Ǥ��A�i��ҿסu����v������G���B�u��B�A�~�B�����B���ݡB���|���h�B�F����´�A���l�u�C
�@�U�~�e�A�Jù�����H����F���v���E���O�U�A���F�{�N���H�������C�o�Ƿ�������N�Q���j�۵M������Ǥ��A�i��ҿסu����v������G���B�u��B�A�~�B�����B���ݡB���|���h�B�F����´�A���l�u�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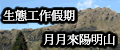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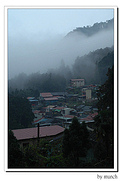 �Ҧ����q�A�L�ۦ�@���Ц��~�[�u���t�ۡA�@�H�X�G�d�w�@���A�ΥL�����H���b�����s������A�C�X�@���S�@�������s���q�A�۫ߤ������A�o�O�O���`�N�AĴ�p�q�c�ߴd�Y�B�r�A�N�N������a���İ_��A���ة��n���𦨫B���S�ʡA������@�k�H���߱��A�g�Ҽg�߳�����n�B�A�q�q�̥i�H�s�������s�İ_�����A�]�i�H�ݨ��o����H�q�⪺�߹ҡC
�Ҧ����q�A�L�ۦ�@���Ц��~�[�u���t�ۡA�@�H�X�G�d�w�@���A�ΥL�����H���b�����s������A�C�X�@���S�@�������s���q�A�۫ߤ������A�o�O�O���`�N�AĴ�p�q�c�ߴd�Y�B�r�A�N�N������a���İ_��A���ة��n���𦨫B���S�ʡA������@�k�H���߱��A�g�Ҽg�߳�����n�B�A�q�q�̥i�H�s�������s�İ_�����A�]�i�H�ݨ��o����H�q�⪺�߹ҡC �°귽�O�y���H�A�����v�O�]�ߤH�A�L�̦b�Q�h�~�e�A�e��Ө�����s�A�åB�b�İ_�}�A�L�̤��O��ͪ������s�H�A���O�o�O�R�۪����s��G�m�h�A��O�d�U�A�åB�@�q���ۡC
�°귽�O�y���H�A�����v�O�]�ߤH�A�L�̦b�Q�h�~�e�A�e��Ө�����s�A�åB�b�İ_�}�A�L�̤��O��ͪ������s�H�A���O�o�O�R�۪����s��G�m�h�A��O�d�U�A�åB�@�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