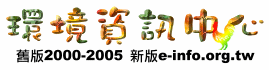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欄作家] 沒有獵人的狩獵文化 作者:黃怡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尤哈尼,在2000年8月12日的「生物多樣性與台灣原住民發展」研討會中,講了一個很好笑的笑話。他說,我們這片島嶼上受保護的獼猴,不但數量繁多,甚至聽傳不少獼猴都眼戴墨鏡、手持大哥大,是牠們從觀光客那兒搶到的。 此笑話當然全屬杜撰,卻很傳神地形容了原住民討厭漢人到國家公園一遊的心情,認為漢人帶來垃圾與噪音,除了更加濡染原住民向錢看齊的習氣,幾乎什麼也沒留下來。10年來各地原住民團體「向國家公園說不」的運動,因為原住民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已漸成氣候,像這樣的笑話現在公開得很,沒有人會認為它不具正當性。 然而尤哈尼在當天講的另一個笑話,卻有點讓人感覺困擾。他說,原住民最懂得尊重生物多樣性,你們看,原住民採收植物都是摘葉不拔株,而且,開獵槍打中一隻動物,鬨的一聲,必定跑掉10隻動物。這如果是在盛行動物權的國家,早被輿論大肆撻伐了,爭議點並不在相對於「動物權」是不是有所謂人類的「狩獵權」,而在於假如我們真要把「生物多樣性」當成個嚴肅的事題來談,探討任何動物得以生存及持續種群的可能,絕不能以這樣輕薄的態度,來替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脫罪。 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原住民覺醒行動,逐漸和保育運動槓上了,台灣如此,全球亦然。譬如2000年8月18日至20日在屏東縣霧台鄉舉行的「原住民狩獵面面觀」研討會,是原、漢族群首次針對狩獵政策,做公開對話。由於地理位置荒僻,霧台當地的魯凱族部落仍保持著相對完整的傳統獵場,農委會自1996年起,委託學術研究單位調查其狩獵生態,考慮應否擺脫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束縛,讓魯凱部落能夠規劃他們本身的職業狩獵,甚或保留部份可忍受獵捕量,開放給外人做運動狩獵。這使保育界人士不得不挺身而出,深怕主管機關為了選票等政治目的而貿然放行。 當我們在檢視這些所謂的狩獵生態調查報告時,會發現有些荒唐,因為它們往往顯示,某某區去年捕到多少山羌、長鬃山羊或野豬,和5年前、10年前相去不遠,故其繁殖能力甚強,足以復原種群數量云云。事實上,憑常識即可知,許多人為因素,都可能影響到狩獲數量,比方說,或許山羌的繁殖能力並不如某些學者預期,其種群數量確實在縮小中,但是基於市場需求殷切,獵人會更為特意去設計捕殺策略,以維持供量。 任何動物種群的絕對密度與相對密度,以及牠們的散布,都有時間因素,需要做較為長期的觀察、記錄與估算,除了這些空間與數量特徵之外,還要做遺傳特徵的敘述(譬如是否個頭越來越小或越大等等),以及種群內個體之間與其他物種之間,究竟存在什麼自然調節的現象。農委會委託的這類調查報告,大致說來都有重「狩獵」而輕「生態」的傾向,事實上,在種群統計學和種群成長模式都做不出來,甚至連生態小區的基本食物鏈資訊都缺乏的情況下,要談任何政策變遷都是「畫虎闌」。 台灣的生物多樣性報告一直無法出爐,也是同樣問題,基礎田野工作做得太少,有一些物種(動物與植物都有),研究者仍在引用日據時代日本學者的實證報告呢。野生動物雖然是可以再生的自然資源,即使沒有人獵捕,繁殖季節時的種群數量也是基本相等的,生得多,死得也多,原因在牠們所賴以維生的資源是恆定的,死亡原因包括饑餓、營養不良、天敵捕殺、疾病、意外等。霧台鄉狩獵生態研究中,對於原住民經常捕獲的山羌、長鬃山羊、山豬等,在死因方面幾乎全無調查,祇一味強調從狩獲數量看,大致沒有減少;另一方面,研究學者也從不針對野生動物的環境容納量,去估算野生動物的最大飽和數量。請問,他們「可忍受獵捕量」的數據是怎麼來的呢? 再說,任何原住民部落中,真正了解山林生態健康生態的獵人,已經比例偏低了。為什麼?因為原來從5、6歲就跟著長輩去狩獵的孩子,都到國民小學,然後是國民中學讀書了,依照他們的教育養成,反而比較容易適應都會生活。沒有傳統獵人,哪來的傳統狩獵文化?加以獵具的現代化與多樣化,使傳統的資源獵取方式改變太大,以及狩獲的消費者從原住民為主,轉為以漢人為主...,凡此等等,皆足以證明原住民狩獵文化的消亡是時勢所趨。 假如農委會意圖開放狩獵的這些地區,各動物種群數量穩定,一如某些很粗略的報告所呈示,那麼,更沒有必要進一步開放狩獵了,因為那表示該等區的物種在現存的狩獵程度下,彼此按比例繁殖,已達到一種相對的平衡狀態,也就是「頂級生態系統」,這豈不是台灣實施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理想階段嗎?有何必要以進一步開放狩獵來干擾它呢? 所以,或許獼猴多到有些戴上墨鏡、手持大哥大,還是我所樂見的,這總比被一群殺氣疼騰獵人在山林中誤殺要來得好多了。至少我們在生命倫理上比較說得過去。 站內轉載:http://news.ngo.org.tw/reviewer/huangyi/2001/re-huangyi01011001.ht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