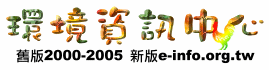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欄作家] 不只是農業 作者:賴偉傑 我對台灣農村問題資料讀得再多,可能都比不上一次去朋友老家的震撼:幾年前有一次跟他一起南下出差,順便彎去他家彰化竹塘鄉,他老家年輕人都跑了,田沒人要種,剩他臥病的祖母,唯一「經濟來源」是原來就留在老家的二伯,當濁水溪盜採砂石業者雇用的卡車司機,而在台北工作大伯,最近受傷回鄉下休養,多一雙筷子吃飯,反倒解決陪伴祖母的人力問題。這些巧合,一個工殤、一個盜採砂石,讓他們老家可以「人盡其才」,維持平穩。我一直忘不了那種令人絕望的感覺,這是真實的農村,但出路在那邊? 當時剛好立法院在審「農業發展條例」,但最引人注目的卻是「農地自由買賣與興建農舍」。我們有一連串的質疑:到底所謂的農地三等級的劃定依據及區位何在?到底該留下多少農地以為糧食基地?農地具有涵養水源生態功能的承載度為何?建立在農業生態系統上的鄉村及人文景觀會如何劇烈改變?保育用地範圍應如何劃定,維持多少比例,才真正具有保育的意義?重要農業用地、保育用地,農民獨自承擔生態保育重責大任,政府是否有符合公平正義的「生態銀行」補貼回饋機制? 然而農委會的政策說帖指出:「台灣農業面臨加入WTO的衝擊,應以知識為軸心,科技為手段,加速調整由數量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發展,將科技知識及文化知識附加於農產品,並且將之市場化及商品化,以提高農業的附加價值,提升競爭力。」這些美好的字眼,其實搭配農政單位後來只退守到「農地農用」政策,正是量身打造「農企業」的土壤,然而,以中小農為主的台灣農業,就成為在這一波「自由競爭」的型態下,產生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法則下的「被淘汰者」,「競爭力」成了農業指標,而其他的如農村互助網絡這種「社會性功能」沒法量計的,就成了農村首先破敗與解體的部分。 台灣的環境問題,其實就是一連串量化農漁業、量化土地的結果。因為當漁業和農業被換算為「產值」時,因為農漁村人口少,地偏僻,產值不多,所以「選票壓力應該比較少」,「只要回饋金給的比原先產值多,他們就該滿足的吧!」,於是多少農地和海岸,不斷為鄰避型、甚至是錯誤的建設所糟蹋。而進一步,更多資本市場的金融工具以及思維就進來了,於是土地債券化,或是農田可休耕竹科不能沒水的論調。 也因此,錯誤的環境與自然資源政策,其實是農漁業價值崩盤的開始,當什麼是以為用錢就可以解決的時候,基本上有再多以錢為唯一度量的善意,都只在加速撕裂農漁村、農漁民及其網絡與文化。 巡田路、巡水路,這般日常農活的作息,保持灌溉活水及其源頭,其實是最佳的生態巡守員;然而當官方的「農地釋出政策」大量徵收農田以作為公共設施用地,當有毒事業廢棄物濫倒、工業廢水污染,甚至蓋焚化爐垃圾場時,官方連串的「非農業」不當政策,悄悄扭曲了農村的價值,賠償金甚至爭取農地自由買賣,成為農村「便現」的捷徑。然而不熟悉的金融遊戲,讓農民或其子弟把變賣土地的現金快速散去,得不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而這只是農業問題的某一個面向,然而如果沒有真正到農村現場,更縝密的討論,更基進的互動,就會讓台灣的農村問題與出路,只簡化成當年所謂老農派立委「年金、農地自由買賣、補貼」。 兩年前農漁民十萬人上街頭,不管是為了農漁會的存廢,還是加入WTO之後台灣農漁業面臨衝擊,還是長期以來犧牲農業服務工業的積怨,對於來自四面八方走在台北街頭,皮膚黝黑、憨直誠懇的老農民老漁民,整個社會展現蒼白的人道感動,因為在車水馬龍、光鮮亮麗的都會區。那會讓你想起自己消失已久的靦靦與感恩,以及對汗水、泥土、大海搏鬥的悲愴影像。政治人物搶著表態永遠跟農漁民站在一起,輿論媒體也盡是感染了悲天憫人的語調。 但兩年過去,十萬人的場面與感動只成為農漁會信用部的護身符,農業問題仍然沒解決。這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同樣是農漁民的抗爭,卻從來只得到漠視、污名與輕蔑! 蘭嶼達悟人是漁民;金山、萬里、貢寮鄉民是漁民;雲林林內人、新竹竹北人是農民;林口鄉民是漁民以及農民;台南東山鄉民是農民;石門鄉民是農民:八里和淡水淡海人是漁民;宜蘭建蘭段人是農民,然而,當他們的家園、農田、柳丁園、漁場,被強制作為核廢料場、核電廠、焚化爐、焚化爐灰渣掩埋場、高爾夫球場、污水處理廠和廢土填海、建蘭段稻米良田上建掩埋場時,他們面對的是國家或財團的既定政策、專家最大卻錯誤百出的草率環評、鎮暴警察下強行動工。有多少政治人物和社會大眾會體諒這些「農民」和「漁民」被刨根的心情? 楊儒門的出現絕對不是偶然。 楊儒門放置白米炸彈及落網,又讓農業議題再度獲得社會關注。社運團體積極介入聲援,論述農業問題,並且與在地的農業第一線工作者合作,能不能拋離短暫的感動與軟性人道主義,扭轉目前農村基層相當主流的「年金、農地自由買賣、補貼」解決方案,帶往更基進的方向,值得所有關心台灣環境議題的朋友長期關注。 白米炸彈客事件,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聲援楊儒門,卻都一致地說「我們也覺得應該正視農民的困境」,但這不應該淪為最廉價、最便宜的口號。喊的滿天響的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有幸」,終究還要面臨「生存」問題,而生存不是只講農民、農業問題,而是整個「農村」被各種政策錯亂宰割的問題。因此,對每個社運團體來講,都是個嚴峻的考驗,考驗不在於要選邊支持楊儒門的行為與否,而是考驗著每個團體長期以來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是否流於片面,以及團體的主張是否能通過城鄉差距的檢驗,長久以來農漁村面臨的困境,需要什麼更細膩更在地的社會福利配套。楊儒門意外的給了每一個自詡為進步的社會團體「家庭作業」與機會,那就是必須共同面臨整個農業轉型或崩盤的威脅下,所連動的所有困局。 (2005-01-1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