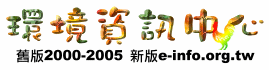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參與筆記 (下) 作者:林宜儒 (台灣環境行動網)
相同的事件也在之前準備會議上發生過,聯合國秘書處非但沒能以前車之鑑改善處理模式,反而重複演出這荒謬的劇本,不禁令人懷疑官方會議是否只是藉由這空間理由行排擠各國非政府組織及媒體之實,畢竟秘書處所採用的方式是讓國與國之間的非政府組織互相競爭,那由秘書處強行制定的名額,有感於此亂象絕非意外事件的認知,於是也有團體提出「No us(NGO delegates),No discussion」的訴求,並集結各國媒體(不論是否現場參與),廣泛傳播予全球各地。 會員國官方代表是不在限制名單之列,根據與會加拿大非政府組織代表指出,加拿大有60位企業代表技術轉變為官方代表,如果秘書處無法揪出是否其他國家代表,就應全面開放讓已註冊之各國非政府組織進入,否則若有惡霸企業以商逼政,代表弱勢之組織代表,將完全無法行監督之責。 我本來也很沮喪地想,這一天,會不會就這樣毀了?但看到各國草根運動的人士,那麼積極地,籌劃和遊說各種可行方案,其中又以女性為多數,希望和打從內心的敬佩油然而生,我不禁微笑,並利用機會遞上名片與當地連絡方式,表明合作的意願。另外有一則有趣的插曲是一位男性日裔美籍的法律教授,他和他帶領的一群大學生一直在我附近,也得以讓我們有些聊天的機會,當他知道我在美國讀書,對待我比較easy-going(卻對他的學生嚴格到上廁所都只能夠在規定時間全體行動),但免不了有些優越感(律師、大學教授、曾在聯合國擔任負責NGO事務要職),他說NGO需要的是真正懂得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運作及法規的人士替NGO代言,根據我過去在聯合國擔任負責NGO事務的經驗,NGO多為一堆自以為很有辦法的專家,雖然在各領域都發揮的淋漓盡致,卻無法和彼此在同一屋簷下心平氣和的交流,與其說力氣是用來對抗霸權,還不如說用來對抗其他NGO比較多。我還來不及回應,沒想到附近的一位來自加拿大已經為人權奮戰三、四十年的女士馬上回應著「我不這樣認為,只有將最真實的各種現象帶給官僚系統,才是NGO應該展現之魄力。如果什麼都得照政客那一套來執行才叫合宜的文明行徑,那未免太過窄化、也局限了所有可能的創造力。」她繼續回應,NGO當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的確是重要,但是NGO需要的的領導人才是能溝通協調,帶動組織的活力,絕不只是一些資訊資源豐富,而毫無整合效率的專家。 給政府部門的小箴言 NGO之所以為NGO,是因為有其專職議題與知識領域,絕非為行政單位之延伸,也不是因政府單位因敏感領域無法出面執行,而要NGO代勞。筆者發現,即使新政府一上任就提出了非政府組織工作之於台灣之重要性,各公務機關對民間組織之認識,相信用淺薄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更甭提及功能認定(recognition)了。 NGO不同於利益團體或自救組織在追求自己狹隘、局部的利益,而忽略了公共福祉,更應不斷培養世界公民之責任,進而與普世價值有對話空間,並建立對各式問題合理的對應措施,避免淪於絕望邊陲,徒有坐以待斃之遺憾。 雖然參與國際會議也不等於加入了國際組織,但是NGO絕對有運用此機會來檢視各政府(政治實體)對國際合作和國際承諾之第一手資料之參與必要,更應積極主動將人民的聲音傳播給有相同境遇之其他族群進行公共政策的倡導,尤其在直接參與的部份,由動悉政治運作脈絡,周邊運作模式,可以和與會者共建意義,進而重建台灣在健康促進議題之國際共鳴。之前在多次不算成功之準備會議,世界各國許多組織就已警覺,不能將此次地球高峰會視作對已傷痕累累之全球環境將產生極大變革的神話,更沒有人會說當加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台灣環境衛生與健康就不會有問題了。 而是將NGO以議題連結的主體性與機動性,與世界各國產生多層面的觸及與發展合作,再回頭不斷自省本土社會脈絡,尤其隱而未現之關鍵徵結。另一方面,在面對國際社會,我們也應不斷追索在哪一種情境條件下,提出台灣處境,跟著諮詢意見,台灣會得到重視與支持,並洞悉周遭互動模式,創造所有之前不曾預見的可能性,絕對不要故弄玄虛,也才能有與其他國家共同建構實質之互動意義,進而建立互利雙贏之國際認同。 ※若想瞭解整個會議報告紀錄摘要,請上網至 http://www.earthisland.org/wosh/ 原文發表於 TEAN 2002 約翰尼斯堡地球高峰會參與報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