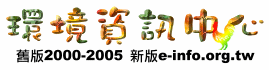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欄作家] 追求不朽 (上) 作者:賈福相 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往往是沒有意思的問題,譬如說:甚麼是愛?有沒有靈魂?有沒有神?玫瑰花為什麼好看?這些問題虛無縹緲,但人間如果沒有愛,沒有靈魂,沒有神(自然、天),沒有玫瑰,會是甚麼樣子? 讓我談談「活著的意思」,如果我現在說:「活著是為了追求快樂。」那麼大家可以離開了,隔靴搔癢嘛。中國的傳統是不講快樂的,快樂的追求來自西方、來自近代,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有下列名句:「人人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快樂的絕對權利。」這句話影響了近代人的行為。如果我們接受「追求快樂」是活著的意思,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是快樂呢?」快樂複雜而多樣,有的屬靈、有的屬肉,有的屬今生,有的屬千秋萬世,千秋萬世的快樂就是不朽。 不朽是人對時間的競爭,個體生命百年之後,都會腐朽,因為要朽,所以就追求不朽。古人的「生年不滿百,長懷十歲憂」,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人是屬於雙重國度,在動物的國度裡活著是為了生存,被慾和貪支持著,要食要色,要名要利,要洞房花燭、要金榜題名。但人也同時生活在理想的國度裡,想一些、做一些不切身、超現實、超生死的事,超現實、超生死就是不朽。戊戌政變的譚嗣同,慷慨就義,高唱:「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結束了33歲的青春,而贏得不朽。 我今年66歲,已經生活了三個階段:生死不保的階段,挨餓受凍的階段,和過度消費的階段。回首前塵,在每一個階段,我都常常避開「求生本能」的動物國度,跑到理想國去,夢著「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或「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這些理想國度的誘惑,把我的人生點綴成幽默、點綴成羅曼蒂克,而且有聲有色地活了過來。 我是一個學海洋生物的人,在國外教了一輩子書,做了一輩子研究,也做了15年大學行政。現在我要講三件小事,事雖小,但對我今日的生活,卻有深厚的意義。 第一件事是在三年半之前,我第一個孫子的誕生,那時我在香港科大教書,我的孫子在加拿大多倫多出生,4個月後,我才回去看他,抱在懷中,那一個暖暖的14磅小身體,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或笑、或哭、或睡、或醒,30分鐘就重溫了60年的親密經驗,在我孫子的表情中,我看到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妻子、我的女兒,就彷彿30多年前抱著我女兒那樣無條件的親近,把自己活著的意思,全部溶解在那一個小小的生命裡。 今天我已經有兩個孫兒、兩個孫女,他們使我快樂,使我生活充實,使我生活有新意。 第二件事,發生在一年前,當亞伯特大學的研究生院院長寫信告訴我,校董會已通過把「亞大海外博士生入學獎學金」,改名為賈福相獎學金,當時,我有種特別的感覺,這種感覺彷彿比我經驗過的快樂更深了一層,而且久久不退,兩個月前研究生院舉行了一次雞尾酒會,招恃新來的34位得獎的博士生(來自18個國家)和他(她)們的指導教授們,也請了我的家人。看到那一些陌生的新面孔,渴望著知識,年輕純潔,我的心靈跳躍擴大,把四海都容下了。人類本來是一個大家族,只有合作方可共生。在致辭的時候,感謝那幾杯葡萄酒,我講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話,有一位朋友在我耳旁悄悄地道賀:「賈福相,別人要捐幾百萬美元,或死後才有這種榮譽,你沒有錢,也沒有死,憑甚麼?」 憑甚麼,且不去管他,我沉思著的問題是:「我為什麼如此高興,是『浮名絆此身』嗎?」 第三件事是去年11月中,我的研究生,博士後和同行的朋友們在星期五港海洋研究所舉行了「賈福相榮休慶祝會」,與會者七十人,來自日本、香港、台灣、夏威夷、紐西蘭、美國和加拿大諸地。我的家人,除大女婿不克參加外,全來了。兩天兩夜漪歟盛哉,眼看著昔日的慘綠少年,長大成獨立學者,在台上滔滔侃侃,各談自己的研究。那天晚上,他們站成了長長陣線,一個接一個的傳遞著一個重數公斤的紙箱送到我手上,這時妻子再也不能忍受了,竟哭出了聲來。 箱子內是一隻銅鑄的海星,用六條足保護她的幼蟲,這是我博士論文的研究動物和題目,銅像由佛羅里達州一位名雕塑家製作,模型是我一位學生的妻子(一位勢術家)參考了標本和我的論文而創作的。塑像上有幾行小字:「海星的成功是由他第二代活著的幼蟲數量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是用他培養的人才的成功來決定。」 抱著這一隻銅鑄海星,想到39年前,我從星期五港開始,今天又回來,跑了一圈,對自己科研生活畫一個句點。可惜我的導師,弗奈爾先生,指引我走入海洋生物的天地,作古已15年了。看著我的學生,我的學生的學生,想到我的老師,四代同堂,那一種比快樂更深一層的感覺,又浸溶了我。 這三件小事、這三種經驗,日夜跟隨著我,揮之不去,它們帶給了我一種新意思。 如果一個人老是追求不朽,也相當無聊,做聖人是沒有意思的,也許根本沒有聖人,人是在朽與不朽之間徘徊,一來一往成了古今。風流人物如曹操者有時長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但隔幾天,又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唐朝的大詩人,杜甫也在勸自己「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無窮」就是不朽,「有限」就是人生。世界上許多大藝術家都在「及時行樂」,而始終念念不忘的又是「不朽之作」。這種行為當然是矛盾,但矛盾是必然,因為我們要切身的現實快樂,也要理想的不朽快樂,唯有兩者兼具,才是陰陽合德,才是完整。(待續) (2005-07-0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