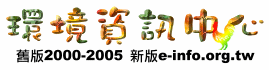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專欄作家] 閒讀書,讀閒書 (下) 作者:賈福相 莊生一笑 1976年林語堂先生病逝香港,1994年82歲。1994年是林語堂先生的百歲生日,正中書局出版了一系列書紀念這位大師。最近,朋友送我一本《回顧林語堂》,其中有他親朋好友的懷念文章,也刊出了林先生的11篇散文。 我的閒書中有好幾本是林語堂寫的,包括他的英譯《道德經》,但沒有一本讀完過。林先生的筆調我不太喜歡,但他的風采和主張卻是我所嚮往的。四十多年前我在江南流亡,17歲,手邊有兩本書,一是《范氏大代數》,一是林語堂的《高中開明英文》讀本。有許多早晨,我都站在長安鎮的運河岸上,流水潺潺,楊柳依依,伴我大聲地朗讀開明英文,有很多生字看不懂,又沒有字典,但也窮讀不歇。後來有人問我是怎麼學英文的,我常常講那一段運河岸上的故事。 林語堂與幽默分不開。六十多年了,很多人都在談幽默,但每個人對幽默都有不同的見解。在中學時我就讀過林先生的《論幽默》,文章容易懂,但抓不住重心,今天再讀一遍,仍是那種感覺。林先生說:「儒家斤斤拘執棺槨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住莊生一聲狂笑。」 幽默是林先生音譯的英文字:「Humor」。莊子不知道,林先生的文章中記載的那些中國歷史幽默人物也不知道。 英文「Humor」的定義也很籠統,大致說來幽默是一種語言、寫作或行動中的喜劇或玩笑素質,大而為一種溫文瀟灑的人生觀,或「無可無不可,恂恂如也」的態度。林先生說幽默要恬淡自適,要同情、要近情、要真情。 我認為幽默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要死愛面子,不要自我膨脹,有空就和自己開開玩笑。在這種心情下,真理的面目才會看得更清楚。有一次,子路沒有趕上隊,碰到一位鋤草的老人,就問:「你看見我的老師夫子嗎?」那位老人說:「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子路後來找到孔子,告訴了這件事,孔子說:「真是位了不起的隱者啊!快去請教。」那位老人不理世俗而直言,有點狂,有點狷,孔子挨了罵,知道罵得有理,不生氣,反而誇獎罵他的人,有些幽默,兩者都瀟灑。 最近讀冰心的《九旬文選》,有段寫她八十多歲的時候請朋友替她刻了枚「是為賊」的印章,這也是一種幽默的態度。 天下到處都有拍馬屁的人,天下到處都有惡意中傷的妄言者,這些都是怕上欺下巧言令色的小人,不瀟灑,也不幽默。 手頭剛好有本英文雜誌,其中有一則銘言:「處理生活和精神壓力的兩部曲:第一,不要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煩心;第二,天下事都是雞毛蒜皮!」 林語堂的小女兒相如,寫她父親:「他為詩詞感動而哭過好多次,後來我們一起念《紅樓夢》,有時她也哭得眼淚汪汪。」 莊子一聲狂笑,2300年,笑出了個真性情的林語堂。林氏的幽默也該擂鼓一番了。 湖邊閒情 台北的一個朋友寄給我一本梭羅的《湖濱散記》,孟祥森先生譯,桂冠圖書公司1993年版,這本書的原文我曾經讀過,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那時我在英國新堡大學教書,每周3次在校本部上課,其他時間就在得夫海洋研究所做實驗。研究所有6位博士生,其中與我最要好的是約翰.德利。他是劍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瘦長、害羞、沉默寡言,他父親經年在外經商,母親和他的妹妹住在離劍橋大學10里外的一家小農場,養雞、賽馬、養羊,園中種蔬菜和水果,除自己食用外,也在市場上出售。 一次我們在他家作客,我的雙生女兒才5歲,她們第一次看到擠羊奶,第一次看到母雞生蛋,覺得又新鮮又好奇。她們問我蛋是怎麼生的,我說是從雞屁股裡擠出來的。第二天早上吃炒雞蛋的時候,她們還在講雞屁股擠蛋的事,德利的家人覺得好笑,我妻子卻紅著臉替女兒們道歉。 黃昏我和約翰在湖邊散步,人陽西下了,彩霞滿天,農莊一片安詳。我憶起了在山東農莊的童年,就講了一首辛棄疾的詞給約翰聽。
明月別枝驚鵲, 即景即情,我們談田園,談自然,一直談到星辰滿天。約翰問我有沒有讀過梭羅,我說沒有,第二天他就給了我一本《湖濱散記》。 今天再讀梭羅的《湖濱散記》,更了解他當時的心情,而今天的自然世界,卻更是瘡痕累累了,年代不同,環境不同。我並不完全贊成梭氏「統治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我主張民選的政府,政府有權利收稅,有義務執行人民的立法,有責任保護人民的生命產。 我想任何一個崇尚自然的人,任何一個尊敬自然的人,都會憎惡戰爭,憎惡人間的不等,愛黔生(Emerson)如此,梭羅如此,甘地也如此。 文化是人類思想的紀錄,人不同,思想不同,文化才有東有西,有古有今,光華而燦爛,在歷史的滾滾大河中,過濾得更加雋永。 野鶴在空中飛翔,背馱著青天,飄飄千里;蜥蜴在地上爬行,半輩子還是肚皮底下那一片泥土。野鶴沒有資格嘲笑蜥蜴,蜥蜴也不需要替自己辯白。 沒有蛤膜的咕咕,百靈鳥的歌算甚麼? 沒有路邊的風鈴草,如火如荼的木棉花算甚麼? 忙人不笑閒者,閒人也不必沾沾自喜。閒就是怕,忙就是閒,閒情更真,閒事更忙。閒書更有意思。(2005-10-30)
【文章連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