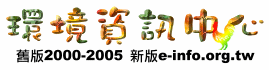
|
|
|
[自然與倫理] 生命之河:過去、現今、與未來(3)-自身與他人
作者:羅斯頓 (Holmes Rolston III) 一個人的倫理容量,可約略用其思及「我們」的幅度來估量。自我主義(Egoism)區分了一個孤立的「我」,在此界限外僅發現「他」與「她」;在這些無法化約的核心衝撞中可找到倫理的競爭,一對多,各自尋索其自身自明之利益。利他主義(Altruism)則不但看到「他人」,而且也是多數的(pluralistic),但卻出現了同情憐憫的能力。 同時超越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之後,「我」有時能認同「你」,因此產生了說出「我們」的可能性。由於我的自身已延伸至他人,因此倫理的關懷並不止於我自身(my skin),而是湧溢至我的同類(my kin)。倫理的成熟伴隨此種親裔感(sense of kinship)的擴展而來,而當它廣闊到能夠認知這種同在性(togetherness)時,自身便可浸融在團體生命中。 關懷他人,對自己有益 我們大部份人可以跨越過自身的追憶來分解我們的身份,再將之與父母孩子,乃至我們的族裔與民族等身份相結合。失去這個能力,我們在生物或文化上不會成功,如同我們前面說過的,因為我們無法充份的投注體現(projective)。 自我主義對個體自身生機的專注,具有一定程度的生物學與心理學上的合理性,但我們也必須認知到對於再生的預備。因此,我們有一個發展道德感的自然開端,不僅是捍衛自身,也包含所屬的群體。親切(kind)的兩種意涵──體貼的(considerate)與相關的(related),有著語源學上的同一根源。意識演化的進展,隨著親切的這兩種意涵之擴展,變得愈來愈少家族部落性,而是更加朝向普世性,最後達到普遍的道德意味;而且此種擴展的遠眺,不僅是全球的(global),更是歷代的(chronological)。 我們在此或許會注意到那遙遠的後人與遠方的族裔,與我們並無太多的「生物性連結」。在人類演化的漫長歲月中,我們的行為鮮少影響那些在時空上離我們遙遠的人,而天擇(natural selection)僅朝向那些與我們較接近者來形塑我們的行為。但現今我們的行為已有非常長效的影響,以致我們的確需要足以存活的倫理,因此擴大關懷眼界乃是我們生物性設計中所要求的。假若我們的倫理關懷可以演化到相稱於我們那既可幫助、亦可傷害、涵蓋全球、且跨越將來世代之駭人的現代能力,在這種道德發展中,我們無疑的會在舊的道德吊詭中找到新的真理──即關懷他人對自己的人格有益。 擴大自身,延伸所愛 在這生命水流中,早先的清楚區分開始消融。即使是自我主義者,也知道人必須對其未來的自身負有責任,因此他必須為預備退休而犧牲。人生的所有階段終將臨現,而「現今」並未特別受青睞。但對於遺留財產給予子女子孫的父母,對於保存土地的農夫,對於團體與機構的捐贈者,他們所珍惜在意的究竟是什麼? 我們若狹隘的定義自身(the self),我們會說是審慎變成了慈善。但如果我們認知到自身所取得其認同的更大而持久的群體,我們會重新將其最初看來是私人性的慈善,視為一種團體性的自我主義(corporate egoism),因為擴大的自身得以延伸與持續在其所愛的目標事物中。 若是如此,當此種親裔感(sense of kinship)在較少本性或民族性、較多倫理性的影響下,得到進一步擴展之後,將發生什麼事?我們不知道自我主義是否會消失、利他主義是否會留存,或是正好相反,如同我們不知水滴何時保存或消融在河流中。總是有人堅稱,任何共同的團體無非是捏造的,因其所有好處與任何利益最終都可以分析為個體所擁有,這些看法或多或少可視為是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的一種。但這是一種倫理的唯名論,不為近來的生物學與社會學理論所支持,現今的理論認為個體的好處與利益之構成,乃是相互依存於個人在其中被構成的較大遺傳性與社會性運動。 駐足思考,我是什麼? 當人駐足思考他所「擁有」的生命時,只有極度傲慢無知者會認為自己是真正「自造」(self-made)或「自全」(self-sufficient),那毋寧是近於捏造的孤獨的自身(lonesome self)。自然與文化的真理存在此自身的他者性之中(otherness of the self),因我們是在共享之流動中的參與者,在其中自身是整體的,但可剎那消融,其生而具有的自主性當被珍惜,但應負責任的、可回應的置放在其賴以支持的母體中。 古猶太教父的格言如此說:「我若不是為己,誰將為我?但我若僅是為己,我是什麼?」我們在此所跟隨連續不斷的思想與生命,讓我們將這個信念實行了一世代;若有誰發現窒礙難行,我們建議他們當行立在其先祖的墓前。 「愛」會去關心在我們離去之後發生了什麼。「愛」的生物性根基在於為人父母(parenting),但這種關懷終會在文化與倫理中成熟與結果。所有真正的愛會投注體現該生命中最為享受的層次,且因而在這當中他能夠走出自身,移轉性、繁衍性的投資自己於他人之中。若非如此,當一個人不關心在其局限的自身死亡之後將發生何事,那麼這只是假裝的、虛偽的愛,是停滯腐敗的自戀,對維繫生存毫無助益。 我們可獲得比現今所認為更為豐富的關於「共同公益」(commons)的概念,因我們不再有自身放大的自我,不只是扭搶著應共享的公益,而是自覺到切勿愚蠢貪心的只為找到死後的弔唁者,或只為我們所訴求的利益作自私的算計。自我可以在愛裡面,活在我們所讚揚的共同公益中,而處於戰鬥心態者則只能活在謹慎恐懼中。那些加入此集體生命水流的人,可以在地球所能載負的容量中找到新的意義。
【文章連載】 本文譯自:羅斯頓教授所著《哲學走向野性》(Philosophy Gone Wild),61-71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