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作者:詹家龍(台灣蝴蝶保育學會研究員)、楊平世(台灣大學昆蟲系教授)
蝴蝶在人類眼中,似是一群飛不過滄海的柔弱生命,但事實並非如此。一類叫斑蝶Danainae的蝴蝶,不僅會像候鳥般隨著季節變換南北遷移,有的更能夠輕易飛越海洋,甚至會形成舉世罕見的「越冬型蝴蝶谷」。《青斑蝶遷徙之謎》一書的主角青斑蝶,便是這類堪稱「蝴蝶旅行家」族類中的佼佼者。
日本自1980年代開始針對青斑蝶進行「標識再捕法」的研究後發現,青斑蝶會在每年春夏之際,從日本南西諸島往北遷移至日本的九州、四國、本州甚至北海道,秋天則會往南遷移至日本南西諸島。由於日本南西諸島位置最近距台灣不過近百公里,於是開始有人提出青斑蝶往返台灣、日本的可能性。直到2000年6月19日,一隻台灣大學昆蟲系研究生李信德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頂標上「1032C NTU」的青斑蝶,12天後在日本九州鹿兒島揖宿被日人中峰浩司捕獲後,終於證實了這項說法;隔年11月25日,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許國聖與林文信在台東縣達仁鄉與屏東縣獅子鄉交界的壽卡山區,捕捉到一隻來自日本大阪、後翅標記有「SOA 118」的雄青斑蝶,兩地的直線距離更長達2,035公里。 自此之後,不僅日本人開始注意青斑蝶,台灣人也對這些會飛到日本的蝴蝶感到相當好奇。由佐藤英治所寫的《青斑蝶遷徙之謎》在台灣的出版,則讓我們得以一窺這看似弱不禁風的生物,其小小軀體內隱藏著的巨大能量的祕密。和大多數外文自然生態書籍中譯本不同的是,《青斑蝶遷徙之謎》講的雖是日本的青斑蝶,但由於其和台灣的青斑蝶隸屬同一亞種,所以書中描述的生態現象,也同樣會在台灣的山林裡上演。走進中低海拔森林,你可以在牛嬭菜(Marsdenia formosana)的寬大葉片上,找到青斑蝶幼蟲所留下的特殊取食印記「環狀食痕」;每年初夏,大屯山頂的青斑蝶大發生,比起鹿兒島縣種子島的盛況,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多加留意,有一天你也可能會發現一隻上面寫著日文編號的蝴蝶。 《青斑蝶遷徙之謎》作者佐藤英治也在書中提出的一些未解的生態之謎,或許有些答案就隱藏在台灣的山林裡,例如:青斑蝶在南方形成越冬集團的可能性?根據筆者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目前已知越冬蝶谷內調查到的青斑蝶數量只有個位數記錄,至於少數引用他人文獻用來舉證東部存在青斑蝶的越冬谷,則純粹是將小紋青斑蝶類(Tirumala spp.)及琉球青斑蝶(Ideopsis similis)類越冬集團的泛稱「青斑蝶類」,誤以為是單一物種青斑蝶(Parantica sita)所致。但這並不代表青斑蝶越冬集團沒有存在的可能性,因為筆者曾在東部一兩個特定山谷內發現數十隻青斑蝶的近緣種小青斑蝶(Parantica swinhoei)的冬季棲息地,或許青斑蝶也存在著類似情況也未可知。 最早進行斑蝶遷移生態研究的加拿大動物學家Frederick Urquhart(1919-2002)自1937年便開始嘗試用標記方式解開帝王斑蝶(Danaus plexippus)的遷移之謎,一直到1975年終於接獲同事Ken and Cathy Brugger的通報,在墨西哥市近郊約240公里處的Neovolcanic Plateau,發現上百萬隻帝王斑蝶越冬地點;日本的青斑蝶遷移研究至今也已超過20年,並在近年證實牠們會遠渡重洋來到台灣。 相較之下,和墨西哥「帝王蝶谷」並列為世界二大越冬蝶谷的台灣「紫蝶幽谷」遷移生態研究的進展卻相對緩慢,自從蝴蝶專家陳維壽在1970年代披露紫蝶幽谷存在後,長期以來關於這些群聚南台灣茂林等地的越冬斑蝶究竟來自何處,一直沒有進行相關的標放研究。為解開這些斑蝶遷移之謎,台灣蝴蝶保育學會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補助下,近年來開始訓練紫蝶保育志工進行標放研究,並在社會各界大力協助下,才逐漸描繪出台灣產斑蝶類之遷移路線。 由此可知,不論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或台灣,大量志工的投入仍是解開蝴蝶遷移之謎的最有效方法。衷心期待《青斑蝶遷徙之謎》在台灣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蝴蝶效應」,一般社會大眾除可接受專業訓練加入標放志工行列外,平時在野外踏青能對各種斑蝶多加留意,一發現有號碼的蝴蝶,請儘量以攝影的方式紀錄,並與台灣蝴蝶保育學會聯繫。
只要有興趣,您也可以參與蝴蝶標放! 2000年7月間,一隻由李信德於2000年6月19日李信德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登山車道所標放的青斑蝶在日本被捕捉,這隻青斑蝶能在14天後遠渡重洋飛往1,140公里外的日本九州鹿兒島,揭開了台、日青斑蝶確實在交流的祕密,也拉近了台、日蝶類學者間的交流。 如今,李信德在2000-2003年間標放的青斑蝶共有3隻飛往日本,2001年在日本本州奈良標放的青斑蝶也首次飛抵台東山區;之後陸續又有3隻在日本標放的青斑蝶飛抵台灣,證實台、日間青斑蝶確在「雙向移動」,林唯潁也曾就採自日本及台灣各地的青斑蝶分析DNA組成,發現台、日不同地區青斑蝶確有不同程度基因交流現象。 日本於1980年代就開始進行青斑蝶的標放研究,發現青斑蝶在日本各列島間存在移棲的現象;如今,標放青斑蝶幾乎已成為日本愛蝶人的「全民運動」,這項活動及青斑蝶移棲之謎,在佐藤英治的《青斑蝶遷徙之謎》中有詳盡又生動的描述,台灣的愛蝶人不妨細細品味。台灣在陽明山國家公園所做的青斑蝶標放,早在1989年開始,當時只想了解為什麼每年5-7月青斑蝶類會在澤蘭群集?究竟有多少種斑蝶會出現在澤蘭花上?群聚結構如何?大、小青斑蝶的族群數量和比例……等等,當然也包括青斑蝶的飛翔距離、壽命,雌雄性比及其和植物間之關係。根據這些資訊,這幾年來陽明山國家公園每年一到青斑蝶大發生的季節,便舉辦大型賞青斑蝶活動,也發動關心蝴蝶及生態的朋友、家庭進行標放青斑蝶活動;可惜的是,這個活動不像日本那樣具有持續性和研究性,如果我們能發動愛蝶人在這段期間組織進行標放及追蹤活動,相信也能帶動蝶類研究氛圍,更能對蝶類及生態保育有更大的助益。但願《青斑蝶遷徙之謎》的出版,能給愛蝶人及主管國家公園的朋友們更大的啟示。 從事生態保育研究及推廣工作多年,深感必須結合更多熱心的行動派民眾,政府對於保育政策制定及執行的熱忱,也還有更大的努力空間。為什麼日本能?透過《青斑蝶遷徙之謎》的介紹,也許讀者們能找到答案。
|
|
|
|
|
|
文字/攝影:陳秀竹(金門國家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中山林遊客中山旁的山茶花,在去(2006)年11月30日中午,一隻漂亮的蝴蝶來訪花吸蜜,意外被拍入鏡頭,經向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徐堉峰教授請教,竟然是金門的新紀錄種艷粉蝶(Delias
pasithoe),又叫紅肩粉蝶。
徐堉峰教授於2004年曾與呂志堅、羅尹廷老師共同為金管處編撰《金門常見昆蟲》,徐教授在書中所說,鱗翅目的昆蟲,即俗稱的蝶、蛾類,因其主要的特徵是翅膀及肩上都覆蓋著鱗片,裡面包含的化學成分及表面的物理結構,都可以形成各式各樣的色彩、花紋及光芒,尤其是蝴蝶,因此成為人們喜愛的生物之一。
豔粉蝶屬於粉蝶科,通常給人色彩素淡、體型中小型的印象,粉蝶的頭部多有發達的下唇鬚、觸角末端膨大明顯,成蝶喜歡吸食花蜜,腐爛的水果及礦鹽水對牠們也很有吸引力。金門國家公園中山林園區花木扶疏,雖然進入冬季,但園區內的聖誕紅、紅粉撲花、美洲合歡、琴葉櫻、金露花、九重葛、鵝掌藤等多種植物花正盛開,常常吸引許多美麗的蝴蝶在花前翩翩起舞,或是停棲吸食花蜜,非常精彩! |
|
|
|
|
|
作者:溫于璇、孫秀如(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諦聽人與大地的對話
在十一月的玉米田裡製造音樂的風是匆忙的。 在閱讀完上述的文字摘錄時,以為這《沙郡年記》會是描繪自然景象的文學書籍,實際上也就像它的中譯本導讀所述:「這是一本很難加以簡單歸類的書,因它橫跨了生態、哲學、文學、歷史等範疇,既是美文,也是經典,如此嚴肅卻又那樣清淡流暢。」介紹到此,免不了令人好奇,這究竟是一本怎樣的經典作品? 《沙郡年記》分為4部分,第一部分以「沙郡歲月」帶出一年12個月份的四季素描;接著則以「地景的特質」勾勒出奧祕的自然美景;第三個部分「鄉野的情趣」,敘述作者生涯中幾個不同地方的經驗插曲,告誡著自然資源保護的意義;最後,「消失的野地」則以哲學性的文章,為土地倫理發聲。 1948年,李奧帕德(Aldo Leopold;或譯為李奧波)完成《沙郡年記》的手稿,不單純寫些花花草草的故事,更可以從一棵枯木的年輪,讀出一個世代的歷史與變化;從一群雁的飛過,道出世界無疆界的事實,大力尊崇「自然」這一本生命之書,提醒著人們要向自然學習。透過李奧帕德對於自然生態長期的觀察與細微的互動,提出了建立土地倫理,重建一套人與土地相處的模式,這個論述與主張也使李奧帕德在近代有了「環境保育之父」的名號;然而從《沙郡年記》完成至今,將近60年的歲月中,和我們共同生存在這個地球上的生物們,仍舊以極快的速度在滅絕中。野地的減少與消失、都市的發展與擴張,到底讓我們的生命缺少了什麼? 「休息!帶頭的鋸木者大喊,於是我們停下來喘一口氣。」 多久沒停下腳步去看看路邊的小花?又有多久沒聽聽自然的聲音?隨著《沙郡年記》,讓李奧帕德如詩般流暢的文筆,與對自然深刻的體驗,帶領我們重新看待生命,找回自然界的生態平衡。 李奧帕德的生命在本書完成後一年停止,但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影響,永不停格。
【相關連結】
【延伸閱讀】
◎有關綠色學苑的詳細活動訊息與報名方式,請見http://e-info.org.tw/node/19207。 |
|
|
|
|
|
譯者:賈福相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彎曲的樹 南方有棵彎曲的樹,野葡萄攀附著, 南方有棵彎曲的樹,野葡萄覆蓋著, 南方有棵彎曲的樹,野葡萄環繞著,
Crooked Tree
Translated by Fu-Shiang Chia
Wild grapes climb a southern crooked tree. Wild grapes cover a southern crooked tree. Wild grapes surround a southern crooked tree. 木質藤本植物葛藟又名「野葡萄」或「光葉葡萄」,嫩枝有絨毛。葉卿形至三角狀卵形,長4-10公分,寬3-8公分,先端漸尖,基部心形或近截形,表面光滑,背面沿葉脈長有柔毛;葉緣為不規則狀齒牙緣。圓錐花序,花軸被白色絲狀毛;花黃綠色。漿果球形,徑0.6-0.7公分,黑色。從韓國、日本、中國(華北、長江流域)以至中南半島均有分布,包括台灣在內。 葛藟枝有卷鬚,常攀附樹枝並往上蔓生至樹冠,因此才會在彎曲的枝枒上「纍之」、「荒之」、「縈之」,或在河邊濕地上蔓延生長,覆蓋整段河岸或整片濕地。葛藟之葉、果實均竹杏葡萄相似,只是形狀較小。果實成熟時青黑微赤,可供食用,但宲道酸而不美,古人採集可能泰半用以釀酒,少部分作為果蔬用。直至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帶回葡萄後,野葡萄的原來功用才由葡萄取代。 〈王風•葛藟〉和〈大雅•旱麓〉所提到的葛藟都是本植物。而〈周南•樛木〉說樹枝彎曲下垂,所以葛藟得以附著其上而生,比喻婦人依靠夫家,或者眾妾依附后妃。此外,《山海經》〈中山經〉提到「畢山其上多櫐」,文中的「櫐」,也是野葡萄。(本段植物解說文字摘錄自林業試驗所潘富俊研究員著作《詩經植物圖鑑》) |
|
|
|
|
|
|
|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信託基金會(籌) |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中山林遊客中山旁的山茶花,在去(2006)年11月30日中午,一隻漂亮的蝴蝶來訪花吸蜜,意外被拍入鏡頭,經向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徐堉峰教授請教,竟然是金門的新紀錄種艷粉蝶(Delias
pasithoe),又叫紅肩粉蝶。豔粉蝶並不是台灣特有的,而是分布在中國華南的亞種,如此的發現可說是金門的新記錄,牠的幼蟲以各種的桑寄生為食,生態很有趣!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中山林遊客中山旁的山茶花,在去(2006)年11月30日中午,一隻漂亮的蝴蝶來訪花吸蜜,意外被拍入鏡頭,經向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徐堉峰教授請教,竟然是金門的新紀錄種艷粉蝶(Delias
pasithoe),又叫紅肩粉蝶。豔粉蝶並不是台灣特有的,而是分布在中國華南的亞種,如此的發現可說是金門的新記錄,牠的幼蟲以各種的桑寄生為食,生態很有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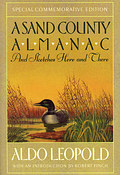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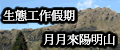



 豔粉蝶並不是台灣特有的,而是分布在中國華南的亞種,如此的發現可說是金門的新記錄,牠的幼蟲以各種的桑寄生為食,生態很有趣!根據台灣省立博物館出版,由趙力、王效岳共同所編撰的《中國鱗翅目》的描述,豔粉蝶分布於中國的雲南、廣東、廣西、海南島、四川及福建、台灣,另外在不丹、尼泊爾、印度、緬甸、泰國、越南、寮國、柬埔寨、印尼、菲律賓等國廣為分布,最北可達極圈附近,海拔可高達5,000公尺。
豔粉蝶並不是台灣特有的,而是分布在中國華南的亞種,如此的發現可說是金門的新記錄,牠的幼蟲以各種的桑寄生為食,生態很有趣!根據台灣省立博物館出版,由趙力、王效岳共同所編撰的《中國鱗翅目》的描述,豔粉蝶分布於中國的雲南、廣東、廣西、海南島、四川及福建、台灣,另外在不丹、尼泊爾、印度、緬甸、泰國、越南、寮國、柬埔寨、印尼、菲律賓等國廣為分布,最北可達極圈附近,海拔可高達5,000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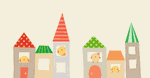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綠色學苑開課囉!本書為第四次聚會分享主題。希望看完這篇書介後,也會讓您愛上這本書,並且來綠色學苑裡分享您的感動與想法囉~~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綠色學苑開課囉!本書為第四次聚會分享主題。希望看完這篇書介後,也會讓您愛上這本書,並且來綠色學苑裡分享您的感動與想法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