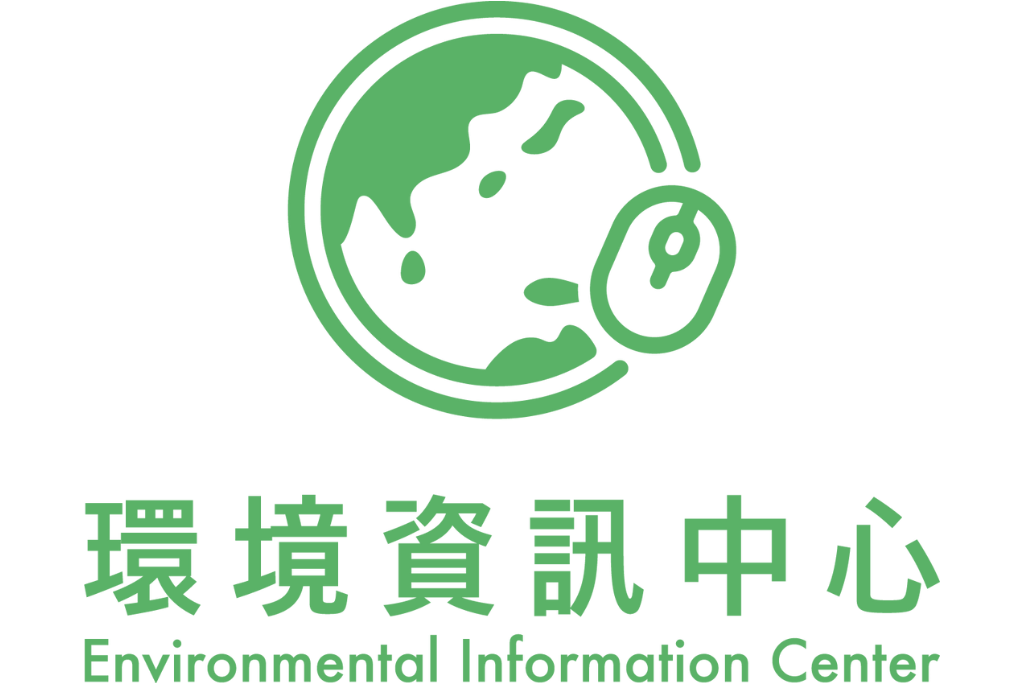國道五號高架在兩山間的天空穿過,車流呼嘯,對於大多數的台北人來說,坪林這個40分鐘台北車程可及的地方,比花東更陌生,更遙遠。
由於位於翡翠水庫集水區,坪林開發設限,當劉克襄讚揚當地的天然環境,75歲的住民劉媽媽忍不住說,坪林被犧牲了。國道開路以後呢?弔詭的是,坪林自此成為一個容易路過,而不易停留的地方,住民流向台北,觀光客流向宜花。開路讓台北和財團以其雄厚的財力,不是拉走人力資源,就是掠奪土地。鄰近的宜花興起假農舍和農地炒地大戰,桃園山區因開發以至水土流失,面臨死亡的石門水庫不時限水。

感覺會有龍貓出來的森林。攝影:莊惠詮。圖片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
以地方為優先的價值和力量
當財團和在地人以自由市場的機制合力出賣家鄉的好山好水,這不也是一種犧牲,又或邊緣化下的自我剝削?不開發不表示政府和財團就是好心,在以台北為中心的思維下,用水安全的保育是重要的,但被保育和被限制的卻是坪林,所以應該這麼說,只要以台北市為中心思考,所謂開發和保育何者重要根本不是問題,只有偏鄉才被迫要做這種爭論和取捨,只是剝奪的形式不同。於是問題的關鍵就不是保育或開發,而在於是否我們可以發展出一種以地方為優先的價值和力量,以抵擋政客結合商業資本出賣鄉土?
在保護區限制下,若不想傷害土地以求提高產量,那麼提高茶品價值以達到經濟效益就是關鍵,目前坪林約有25%的茶園屬有機栽培,相較於全台不到1%,顯得鶴立雞群。然而經濟效益的迷思是一個緊箍咒,市場價格並不等於社區價值,我們還是要面對許多價值無法被直接換算成價格的情況。
漁光國小 體制內的森林小學
我體驗到多年前蘭嶼小禎老師的說法,新北市山區比蘭嶼學校更偏鄉,50年前漁光國小有140人以上,現在只12個學生,鴻志老師將劣勢轉化為優勢,進行小班教學,以校園農場培養知識、執行力和品格,讓漁光儼然就是體制內的森林小學。這樣的教學創新讓鴻志老師屢獲教育獎項,而努力換來的卻是降級為分班,連分校都不是,鴻志老師落寞的說。
以德國的經驗來說,當地社區決定要保留農村風光做為先決價值時,願意務農者可以得到補貼,日本則嚴格要求農地農用。鴻志老師不只提供當地農民子女教育機會,讓農民安心居留,他開發的遊學團又為當地旅遊業注入商機,這種教學模式正在全台百花齊放,而這些卻不會反映在教育局的「經濟效益」。並非教育事業不用經濟考量,而是它們需要被換算成整體價值來理解。當政府可以給財團眾多減稅優惠和污染特權,達到外部化成本時,經濟效益的說法就更顯虛偽。

左,漁光國小的菜園;右:準備進行室內萎凋的茶葉。
小而美的在地經濟、環境和文化
多雲的月夜,星光寂寂,我們聊著數十年前在地經濟圈的故事,趕鴨人讓鴨群由宜蘭往北逐稻遊牧,鴨子來到坪林時剛好長大賣出,外地商人來到山區販賣商品,在沒有飯館的山區由劉媽媽家庭招待;藥商把藥袋掛在牆上,過往的無人商店;山上漂下剛新筏的木頭;河裡魚光閃閃,正是漁光之名的由來。若不是身在坪林,我還以為是倪齊民筆下中國豐饒的《北大荒》,140多個漁光孩子在其中學習和生活。
這些事提供了重要的思維,若我們能以在地為中心做出永續發展的考量,讓在地的經濟、環境和文化,形成小而美的自我負責系統,當開發和保育自我回饋時,就有機會在整體價值與市場價格間找到平衡,近來司馬庫斯部落決議遊客減半,銅門部落要求遊客步行進入,這些對開發的限縮都是由相對不那麼富裕的群體完成,他們比不用負責的都市資本更能認清價格的代價,並以整體價值衡量和行動。環境保育若要有穩固的守護結構,積極目標也許就不只是單向度的抵抗破壞,而是朝向協助建立「結構性支持的環境」,讓地方更易於建立自我負責的社會生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