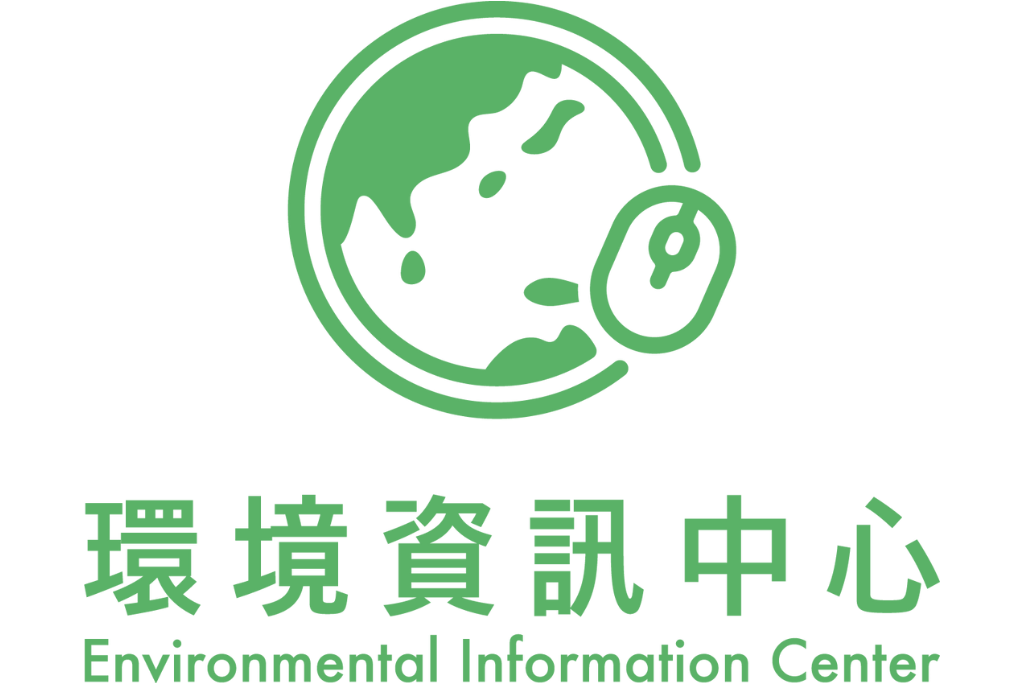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兩高)的新野生動物刑事案件司法解釋,意在對輕微情節提供司法救濟,卻被認為可能使執法難以操作

6年前,深圳青年王鵬因售賣數隻繁殖的鸚鵡而被判刑5年,成為轟動一時的「深圳鸚鵡案」。該判決的法律依據認為人工繁殖的鸚鵡屬於中國《刑法》中「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所指的「珍貴、瀕危」動物,受到各方質疑不合情理。
這份20條的解釋對涉及野生動物案件的定罪量刑做出指導,要求在公訴和審判實踐中考慮涉案動物是否為人工繁殖、物種的人工繁殖現狀、野外瀕危程度等情節,區分情節輕重,拉大兩者定罪量刑的差距。部分「輕微情節」將被免予起訴和處罰,或是直接不作為犯罪處理。
這份看起來更加「合情」的司法解釋在受到部分法律界人士和動物養殖戶歡迎的同時,也引發了關於這種「從輕發落」是否會帶來動保困境的擔憂。
「不合情理」的判決
在「鸚鵡案」中,王鵬因擁有和售賣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一和二(等同於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的鸚鵡而被以「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王鵬不服上訴,二審辯護人以人工繁殖動物不應作為野生動物為由作無罪辯護。
2018年,二審法院承認出售人工繁殖動物社會危害性小於出售野生個體,但仍根據最高法2000年《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2000動物犯罪解釋」),認為《刑法》所說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殖個體,因此減刑但不除罪,破例將刑期減至2年,低於法定最低刑——5年。
判決一出,大量輿論認為它機械地將人工繁殖個體等同於野外種群,是違背公眾一般認知的機械司法的典型。刑法學者羅翔在二審落槌後撰文表示這依然是一個錯誤的判決,因為當事人王鵬並不知道人工繁殖動物在《刑法》上屬於野生動物,因此「不知者不罪」。連《人民日報》都發文指出是法律普及的不足導致王鵬在不知中觸犯法律,也讓公眾覺得判決不合情理。

王鵬案二審辯護律師斯偉江和徐昕看到了此案的標誌性。在2018年二審宣判後,他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交建議,要求對「2000年動物犯罪解釋」進行審查,並獲得了回覆。覆函中告知,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已啟動了新的野生動植物資源犯罪司法解釋制訂工作,「擬明確規定對於涉案動物係人工繁殖的,要體現從寬立場。」
4年後,這份司法解釋問世。王鵬案和諸多類似案件的影子在其中浮現。在與此次司法解釋配合發布的「答記者問」中,「兩高」相關負責人強調對涉及野生動物案件的定罪量刑須「確保符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它特別舉了「江西鸚鵡案」中的費氏牡丹鸚鵡作為例子,稱該物種雖被列入CITES附錄二,但在中國養殖技術成熟,卻因為「歷史原因」普遍證件不全。他們提出對於此類案件,「追究刑事責任應當特別慎重,要重在通過完善相關行政管理加以解決」。
人工繁殖:被網開一面的痼疾
對新司法解釋的公眾反應呈現出分化。一方面,是一些曾代理相關案件的律師和一些野生動物養殖戶對此表示歡迎。有律師對媒體表示新司法解釋將涉及人工繁殖個體和野外個體的案件區分對待「是一種進步」,有養殖戶說《解釋》的頒布令他們激動,「彷彿迎來了春天」,王鵬則告訴記者,《解釋》的頒布讓他的「犧牲」有了意義。
與此同時,它卻引發了保護工作者和一線執法者的擔憂。擔憂來自兩方面:
第一,它提出以涉案野生動物或其製品的貨幣價值高低來區分情節嚴重程度,而不再如過去那樣以涉案動物數量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
它設置了根據不同情形最低一萬或兩萬元的入刑起點,這意味著涉及「低價值」動物的案件,將不會再出現「一隻入刑」的情況。在兩萬元的入刑起點之上,它還設置了兩萬到20萬元(情節較輕)、20萬至200萬元,以及200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三個等級,並設定了減刑情節。如果涉案動物價值超過兩萬元但低於20萬,根據本次釋法,只要行為人具有未造成動物死亡、全部退贓退賠、有悔罪表現等從輕情節,依然可以不被起訴、免於刑事處罰,甚至不作為犯罪處理。根據國家林業局2017年《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價值評估方法》,4隻小熊貓、19隻獼猴、39條眼鏡蛇的評估價值都不滿20萬,以上動物都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因此,有動保志願者撰文表示擔心許多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犯罪行為實際都會「降檔量刑」。
第二,新司法解釋宣布廢除「2000年動物犯罪解釋」,區別對待涉及人工繁殖野生動物與來自野外的野生動物的案件,提出涉案動物被列入「人工繁殖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和人工繁殖技術成熟、已成規模,被作為寵物買賣、運輸的案件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如需追究刑事責任的則從寬處理。
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韋凱雯(Amanda Whitfort)告訴中外對話:「本次釋法區分涉及人工繁殖和野外動物案件的基礎是認為買賣人工繁殖的野生動物不會影響野外種群及其生態系統。但是,很多野外獵捕的動物恰恰是打著人工繁殖的幌子進入市場的。」她認為,不再把對據稱是人工繁殖瀕危物種的貿易、持有和使用作為刑事案件,可能會加劇世界範圍的盜獵和走私問題,鼓勵非法販賣者繼續犯法。
一位從業超過30年的森林公安民警告訴告訴中外對話,本次司法解釋將證明涉案動物是人工繁殖還是野外獵捕的舉證責任重心轉移到了公安和檢察機關。在過去,是犯罪嫌疑人需要出示涉案動物的人工繁殖許可證和專用標識來證明動物為人工繁殖,從而為自己脫罪,而今後,公安和檢察機關必須證明動物來自野外獵捕才能定罪。
他表示,這給基層野生動物執法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因為目前沒有任何鑑定技術可以準確區分野外和人工繁殖個體。他舉例說:「比如我看到有人提了一隻被打死的白鷳下山,上去問他白鷳是哪裡來的。對方說是自己養的,飛到山上去了,他把它打死拿下來,我們就基本拿他沒辦法。就算有目擊者證明親眼看到他打野生白鷳,或有人證明他家從來沒有養過白鷳,也難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如果是跨省大批量非法販運野生動物,要追究刑事責任就更難了。」他預計,未來大量案件將因為公安機關無法證明涉案動物是野外個體而不了了之。他補充道:「辦案者可能會畏懼接手這樣的案子。」
雖然不再追究刑事責任,但相關案件可能從此被移送給林業與草原、市場監督、漁政部門,成為行政執法的對象,即所謂「刑行銜接」。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八條,繁殖列入人工繁殖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物種,應取得人工繁殖許可證和專用標識,沒有這兩者,依然應該予以行政處罰。但是這位民警表示,現存的大量證照齊全的養殖場可以用來「洗白」非法獵捕的野外個體,讓行政執法也舉步維艱。
比如山羌是一種極為敏感的動物,在人工環境下很難繁殖後代。他調查過省內所有的山羌養殖場,發現沒有一家養殖成功。「你辦一個表面上合法的養殖場,然後通過不負責任的管理機構給你發放專用標識,你就坐地收購獵捕來的山羌,不斷收不斷賣。」這些養殖場事實上的功能是「洗白」來自盜獵盜捕的野外個體。他又以蛇為例,他曾發現養蛇場在繁殖季節收購野生懷卵母蛇,用繁殖箱孵化小蛇作為「人工繁殖個體」出售的現象非常普遍。「當你看到養蛇場大量存在,你就不寒而慄。」
逐步擴大的「人工繁殖」邊界
而關於何謂「人工繁殖技術成熟、已成規模」,目前並無正式文件界定。2003年國家林業局曾發布《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梅花鹿等54種陸生野生動物名單》,此後最高法曾宣布名單上的動物不屬於《刑法》規定的犯罪對象。但這份名單已於2012年廢止,儘管此後它依然被部分司法機關用於審判實踐,作為減輕處罰或做無罪判決的依據。
國家林草局辦公室執法監督處處長汶哲的一篇文章認為,新司法解釋實施後,這個問題將成為涉及人工繁殖野生動物案件的爭議焦點,「面對即將到來的司法機關諮詢、當事人訴求,林草部門需要研究『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的物種認定問題。」

這個使用範圍在2017年國家林業局「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第一批)」和2020年5月農業農村部的《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該目錄包含多種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允許人工繁殖利用的陸生野生動物的範圍,或將成為未來國家林草局發布「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物種的一種機制。
在上述19種被允許作為寵物繁殖販賣的動物中,有15種在中國沒有自然分佈,是根據CITES附錄核准為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僅4種在中國有自然分佈。野生動物保護組織環境調查署(EIA)發現其中非洲灰鸚鵡、輻紋陸龜被列入CITES附錄一,並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分別評估為瀕危和極度瀕危,折衷鸚鵡的亞種桑巴島折衷鸚鵡也已被評為瀕危物種。該機構在提交給國家林草局的意見回饋中寫道:「如果這些物種的商業利用和貿易在中國被合法化,中國市場對野外捕獲的種源的巨大需求將威脅野外種群。」
「刑行銜接」任重道遠
「兩高」在前述「答記者問」中表示將完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之間的雙向銜接機制,防止案件處理在新司法解釋之後「一寬了之」。但兩者的銜接任重道遠。「我們都認為這次市場監管局、林草局的行政監管責任更強了,想要勝任還需要大量的努力。」上述森林民警表示這是同行的普遍看法。「短時間內建立強大的行政執法力量來填補森林公安執法力量的空檔是不現實的,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加強縣一級野保部門的正規化執法能力,是當前非常緊迫的工作。」他補充道。
國家林草局汶哲的文章認為,新司法解釋由於設定了多項不予起訴、處罰或不作為犯罪處理的情節,因此將「客觀上增加行政執法工作量」,因此文章提出「林草部門需要切實加強執法力量配備,確保野生動物資源保護力度不減。」
這篇文章還提到,本次司法解釋第17條提出,司法機關可將涉案動物的種屬類別、是否係人工繁殖,以及對野生動物資源的損害程度等專門性問題委託給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文章認為「這給主管部門提出了新課題」,它寫道:「基層林草部門普遍反映,野生動物保護力量不足、專業人才匱乏,為刑事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出具認定意見難度很大。」這勢必制約主管部門未來開展行政執法的效力。
本次司法解釋的初衷是提供司法救濟,包括對那些盜獵和走私少量野生動物的「普通人」,但動物卻不會陳述自己受到的傷害。香港大學的韋凱雯表示,法官和檢察官充分了解野生動物犯罪對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影響至關重要。但在世界各地,這種訊息都不為法官和檢察官充分了解,以至於很多案件被不恰當地從輕發落。因此,她的團隊發起了「物種受害者陳述計劃」,與科學家合作,整理野生動物盜獵與走私的生態影響,提交給法庭作為審判依據。在香港法官和檢察官使用了這種受害者陳述之後,野生動物走私案件的定罪量刑已經顯著提升。
一位國際動物保護組織的中國專家告訴中外對話,如果是為了解決輕微情節的司法救濟問題,那就應當追究那些把野生動物買賣炒作起來的人的責任,而不是把人工繁殖整體除罪化。她認為這是本次司法解釋「失焦」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