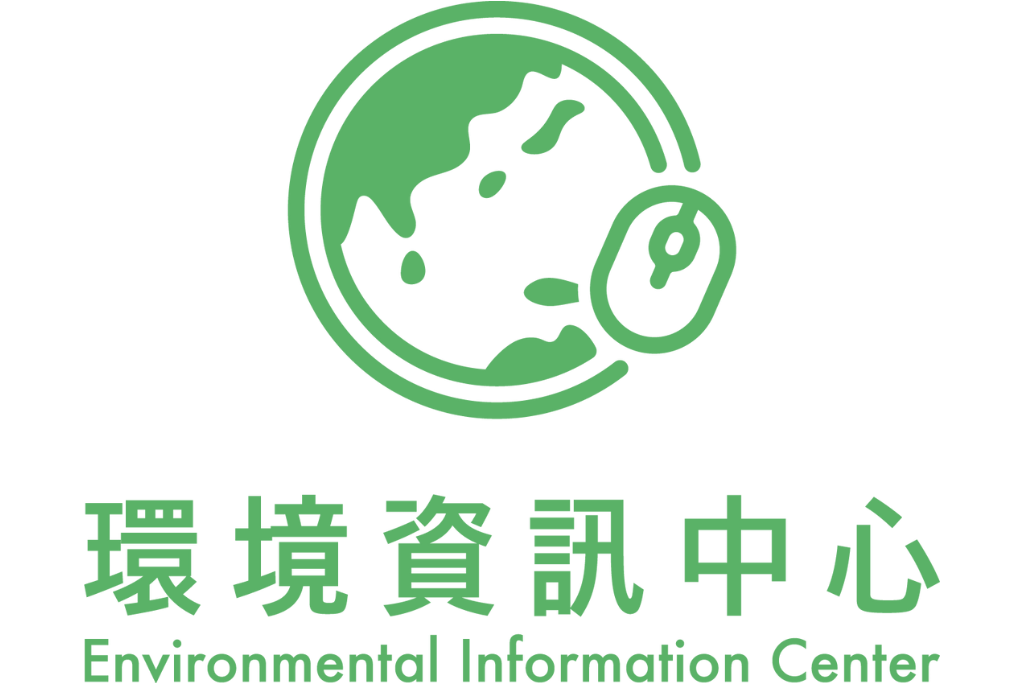推薦文
想像一下,1979年3月28日那天,你是一個住在三哩島核電廠附近的中學生。
核電廠發生事故之後,政府官員、核電廠負責人和前來調查的科學家都說,外洩的輻射劑量並不高,對居民健康和周圍環境的影響微乎其微,大家可以放心。然而,你的老媽卻憂心忡忡,她擔心你的健康會受到影響。
不久,附近農場主人飼養的動物,有的死胎,有的罹癌;幾年之後,社區居民的罹癌率也增加了。還好你沒事,平平安安長大了,目前一切安好。而根據流行病學家長期的調查與追蹤,三哩島核電廠鄰近社區的確有癌症集群的現象。很多人都認為這跟核災有關。
但篤信科學與理性的專家則認為,外洩輻射劑量那麼低,應該不是罹癌率提高的原因。有人因此懷疑:會不會是心理因素所致?那農場的動物呢?牠們也可能感受到什麼而心生恐慌嗎?此外,也有科學家發現樹木的葉子發生基因變異,很可能是輻射引起的。植物的健康,也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想像你是當年的中學生,見證過三哩島二號機事故,一號機重啟、關閉,如今又即將重啟營運,進入人生初老階段的你,會有什麼想法呢?
譯按
本文原載於Springer出版社在 2024年所出版的《氣候變遷時代核電的骯髒秘密》 (Dirty Secrets of Nuclear Power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一書的第六章〈三哩島:一個未解的悖論〉(Three Mile Island: An Unresolved Paradox)。
特別感謝作者Doug Brugge教授與Aaron Datesman博士慷慨授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中譯這篇極為重要的科普文章,以供教育與非商業使用。本篇文章可以幫助公眾理解,三哩島事故當事人所經歷之事,並不僅僅只是美國經驗,而是所有核電國家必須記取的教訓。
本文同時有助於公眾理解,為何工程、物理和生物學不同領域的科學,在評估核災之於民眾健康的影響時,出現了相互衝突的解釋;為何我們可以提出合理的科學解釋與佐證,來解釋核災中的受害民眾的罹癌情況。
感謝江櫻梅老師提出譯文修正建議。譯文如有疏漏,責任應歸於譯者。
〈三哩島:一個未解的悖論〉全文
生物學證據顯示,1979年三哩島核電廠2號機事故對人類造成傷害。由於權威主要取決於工程與物理科學界,這些現有生物學證據可能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
Aaron Datesman 為本文的主要作者。
關鍵字:細胞遺傳學、流行病學、核子事故、輻射、三哩島
在三哩島事故發生幾週後,我於5月7日前往華盛頓。我到華府是為了駁斥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珍.芳達(Jane Fonda)等人向新聞媒體所散佈的意在使人遠離核電的宣傳云云。我今年71歲,每天工作20小時,壓力很大。第二天我心臟病發作。你可能會說,我是唯一一個受到哈里斯堡(Harrisburg)附近那座反應爐影響的人。不對,這個說法不對。問題並不在反應爐,而是在珍.芳達。反應爐並不危險。 ——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博士於《華爾街日報》撰文 (Teller, 1979) 三哩島核電廠事故發生時,我住在…三哩島核電廠西北方約4英里處。1979年3月29日週四,我和兒子一整天都在車庫工作,車庫門開著。晚上洗澡時,我的臉、脖子與手看起來像嚴重燒傷。我感到噁心,眼睛又紅又痛,眼前一面模糊。我週五一早起床,嘴唇、鼻子都起水泡,喉嚨、胸口像火燒,口中味道像是燒焦的鍍鋅鋼板。兒子也有類似經歷,他當時22歲。 ——居住在三哩島附近居民的書面證詞 (Aamodt & Aamodt, 1984)。 參與三哩島核電廠研究無疑改變了我的人生與研究方向。儘管我內心充滿煎熬,但我願意再次嘗試,因為我從中學習到關於科學、學術、法院,以及人們如何在艱困處境中奮力對抗剝削他們的體制,而那個體制原本應該為他們服務。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分校史蒂文.溫 (Steve Wing) 教授;與作者的私人通信,2016 年。
賓州三哩島核電廠2號機於1979年3月28日發生爐心熔燬事故,此一事件至今仍是西半球最大的核電廠事故,也是最大的工業災難。因此在任何探討核電之於美國社會過去、現在與未來角色的討論中,這個主題都不可或缺。雖然人們對這起事故的記憶可能逐漸消失,但圍繞這一事件的一個深刻悖論,卻依然懸而未決。這個悖論的性質及其解決方式,會對美國乃至世界核電未來的發展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本章開頭的兩段引文闡述這個悖論的兩個面向。熱核彈的發明者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也是電影角色奇愛博士的靈感來源,他曾斷言,並沒有人會因為三哩島的事故而受到傷害。[1]無論泰勒博士的專業素養如何,他在1979年3月底人並不在賓州。而當時在場的其他人的觀察與看法,與他截然不同,簡言之,他們健康情況是事故嚴重程度的指標。權威與經驗之間的衝突,究竟應該如何解決?本文作者認為,這項悖論突顯出,權威人士既嚴重又令人擔憂的失靈。就本案而言,專家意見更重視物理測量而非生物學結果,因此可能未能識別,並且正確確認三哩島輻射所造成的傷害(包括短期與長期傷害)。
事故發生兩天後,當下達建議疏散當地最弱勢群體的命令之時,受損設施已經向環境中釋出大約 2,000 萬居里(20 MCi)的放射性惰性氣體氙-133 (Xe-133)。如圖6.1所示,大部分釋出的放射性物質是隨著風勢,以低羽流的形式向西北移動。雖然經常見到事故造成「微乎其微的劑量」這種聲明(Hatch et al., 1990),但釋出的放射性物質相當於20 公噸的鐳(44,000 磅),鐳是自然界中放射性最強的元素。據估計少量的碘 131,大約為 14 居里,也沉積在三哩島核電廠設施周圍10英里範圍,而從當地乳牛場所收集的牛奶中,發現到一些放射性碘。

雖然事故所釋放的輻射劑量並不算小,但根據傳統的科學理解,個人所承受的劑量並不令人擔憂,這倒也沒錯。伽馬射線對個人的最大劑量估計在0.7毫西弗(mSv)至2毫西弗之間,這相當於每年背景輻射劑量。[2]分析顯示,居住在50英里範圍內的200萬民眾的總曝露量約為37人西弗 (person - sievert)。預計該劑量將會在受影響群體中造成兩例癌症死亡。撇開以兩例死亡為中心的倫理問題不談,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此事的影響程度,應該無法觀察到事故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然而,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幾項獨立調查報告顯示,三哩島核電廠事故輻射釋放與癌症發病率或死亡率的增加有關,健康終點參數[3]包括女性肺癌發生率與乳癌死亡率(Wilson et al., 2023)。如果未造成傷害的科學預測是正確的,那證明造成傷害的流行病學發現必然出錯。另一方面,如果流行病學的發現屬實,那觀察到的醫療結果又是如何由於低水平的曝露而產生呢?
有一個老套卻很貼切笑話,就是「你要怎麼得到關於一個爭議話題的五個不同意見?」,答案是「你去問三位流行病學家」。過多的流行病學結果是不會提供明確的解釋,因此就如同這個笑話所引發的爭議,會比它所提出的解釋更多。幸運的是,與這起事故相關的其他科學研究領域,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更多啟發。我們來簡單回顧這段歷史,這就很有趣。
三哩島事故激發數十人終身投入社會運動,迪金森學院(Dickinson College)圖書館的檔案可以看到其中某些故事。可惜的是,迪金森學院的檔案館並未收錄兩名在三哩島事故中最有貢獻的社會運動者,諾曼.阿莫特 (Norman Aamodt)和瑪喬麗.阿莫特(Marjorie Aamodt) 的文章。然而,在核子管理委員會(t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圖書館中,使用「Aamodt」當成搜尋的關鍵字時,系統卻要求,搜尋條件應該要更精確,並且限制搜尋結果在1000項以內。
阿莫特夫婦的背景很有趣。雖然他們在1979年時居住於賓州切斯特郡(Chester county)的養牛場,但他們都受過技術教育。兩人是在任職於貝爾實驗室時相識,當時這個實驗室無疑是首屈一指的研究機構。阿莫特夫婦是經由一則分類廣告,而參與三哩島事故,尋求專業知識來確定事故原因。此後,他們終生投入此事,尤其是在美國賓州中區地方法院的訴訟,他們加入原告方,這個案子後來稱為三哩島核電廠案件合併審理案(TMI Consolidated)。此案的原告超過2000人,原告民眾相信自身由於三哩島核電廠爐心熔燬而遭受傷害。
在1984年由三哩島公共衛生基金(the Three Mile Island Public Health Fund)所贊助的三哩島劑量測定研討會上,瑪喬麗.阿莫特(Marjorie Aamodt)提出以下聲明:
……我是研究核電廠西北地區癌症死亡人數的女性之一。我只想說,這不只是死亡人數的問題,而是我們能從死亡中學到什麼的問題。我相信,這些人才是事故發生時真正的劑量計。(Beyea, 1985a)
瑪喬麗.阿莫特所發起的健康調查報告顯示,三哩島核電廠西北部某些分散的地區存在癌症集群(cancer clusters)現象。瑪喬麗.阿莫特發言的場所(涉及劑量測定,也就是曝露的物理測量)與她本人的陳述(「這些人才是事故發生時真正的劑量計」),清楚顯示物理測量與生物結果間的衝突。我們又該如何解決這個衝突?
因為阿莫特的這份調查報告,促使三哩島核電廠公共衛生基金提供資助,由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者、知名流行病學家默文.蘇瑟 (Mervyn Susser)指導,展開一場更大規模、更嚴格的流行病學調查(包括方圓10英里內的13萬人)。 蘇瑟教授擁有受人注目的背景,他與妻子澤娜.斯坦因 (Zena Stein)都是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者,他們由於政治立場於1956 年離開南非。蘇瑟於1966 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系主任,1980年代初期愛滋病在紐約爆發時,他是最早開始研究愛滋的流行病學家之一。他的形象絕不是一個向有害產業承歡獻媚的人。
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結果,常被描述成「並無證據顯示,三哩島核子事故會對健康造成影響」。這種解釋並不全然正確。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實際發現,受影響族群的肺癌發生率明顯上升。此事的爭議並非來自於研究結果,而是來自對研究的解讀。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聲稱,三哩島的放射性釋放不可能是致病的因素(Hatch et al., 1990),部分原因是當時曝露的輻射劑量較低。[4]然而他們從未斷言,並未發現癌症發生率過高。
對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結果的錯誤印象已經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三哩島核電廠案併案審理中,原告律師自行邀請專家,重新評估證據。這位專家就是史蒂文.溫(Steven Wing),他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流行病學家,也是本章開頭所引用第三段話的作者。溫教授先前曾分析橡樹嶺國家實驗室職業曝露工人的死亡率數據,橡樹嶺的經歷使他深深質疑政府/工業/科學界等環節(nexus)與核武、核電之事的聯繫。由於先前的經歷,溫教授在參與三哩島核電廠的訴訟之事,有所猶豫。但看到阿莫特在癌症集群調查的品質,以及這兩位傑出人士所展現出的承諾與理性,溫教授遂改變主意。
利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員所蒐集而得的數據,溫教授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團隊得出了基本上相似的結論。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的調查結果發表後,蘇瑟在《環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期刊所發表的一封信中,明確寫道:
我們的結果與溫教授等人的結果並無重大差異。但我們的結論並不相同:我們並未發現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癌症發病率是核子事故的結果;而他們則聲稱,有此證據。(Susser, 1997)
本文作者認為,這項陳述是就哥倫比亞大學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爭議的有效總結。與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不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團隊願意斷言,三哩島核電廠事故釋放可能導致肺癌發生率上升。他們願意提出這項有爭議的主張,似乎主要基於三項因素:
- 並未預設輻射劑量屬於「低劑量」範圍;
- 採用更細緻的數據分析方法,因而確信肺癌劑量反應關係的結論;
- 給予輻射曝露的個案證據更高的權重。
簡言之,兩個深具資歷的流行病學家團隊,使用相同數據,得到相似結果,但解讀這些結果,卻得到截然不同的結論。讀者或許會認為,流行病學並不是一種嚴謹的科學學門。但就本文作者的理解,這其中蘊含著一個更微妙的道理:流行病學所能得出結論,只能達到從物理測量所知的被曝造成危害,或從研究生物機制所知的被曝導致危害,這兩種潛在的認識相當。
因此,瑪喬麗.阿莫特在1984年研討會所提出的洞見,就彌足珍貴。如果由於可能缺乏物理理解,而無法可靠地解釋流行病學結果,如此一來,生物劑量可能會提供一些啟示,也就是直接測量曝露對生物體影響的標準。這樣的標準確實存在。事實上,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的兩位科學家早在1962年就已經描述它的性質與用途。相關的科學領域是細胞遺傳學,即研究人類染色體的結構與功能,DNA錯誤修復所導致的染色體「畸變」(aberrations)為游離輻射曝露嚴重程度的指標。
瑪喬麗.阿莫特並非唯一抱持這種觀點的人。賓州衛生部曾於 1979 年成立的衛生研究諮詢小組,該小組最初呼籲,細胞遺傳學劑量測定計畫應該成為幾項建議的調查之一。然而,由於「DNA鏈斷裂原因尚不確定」,他們後來重新考慮這個立場(Wilson et al., 2023 )。不過賓州衛生部所建議的細胞遺傳學研究,似乎從未進行。
儘管如此,最後還是有人做了人類細胞遺傳學調查,即生物學調查。有位俄羅斯科學家名叫弗拉基米爾.舍甫琴科(Vladimir Shevchenko),曾在 1994年與1995年兩次造訪賓州中部,當時他擔任三哩島核電廠案件合併審理的原告方專家證人。他受到諾曼.阿莫特(Norman Aamodt)之請而參與此案,兩人相識於1994年的瑞士日內瓦的科學會議。舍甫琴科博士曾在蘇聯接受生態學訓練,專業領域是評估放射性污染之於森林生態系統的損害。
由於工作,他多次前往前蘇聯各地多個輻射災害的現場[5],包括塞米巴拉金斯克試驗場(the Semipalatinsk test site)附近的西伯利亞西部、製造鈽的馬亞克試驗場(the Mayak site)附近的地區,以及 1986 年烏克蘭車諾比等地,當年反應爐發生爆炸,但機組卻欠缺圍組體結構。諾曼.阿莫特當時有幸多日接送舍甫琴科博士在賓州哈里斯堡附近地區四下走動,觀察樹木 。
從賓州的 80 多棵樹木上所採集的樹芯,後來被送到俄羅斯分析。舍甫琴科在呈交給賓州中區地方法院的一份官方報告中,傳達他的專業科學意見,即樹木受損顯示,在三哩島西北部與西部地區,氙氣羽流最強烈的地方,輻射曝露在2000毫西弗至1萬毫西弗間。舍甫琴科並非唯一一位提出這種看法的學者。美國科學家詹姆斯.岡克爾(James Gunckel)是研究游離輻射改變植物生長發育的世界權威,在大約10年前就曾提出相同的觀點。岡克爾博士研究過如圖6.2所示的畸形植物,並於1984年寫過下述內容:
我仔細檢查在三哩島意外發生不久後所蒐集到的一些常見植物標本,並與近來所蒐集的標本相互比較。目前的異常,可能是由誘發的染色體畸變延續而來…觀測到的植物異常類型可能是由於1979年3月29日的輻射落塵所引起。(Aamodt & Aamodt, 1984)

植物研究結果意義重大,因為它們與當局所說的傳統解釋相互衝突。正如當局所言,人類所受的某些不良健康影響,並非不能用心理學來解釋。事故以及隨後的疏散對受影響的個人而言,是極其痛苦之事。不過這種心理學解釋與樹木受損的觀察結果,兩者並不相容。
舍甫琴科博士的實地調查,並不侷限於植物生命,他也走訪附近的居民。他寫道,他從樹木的結構、生長與健康狀況,看到受到游離輻射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居民在事故發生時感受到健康情況異常」,包括……皮膚發紅與皮疹、噁心、眼睛發炎、金屬味、呼吸道發炎、腹瀉、肛門出血、脫髮、月經中斷、關節疼痛等。(Shevchenko, 1995)
舍甫琴科博士寫道,人群的症狀與曝露於1000毫西弗範圍內而引起的輻射病症相符。樹木的評估劑量高於人類,這既是因為氙氣羽流升高,也因為樹木的生命部分(樹皮與樹葉)外露,因此未受遮蔽。
舍甫琴科博士並整合一項規模龐大的調查,該調查齊聚俄羅斯科學研究機構內部不同領域的專家,包括植物學與生態學、物理劑量學、免疫學與細胞遺傳學。他所負責的這項調查的最終報告令人不安,而且幾乎不為人所知。他的調查結果如下:
在細胞遺傳學報告中,相互比較雙中節水平的數據[6]與接受輻射人群的細胞遺傳學研究結果……在居住在三哩島地區附近的居民中發現大致相同的雙中節頻率,而居住在俄羅斯受到游離輻射影響最為嚴重(原文如此)的一些地區的居民中,也發現大致相同的雙中節頻率。(Shevchenko, 1995)
簡言之,舍甫琴科博士的發現如下:在賓州中部接受檢查的人群中,他們的生物損傷程度,與原子彈落塵的西伯利亞西部阿爾泰(Altai)人口中所發現的相當,也與西伯利亞西部地區遭受原子彈輻射嚴重影響的人群相當。這項發現與樹木與植物受損變形的觀察結果、訪談所得的見聞,乃至於免疫缺陷的證據(以及其他見解)相符,但同時似乎與「三哩島事故的輻射暴露量與每年平均背景輻射劑量大致相同」的觀察結果,並不一致。
經由比較,討論又回到核心主題:物理測量與生物學結果之間的矛盾。我們認為,以下兩個觀察結果很可能同時正確:
- 三哩島核電廠周圍任何個體的吸收劑量都很小,小於約2毫戈雷(mGy )。這個結論是基於物理測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用被稱為熱發光劑量計(thermoluminescent dosimeters, TLD)的電子設備所做的測量。
- 對於受輻射曝露最嚴重的個體而言,生物學影響相當嚴重(輻射劑量在600毫西弗至1,000毫西弗間)。生物學結果支持這項結論:與輻射曝露相符的個案證據、俄羅斯科學家的調查結果,以及(儘管並非結論性的)流行病學研究。
當然,合理地懷疑舍甫琴科所整合的調查結果,這樣的態度也說得通,因為他的調查是出於法律程序的背景才進行,並未發表於同儕審查的文獻。這些結果可能有誤,遭錯誤詮釋,或以某種方式受到操縱?如果要回應這種疑慮,最明智的方法就是重複調查。由於某些染色體畸變會隨著期間變長而穩定,也就是說,它們會伴隨受試對象的一生,因此這種可能性仍然存在。
本書作者(以及其他合作者)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並進行類似研究。圖 6.3顯示我們 3MILER RUN(三哩島低度放射性氙氣曝露:使用新細胞遺傳學方法重新評估)(Three Mile Island Low level Exposure to Radioxenon: a Re-assessment Using New cytogenomics)研究的核型圖( karyogram)。我們初步研究結果預計將於2024年底公佈。

有人認為,三哩島事故蘊含的悖論反映出物理測量與生物效應之間的對立。核電技術的支持者多半植基於工程與物理科學領域。由於當時的文化崇尚技術,往往漠不關心風險問題,也由於權力與財富都集中在政府與產業界,因此二分法的一方,即基於物理理解為基礎的一方,主導了官方觀點。總體來說,這種權力失衡使得受影響群體所觀察到的自身健康狀況,遭到排除,而使解釋方式傾向於單純的物理理論。
關於核電的未來,三哩島事故的教訓應該是,低程度曝露的危害問題並未解決。如果「低水平」曝露造成的危害程度確實不容忽視,我們就必須採取額外的工程控制措施,以減少這些先前並未能識別出或遭低估的風險。這些必要的改變將會增加核電技術本來就已經欠缺競爭力的成本。
總結要點
- 游離輻射曝露所致的損傷,可以使用基於物理或生物學理解的方法,加以評估。有重要生物學證據顯示,三哩島事故的低水平輻射曝露會造成嚴重損傷。
- 由本文作者所進行的3MILER RUN 研究(三哩島低度放射性氙氣曝露:使用新細胞遺傳學方法重新評估),在本文發表時正在進行。
- 如果生物學跡象顯示,三哩島核電廠的輻射曝露對人體有害,確有其事,如此一來興建新核電廠要達到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所需要的額外工程控制,幾乎可以肯定會極其昂貴。
註釋
[1]值得一提的是,泰勒博士在《華爾街日報》表達這番言論的兩頁廣告是由德萊賽工業公司(Dresser Industries)所出資,該公司所生產的閥門發生故障,正是造成三哩島事故的直接原因。
[2]比較背景輻射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作者認為背景輻射雖然普遍存在,但人們對它並不夠了解。
[3]除其他調查外,匹茲堡大學的研究人員還研究截至 1995 年的癌症發病率數據,以及截至 1998 年的死亡率數據。
[4]摘自哥倫比亞大學團隊發表的論文:三哩島核電廠的釋放可能造成我們所觀察到的趨勢,尤其是肺癌的趨勢,但我們必須衡量下列因素:1.對輻射最敏感的癌症沒有影響,不確定對兒童的影響;2.未量測或未充分控制的因素可能造成混淆;3.我們自身的數據中,核電廠釋放與背景伽馬輻射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4.輻射曝露量低估,而且曝露發生後間隔時間過短。
[5]令人遺憾,舍甫琴科博士年紀不大,大約在2005年卻因胃癌離世。 2018年作者與阿莫特先生交談時,他憶及多年前與舍甫琴科博士相處的時光, 充滿懷念與敬意。
[6]雙中節染色體(dicentric)是染色體畸變的一種。
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 Aamodt,M.,&Aamodt,N.(1984).Petitionersv.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Aamodtmotionsforinvestigationoflicensee’sreportsofradioactivereleasesduringtheinitialdaysoftheTMI-2accidentandpostponementofrestartdecisionpendingresolutionofthisinvestigation.DocketNumber50-289.AdministrativeCourt,Washington,DC,21June.
- Beyea,J.(1985a).ProceedingsoftheWorkshoponThreeMileIslandDosimetry(Vol.1,p.124).ThreeMileIslandPublicHealthFundandtheAcademyofNaturalSciencesofPhiladelphia.
- Beyea,J.(1985b).ProceedingsoftheWorkshoponThreeMileIslandDosimetry(Vol.2,p.B129).ThreeMileIslandPublicHealthFundandtheAcademyofNaturalSciencesofPhiladelphia.
- ShevchenkoV.(1995).ThefinalreportofProf.VladimirA.Shevchenko,Ph.D.,Dr.Sc.,concerningthedosetoanyindividualfromtheTMIUnit2accident.Copyonfilewiththeauthor.
- Teller,E.(1979).IwastheonlyvictimoftheThreeMileIsland.TheWallStreetJournal,31,1979.
- Wilson,R.T.,LaBarge,B.L.,Stahl,L.E.,Goldenberg,D.,Lyamzina,Y.,&
※原文連結:〈ThreeMileIsland:AnUnresolvedParadox〉©TheAuthor(s)2024/D.Brugge,A.Datesman,DirtySecretsofNuclearPowerinanEraofClim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