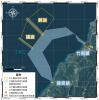§ 序曲
3月初四那場跌破冰河期的大雪之後,春神患了失憶症,主管台灣四千餘種維管束植物的精靈,個個張惶失措。
2004年底旱象、暖冬,外來客的木棉急於邀寵,2005年元月,競相綻放鉻紅,也有些植株堅持季節的禮數,含苞靜待。不料三.四寒害,白花花的北國銀雪,竟然摔落拔海七、八百米的,一片春鬧國度,許許多多亞熱帶的花仙子遂一病不起。
遲至3月底,再度開放的木棉,全數花容失色,朵朵貧血;我也記得,羊蹄甲配合晚春的盈餘,在水霧裡吐露粉紅色的淡妝,直將整個天蓋的陰霾,接引了過來。
我在如是詭異的氣氛中,展開2005年的南橫自然史之旅。
18年前曾經我調查了整條南橫山林路;18年後重新勘履,工作得更徹底,不需特殊理由,而且,愈老愈笨拙地只求個真實,我口述、錄音所有所見與未必得見,設置樣區系統登錄,唯物機械般,試圖逼進繁複生命的時空變遷,奢望得以找出演化的內在秩序或道理,如同愛因斯坦名言:我只想知道上帝的想法,其他的都是細節;我也相信,斯賓諾莎的核心概念:自然、神與實體都是同一件事。我夠天真、夠幸運才能享有如是辛勞。
南橫公路始闢於1968年7月,西起台南、東出海端,全長209.076公里,1972年10月31日完工、通車,沿線砍伐4萬6千公頃原始森林,公路編號台20,甲仙大橋頭里程為台20-58.5K,天池136K,東埡口147.5K,海拔最高段落2,722公尺。
而南橫前身,殆為日治時代關山越警備道路,完建於1930年。南橫通車33年來,因地質、天候或人為破壞,頻傳中斷,就交通功能言之,偏向觀光遊憩,但代價十分高昂。
§ 生命的變奏
4月6日我將進度推展到台20-82K,大小樹木及群芳,逐一處理落籍歸戶,偶而想想過去。多數時候,我專注在物種及其社會建構的天造地設,還有,牠們之間的竊竊私語。這不算偷窺,野外生命的媾合,從未沾染一絲靦腆,無論雌雄蕊與蟲蝶,譜唱的是荷爾蒙的和弦與對位,不需矯情。
4月份第三度前來,我推進到台20-101K,而夜宿梅山,卻得知錯誤的訊息,說是山林老友拉乎伊辭世多年,不是悲傷,不是錯愕,死亡是山林美學,只是讓我作夢,夢見了一段清新與希望。一株紅檜一年可以生產百多萬粒希望,偶而一、二粒讓夢成真,成為築夢的新枝幹,也許,全數種子融入腐植質的再循環,然而無機與有機並無截然的分界,活著卻不斷摸索它們的差別。
我在暗夜驅車回程,記憶圖像當中存有一幕,1988年的某深夜,吉普車強烈的光柱,迅速掃瞄在窗外遊走的樹林,一尊尊大地的舞者,鮮明地伸展肢體,明滅亮暗的律動,烙印在靈魂深處,我瞬間的狂戀,以一生的絕望,換得剎那的永遠。我真的不明白,生命怎會存有如此的戀情,只是那樣的一幕影像,偶爾就會溢出酒香。
而且,18年後同樣場景,悸動的還是過往。生命存有幾種特徵,其一,過程恆無可逆,從無回頭,逼得人生只剩當下,因而回憶如果有意義,無非在彰顯當下,而回憶也只能靠藉當下,於是構成當下與回憶的雙重尷尬,事實上,這只是記憶與回憶的混淆,任何思考都運用著記憶,因而所謂回憶,指的是心念流連於過往,阻止自己的創造性或啟發性。
因此,其二,生命擁有非機械式的無窮可能性,生命是每一瞬間唯一性的進展過程,或每一當下的連續體,無窮的可能性即存在於每一當下。生命過程任一瞬間的唯一,既是無窮可能性與創造性之所在,相對的,也蘊含致死性。小到個人,大至族群或生物種,數十億年來,如果將特定可能性推至極致,亦即扼殺掉更大部分的可能性,其將因堅持而滅亡。
「堅持」並非死抱著特定理念、信仰或意志,而是在念念之間,將可能性作轉化,好讓該理念、信仰、意志等等不斷重生。當代最虛無的概念謂之「永續發展」,最大部分的人使用此字眼之際,事實上,本質上,與古人之奢望服用不老仙丹,或期待長生不死同義。
現代人一輩子花費最大的精力,求取生活、生存、生計,卻忽略生命與生機,前三者說穿了即生殖與功名利祿,且美其名為幸福,這僅止於生物性的展現。從黑猩猩每天做個窩,到人種將流動的窩固定、持續、保全、舒適、美化,乃至於極盡奢侈之能事,本質上無何差異。
資本主義將叢林法則推展到極致,又冠上龐雜、精緻的糖衣碇,以及麻醉劑,在名牌、美食、虛榮堆中腐蝕人性;人性中最生物性的本能,在現代叢林,得到生命有史以來,最恐怖的溫床。
生命意義只是都會生活中,流浪狗不如的逢機明滅;我在童年,看見貧窮年代生活、生存、生計底層的掙扎,如今,卻隨時可見生命、生機無所不用其極地被摧殘。
§ 30年植物研究
穿過內英山,越經萬年橋,我在五月份的調查開抵原始林區。
台20-120.6K,霧社禎楠原始林內首遇困思。18年前我駕輕就熟,一草一木宛似家中傢俱、擺飾,如今卻陌生非常,我努力思考,原來,我30年植物研究,研究的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從未透徹,遑論任一物種的究竟。
可以瞭解,所謂調查研究,常是一種人本中心論,許多狀況下,幾乎等同於掠奪、專制與霸道,但我無意否定研究的功能、價值、意義或貢獻,只是,從一個浸淫此間的學習者觀點,自我的反思與提醒罷了,因為任何習慣總是,帶有致命的愚蠢。
18年前以及更年輕的時代,我敏銳地掌握各物種的區辨及其變異,也下達生態特徵的種種詮釋,一草一木如數家珍,罕有可以遁逃法眼者。然而,隨著所謂經驗知識的累進,數十年來終於知道一無所知,事實上任何生命,從形態、生態、生理、演化,從來處到去處,愈加深入,愈是探及造物主佈局的核心謎題;隨著探索,我們逐次切入生命長河的狂風暴浪,好似觸及自己靈魂底層的脈絡神經,傳來沉綿綿的悸動與痙攣。我只是研究植物,卻引發靈魂的顫抖,也深深為著過往研究的張狂與自信,感到惶恐與不安。
我肯定知識在理性及實務的力量,但亦瞭解其更深沉的傲慢與致命,不幸的是,生命太短暫,研究的神髓無法靠藉教育而傳承。人類文明進展過程中,隨著知識累進暴漲而躍進非凡,卻失掉了老祖宗時代,對生命終極性的體悟。有沒有一種教育的方法或系統,既能夠產生宗教的情愫、生命的感性、美學、全方位的哲思,又能兼具狹義科學的局部圓滿?如同E. O. Wilson 所夢想的「知識大融通」,又能涵蓋他浪漫之餘的漏洞?
所謂調查、研究讓我在此跪天禱地,同山林精靈告解。 (待續)
※ 原文刊載於「文學台灣」2006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