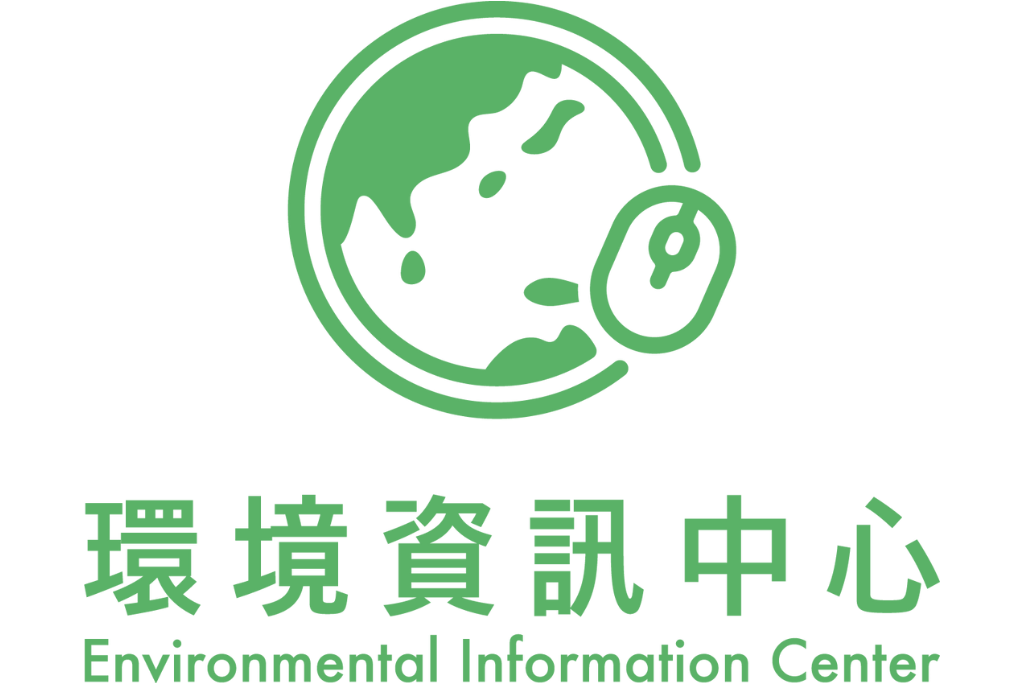習飛
幼鳥的羽翼漸豐了,親鳥在附近的枝梢鳴喚著、循循善誘地鼓勵幼鳥離巢。
飛行的事雖是本能,親鳥也只能夠鼓勵、帶領,卻無法代替。幼鳥一定得靠自己跨出離巢的那一步,才能感覺滑過每一根飛羽的氣流,感覺鼓動雙翼,牽動的骨骼與肌肉,從反覆的起飛與降落練習,掌握速度。這個階段,我們稱為「習飛」。

黑森林中小憩。圖片來源:孟琬瑜
盤算
懷著對高山的想念,這些年,不知道做過多少山行的夢。夢見某些山間生活的景象片刻,夢見過往山中同行的友人。到了小咕嚕上小學的這兩年,類似的夢反倒逐漸減少,彷彿是被流動的時間給稀釋。
直到下筆的此時,我才明白,並不是孩子長大,山就離自己越來越遠;而是隨著他們逐漸健步如飛,山將以另一種鴨子划水的方式,再度與自己靠近。
而有一天,我們將帶著他們,向著生命中的大山,「習飛」。
從我們第一次帶小咕嚕去爬合歡東峰、北峰開始,總有人不知是打趣還是認真地問道「有沒有打算讓小咕嚕幼稚園畢業的時候,去登玉山、撿『百岳』呀?」我們總是笑而不答。對小小孩而言,累積『百岳』具有什麼意義?我一直向著內心探問,卻沒有答案。
幾年之間,我們除了假日全家爬郊山、走古道、步道,以及仍維持著每年兩次帶咕瑀兄妹去合歡群峰,似乎沒有更積極的前進高山的進一步計畫。
事實上,也不能算是沒有任何計畫的。
阿德一直仔細地評估著同時帶咕嚕瑀魚去爬其他高山的可能性,要選哪一條路線入門好?雖然哥哥上高山的能力似乎早已具備,但我們仍希望兄妹倆的記憶裡,大山之行是全家同行的。如此,哥哥要能夠幫忙揹負一些東西,妹妹至少要能夠自己走一整天。
於是又經過兩年的等待,等待妹妹的生理時鐘可以自然早起、可以不用午睡,阿德才決定今年暑假嘗試帶兄妹倆去爬雪山。
鋪陳
從暑假一開始,阿德就向孩子們宣布了8月中旬將帶他們去爬台灣的第二高峰—雪山。也跟偶爾孩子提及、回憶他們更小的時候曾經去過的武陵、七卡山莊,不時地介紹爬山住在山屋裡,黃鼠狼來偷肉吃的情景,以及冰河的遺跡—雪山圈谷。
行前一週,阿德帶我們去添購了太陳舊必須汰換的登山裝備,還把握上雪山之前最後一個假日爬飛鳳山,當作行前的訓練以及裝備測試。
回想從放暑假開始,除了讓兄妹倆去學游泳,阿德安排了路程時間較長的猴硐大粗坑與金字碑古道縱走,以及高海拔的天鑾池與合歡北峰山行,都是大山行之前的訓練與鋪陳。

等媽咪追上的頑皮兄妹。圖片來源:孟婉瑜
虛驚一場:颱風
就在預定的日期剩下三天,一個熱帶低壓也剛剛形成名叫「啟德」的颱風,而且預測影響台灣的時間,剛好就在我們計畫上雪山的那三天。
阿德只好向孩子們宣布,雪山之行可能會因為颱風警報發布、封山,而不得不取消。讓所有的期待,從升到沸點、又瞬間降至冰點。
直到預計上山的前一天早上,颱風的動向預測逆轉為只會從台灣南端擦邊而過,在武陵工作的朋友正雄也建議我們還是準備上山,等待封山禁令解除。對於雪山的期待,又從全然落空轉為充滿希望了。行前的裝備檢視、採買,也隨即重新啟動。
整裝
有些生疏地進行著上山前的整裝與準備,一邊翻出幾近塵封的什物、一邊為回憶解除封印;一面著手防水打包,一面向小咕嚕解說。彷彿藉此,得以丈量自己與山的生份和心理距離。
忙碌到傍晚,車順利上路了,從頭前溪北上淡水河流域。望著被南方的颱風揮灑得精采無比的天色,觀音山與七星山的輪廓在遠方清晰浮現,阿德和我才分別發現忘了東西。然而,小小的困擾不過是短短幾秒時間。許多事物的重要性,似乎已隨著車駛向目的地,甚至愈來愈靠近,也改變了優先順序。
隨著循隧道穿過山脈北邊、進入蘭陽平原,繼續乘著夜間的靜謐,蜿蜒於蘇拉颱風肆虐過的台七甲、上溯蘭陽溪,某一些個「忘記」可以延遲到四天之後,拖著一身的髒與疲憊,卻洗刷了一心的空與清,再回頭檢視、處理。
夜間10點半安抵武陵。咕瑀兄妹因為舊地重遊,也因為明天就要往大山前進,可以住在山屋,興奮得有點兒睡不著,直到12點鐘熄燈才躺平。
清晨5點鐘鬧鈴響起,阿德和我先至屋外整理背包,咕瑀兄妹起來,也各自笑著試揹背包。然而,背包合適不合適,要等走上步道才知。妹妹才五歲半,背長太短,兩個小背包其實都還不適合她呢!
其實孩子們在將近四年前的11月底來過七卡,那時小咕嚕才四歲半,在步道旁的樹上發現了一隻雌的平頭大鍬形蟲,扮演起小小解說員。當時瑀魚還沒兩歲,讓爸爸用嬰兒揹架揹著上來。
我們在過哭坡之後的鐵杉林裡,稍事休息。我將大背包靠在後方石塊上,伸長了腿半倚著歇息,順道放鬆久未負重的肩膀。一隻體色近似赤腹松鼠、爪子白色的黃鼠狼,從阿德附近竄出,繞著我們兜了八九圈,並且不時從倒木底下、石頭後面鑽出來,與我們對看、凝視了好幾回,似乎想要向我們討東西吃。然而,牠動作輕巧、如行雲流水,總在相機剛舉起對準時,就已轉身竄入石縫或倒木下;旋即,又從另一處縫隙探頭,用一對黑溜溜的眼睛,打量著我們。有幾秒鐘,黃鼠狼幾乎碰觸到我的登山鞋。這是孩子們第一次近距離遇見活生生的黃鼠狼,不是沒有生命的標本。
妹妹:把拔,樹上為什麼會長「石頭」啊?
我們熟知的紫黑色冷杉球果,在可愛的登山新手眼中,是這樣純真、有趣的觀察與詮釋。我們是否因為知道了名字,而不再用心觀看、認真感覺了呢?

紫黑色冷杉球果。圖片來源:孟琬瑜
東峰就在步道旁,讓一路上負著背包的辛苦,都拋到九霄雲外。
地面上掉落著冷杉彎曲的枝條,不知道是不是台灣獼猴的傑作。妹妹撿起來說:「好像『燙頭髮的罩子』啊!」來,變個造型吧!
哥哥說:「我才不要『燙頭髮』呢!看我的『偽裝帽』,很帥吧?」
一截掉落的枝條,透過兩個孩子的眼光,投射出不同的光譜,充滿了童心和趣味的觀點,多麼有意思!你的「光譜」將落在何處?還覺得它「只不過是掉落的樹枝」嗎?
玉山圓柏生活在既高又冷的高海拔山區,成長十分緩慢,它們的年紀,很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古老。為了適應低溫、強風、冬季覆雪、結冰等惡劣的自然環境,呈現了不同的生長姿態與樣貌。明天進入圈谷,將看見匍匐著、盤曲糾結的圓柏老樹,可以想想它在漫長時空之中,經歷的生命故事。
離開東峰之後,前往三六九山莊的路程,咕嚕問了我許多爬聖母峰的事情。我知道,這是他在上學期末時看的一本書。於是,跟咕嚕談到了自己也曾從閱讀當中, 知道許多人去爬聖母峰故事。以及自己心中對於山,那份又敬愛、又畏懼的感覺。
開始能夠跟咕嚕談對於山的情感趨避,讓我覺得自己與他更接近了。
黃昏之前突來一陣對流雨,催趕仍在步道上逗留的我們加緊腳步,進入山屋。雨水停歇後,我們和要去翠池做哺乳類調查的一組人分別開始著手備餐。時間愈晚,天色的變化也愈見精彩,索性都坐在屋外,佐著景色、用起晚餐。孩子們前一晚到武陵時太過興奮,睡得較少,負重上山一日勞頓之後,兄妹倆都很早入夢。剩下阿德和我分別煮水及進出收拾。
屋外雲朵沉降,星子自靛藍天幕滲出。聖稜線山頭連綿,恍似一卷卷翻開復堆疊的龐然書冊,製造出巨大的暗影。而品田山的頁頁摺皺,此刻暫且埋沒在暗夜的墨黑中。我回想起十幾年前,自己曾像隻小螞蟻,爬著對面的那幾落「大書」。一位學長總是一面認真地跟我說:「很難囉!很難囉!」一面又鼓勵著說我一定做得到。
轉眼,天蠍座已轉到山屋上方的天空,再過片刻,便要從白木林後方隱遁而去。
清晨5點,阿德輕喚我和小咕嚕,推開山屋的窗戶,便得以望見外頭天空的變化。 太陽將從蘭陽溪方向的雲海中升起。 小咕嚕把每一朵形狀特殊的雲,都想像成一種動物,雲朵時有變化,他也用豐富的想像力,不斷編織著有趣的故事情節。

從箭竹草原上回首,遠景是南湖、中央尖,中景昨日經過的雪山東峰,腳下是變得好小的三六九山莊。圖片來源:孟琬瑜
咕嚕說,黑森林底下茂密的苔蘚,是他心目中美麗的「小森林」。瑀魚時常撿起從樹幹上掉落的地衣。地衣和苔蘚都是森林形成之初開疆拓土的先驅,猶如胚胎著床大地最初的胎盤。
孩子們和媽媽一樣很愛大樹,這次兄妹倆也各自抱了抱大樹。哥哥還一直跟我說,他發現每一株冷杉的樹根都生得好粗。孩子啊,要長成數十公尺高的大樹,一定得要站穩腳步, 穩紮穩打 、慢慢養成的,才能夠橫越時空數百年、甚至上千年。
走在參天的冷杉純林中,身旁都是粗壯通直、直指天際的銀灰色樹幹,宛如置身一座森林的殿堂。在森林的情境氛圍裡,孩子們的提問都很有趣,真希望我能夠一一回想,整理出來分享。
小咕嚕問爸爸說:「為什麼這棵大樹的樹幹好像會旋轉啊?」阿德用三條繩子編織、絞在一起,與不編織,哪一個強度比較強?讓咕嚕和瑀魚想一想,樹幹旋轉有什麼道理嗎?兄妹倆聽完爸爸的引導和解釋之後,便決定回到山莊以後,要幫我的頭髮編「麻花辮」,各自認養一邊,體驗看看樹幹一面生長一面旋轉的原理。
我們走得很慢,一路上都在玩兒,所以才會在第一天遇見黃鼠狼,繞著我們轉了八九圈,要跟我們討食物;又在前往雪山主峰的黑森林中,遇見了台灣獼猴;所以,才會在圈谷往主峰的路途,遇上那陣襲人的冰雹。

森林小語。圖片來源:孟琬瑜
黑森林營地附近有冰冽的潺潺小溪流淌而過,是七家灣溪的上游支流。林間小徑通過兩株玉山圓柏老樹形成的拱門。
冷杉純林開始交織著玉山圓柏林時,天空落下大而密集的雨點。我們和隨後追上來的小胖叔叔的調查隊伍都停下來,套上雨衣。才剛過早上10點,雖然有所準備,然而這陣雨確實來得太早了。
抵達圈谷底時,雨暫時停了,雲層曾經綻開一片藍天,給了我們半小時的好天氣。小胖叔叔一行四人繼續往雪山與北稜角的鞍部前進,他們今天的目的地是翠池。
碗狀的雪山圈谷,是冰河曾經來過台灣的遺跡之一喔!下回來雪山,你們應該又長大了些,我們再一塊兒來尋找冰河擦痕吧!
雲霧散去時,乍見圈谷的壯觀,讓人自覺在廣遠的時空中自身的渺小。
之後,灰黑的積雲飄來又聚攏,雨又下了。前去的山徑,在大雨中成了泥色的小溪,必須涉淺水而行。北稜角往聖稜線方向閃電與雷聲不斷。
接近中午時分,巨大的烏雲匯聚為另一場雨。雨勢愈來愈急驟,轉為銀白色珠子似的冰雹陣陣落下。走在圈谷中無處可掩蔽,只能背對著冰雹來處,耐心等待打在雨衣上的「撒豆」聲漸漸止息。
感情豐富的妹妹以為,「冰雹」是在戲劇中看過,會把人凍成冰柱的「冰風暴」, 當時害怕得哭了起來,直到下山後再回想,才笑著說沒那麼可怕。
不知過了多久,冰雹停了,轉為降雨。等待久了,雙手都凍得僵直。我們決定繼續往上走。我回想起前一天,小咕嚕跟我聊了許多攀登聖母峰的故事。我一面走一面跟小咕嚕說,雖然爸媽以前來過雪山好幾次,也遇過許多不同的天候狀況,但是這次帶著咕嚕瑀魚兄妹倆來爬山,做任何判斷與決定,都會更加謹慎小心,和以前自己跟登山社來爬山的心情很不一樣。
上山的路辛苦嗎?對兩個小小孩來說,是肯定的。但是靠自己的努力完成的甘甜,在夢裡都會偷笑。前去或折返,有時是兩難的抉擇;孩子很想完成雪山之行,卻又面對身體的疲憊。內心的兩種聲音,不斷拔河。也曾是登山新手的我,完全能夠理解。
我們並未壓抑孩子的眼淚,淚水是一種必要的釋放,能夠適時沖走困頓與疲倦堆疊產生的壓力,將他們帶離某種暫時擱淺的心理狀態。雖然不見得能生出新的力量,然而,當他們再度提起勇氣跨步向前,雙腳書寫的生命故事,將如卷軸般向前繼續鋪展。
小咕嚕在上雪山的這天早晨有點頭暈,行進較為緩慢,但腳步仍穩。爸爸在下山的路途對他說:「咕嚕這次所經歷的,或許是爬山較不順利的狀況之一。在壞天氣與身體狀況的干擾之下,仍能堅定地往目標前進,非常難得。要好好記住這過程中的種種體會,往後遇到任何困難,也不過是以緩慢的步伐持續前進、度過難關。」

銀白色珠子似的冰雹陣陣落下。圖片來源:孟琬瑜
頭暈、陣雨、冰雹、雷聲閃電的輪番交織之下,完成旅程終點的心理距離,會因而膨脹。如果我們沒有慢慢走完最後的800公尺,讓心理的距離落實,與實際路程的距離合而為一,這趟山行,只是讓孩子繼續害怕、恐懼的震撼教育。
下山的路,仍舊是雨霧交織。只是心中想像的、困難被膨脹的山路,因為用自己小小的步伐走過,巨大的暗影縮小了,回歸真實。原來自己雖然渺小,山路卻沒有想像中的艱難。在山裡,我們找回了自己真實的定位。孩子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增添了一份自知之明與自信。
當天下午出黑森林前,已經下起了大雷雨,我們始終注意著閃電與雷聲落處,少了森林的遮蔽,沿山徑下行山莊,就是直接穿過那陣滂沱大雨,讓人不免有些躊躇 。
然而,妹妹循著之字坡一路下行,並未停歇,一馬當先返回山莊。咕嚕跟著阿德在後頭,沿途用登山杖在步道側邊開著導流溝,加速步道積水的排除,實做爸爸在太魯閣步道志工中學習的步道維護經驗。
最後穿過大雨回到山莊的小咕嚕,聲音顯得很有力氣。我問他:「頭暈好些了嗎?」「有點兒不舒服,是否還能爬山?」他同意地點點頭。
我和他一同回想,有一次期末考時感冒發燒,每天回到家倒頭就睡 ,隔天仍照常去考試。所有的狀況,爸爸媽媽都看著,理解,也皆屬平常。相信這次的山行經驗,讓他對於自己,又增進了一些了解。
咕嚕回山莊後一直喊餓,看到什麼都覺得好吃;瑀魚一直講話,一直開玩笑。兩個個性鮮明的孩子,對於情緒的表達方式不同,但是我們能夠讀得懂。雪山之行,將成為一份淚中帶笑、笑中彈淚的深刻記憶。
怎麼做到的?帶小小孩上山,需要用哄騙的嗎?大家都在問。
許多的鼓勵、多次休息、教小小孩讀解說牌、彼此欣賞、發現樂趣……。小朋友雖然走得慢,但是我們跨出的每一小步,都比前一刻更接近目的地。我們一直在往目標靠近,這種體會,無比真實。
那場雨,從早上10點多一直下到晚間8時許。孩子們早已經安穩地睡著了,山莊裡的其他隊伍也泰半入夢,雲層才悄悄地綻開一角,露出點點星光。
第三天,從三六九下山前。身上穿的,不是髒的、就是濕了又乾的衣物,頂著一頭逐日油膩的頭髮;行山的背包裡,是不用任何洗劑清潔的食器餐具、碎形的餅乾、面目扭曲的麵包…。然而雨水之後的陽光,肯定可以將心洗滌、再蒸餾,讓你的眼神,重新散發一股清亮的氣韻。
下山路途回首。 或許是因為離雪山太近了,山形很特殊的三六九零峰,只以標高命名。三六九山莊就是因位在三六九零峰下方而得名。照片中山莊右上方背景是凱蘭特昆山附近的另一處圈谷。

或許是因為離雪山太近了,山形很特殊的三六九零峰,只以標高命名。圖片來源:孟琬瑜
爬山前後,有什麼改變嗎?幼稚園的老師在問,園長媽媽也在問。
園長說,妹妹變得結實了。
爸爸說,妹妹的觀察力變敏銳了,喜歡問問題,對於「知」比起以往,更顯得興味盎然
我說,妹妹會自己讀里程數與解說牌了;至少她知道怎麼判讀自己在哪裡,也正在大腦裡面,建構一幅用自己的步伐,丈量空間的的立體地圖。
而小咕嚕,只要我停下腳步調整背包,或者拍照取景稍微久了一點,再趕上去的時候,往往會發現咕嚕在半途中等我。原來,只要回頭沒見著我,他就會停在原地等我追上。他一直很在意全家人走在一起的感覺,即使在平常的郊山或者散步行程,咕嚕都有這樣的特質。只是我們太習慣了他的好,而缺乏更細膩的覺察。
也許孩子什麼都沒變,他們只是以步伐與情感,創造著自己的生命歷程。也或許,是更貼近了真實、深層的自己吧!
8月是高海拔的夏末,許多毛茸茸的熊蜂仍努力地訪花採蜜。有一次我追上小咕嚕的時候,他正在步道旁十分著迷地觀察著熊蜂。他告訴我說,高海拔的熊蜂似乎比中海拔的更可愛,他甚至趁著熊蜂專心訪花的時候,忍不住用指尖,悄悄地輕輕摸著牠們一身柔軟的金黃色絨毛,發現熊蜂並沒有任何閃躲或者反擊,牠的尾巴末端似乎沒有防禦用的刺。

熊蜂努力地訪花採蜜。圖片來源:孟琬瑜
清晨 目睹新生!
下山隔天清晨,一家人仍舊在天將亮未亮前,聽著窗外傳來鉛色水鶇的歌聲,準時清醒。我們走上一條靠近山壁的小徑,從武陵南谷往北谷方向前進。晨昏時分走在這條小徑上,總有些異想不到的奇遇。
眼角餘光瞥見一隻懸掛在近山壁處藤蔓間的曙鳳蝶,旁邊是一株琉球馬兜鈴,牠幼蟲時期的食草。鮮麗的桃紅色在清晨的藍灰色調中,是如此顯眼;略微蜷曲的前後翅翼,說明了牠趁著清晨時分的微光,方才羽化。
結束了蛹期全然的破壞與創造,剛擺脫蛹殼的牠,費力地扭曲著桃紅色的腹部,要將體液注入翅脈,換取往後幾週支持牠在天空飛翔、在花間穿梭的能力。
待陽光翻過稜線,照進谷地裡,牠就要乘著溫暖的空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移動、覓食,展開生命中的新頁。

目睹一隻剛羽化的曙鳳蝶。不停扭動著腹部,努力將體液注入翅脈。。圖片來源:孟琬瑜
也許有人期待地問道,經過長路與雨水洗禮的高山之行,孩子是否也如曙鳳蝶結束蛹期羽化般,脫胎換骨呢?
事實上,孩子們的成長,不是拋棄過去。所有走過的足跡、踩在腳下的影子,都隸屬於他們的生命歷程,也都持續書寫在自己的生命扉頁裡。
而他們也在時光之流中,每一個穩穩的跨步,紮紮實實地長大。不是嗎?
一段森林底下的地被,隨處可見這種像麥克風的褐色馬勃蕈。好奇的小手戳一戳、拍一拍,像中藥痱子粉的孢子,隨即從氣球狀孢子囊頂端的小孔噴出。
早晨8時許,當我們從北谷沿著武陵路折返時,暖暖的陽光早已滿佈谷間群樹。一隻隻大紅紋鳳蝶、烏鴉鳳蝶、曙鳳蝶……,正鼓動著鮮麗的鱗翅,舞過我們的頭頂和眼前。其中會不會也有今日清晨羽化的那一隻呢?
我們終究沒再回頭去探看那隻曙鳳蝶,此刻的牠,想必也在谷地的某處,隨著陽光的節奏拍著彩翅、翩翩然起舞。

雪山到三六九零峰的四個山頭。圖片來源:孟琬瑜
在武陵億年橋,就可以望見雪山到三六九零峰四個山頭。
尾聲
家裡攤晾著像萬國旗的衣服、登山用品店似的裝備,終於在烈陽的加持之下,擺脫了殘留的潮氣,陸續收拾歸位。旅程也進入尾聲。還有什麼殘餘著,藏在大背包裡、或者隨雨水滲在登山鞋的縫線、風雨衣的縫隙裡頭嗎?
回想上回來雪山已屆十年。此番山行,不管是孩子覺得累、走得慢、在路途耽擱、或者雨霧交替掩至,心裡始終清楚明白,山就在那裡。下山時,也不再感到依依不捨。原來山對我的意義,也有了些微的不同?
數日之後,重讀一篇十餘年前讀過的文章〈台灣櫸木的故事〉*。新的感受,萌生於更多的理解與知。我想,行山亦然。
*註:陳玉峰著,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