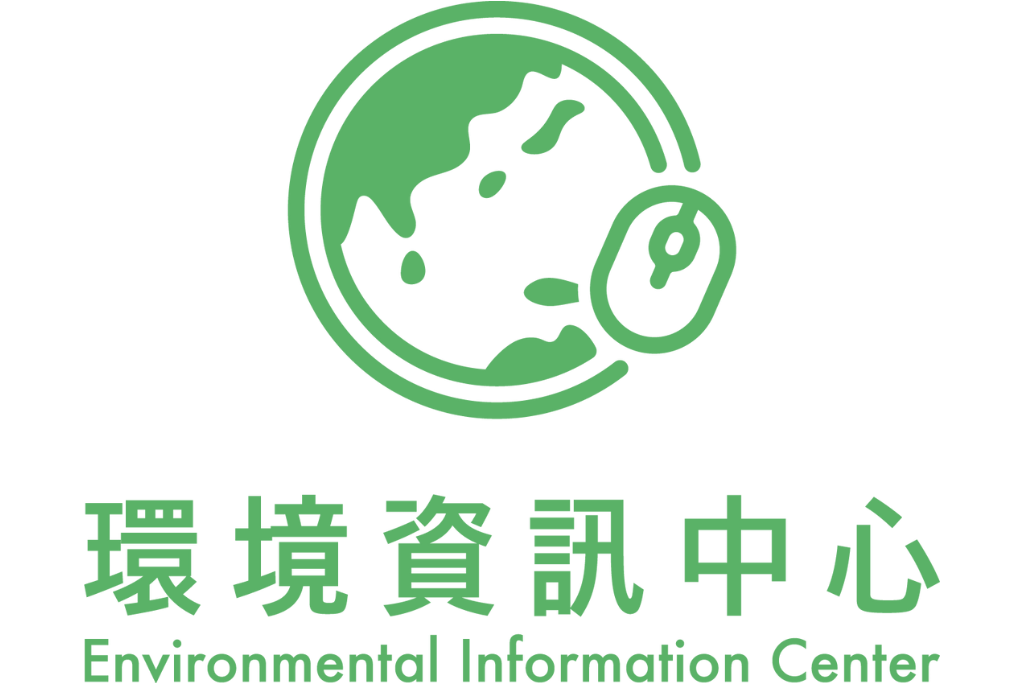編按:揭露流浪動物在收容所處境的紀錄片《十二夜》上映至今七年,浪犬問題仍未減少,路上隨處可見流浪動物蹤跡,寵物結紮觀念也尚待推廣。今年導演Raye的續作《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試著探究浪犬問題的成因和解方,報導詳見〈回到第零天 《十二夜》續作探討零撲殺後的掙扎〉,此篇特別收錄Raye的專訪。

問:在紀錄片中,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位教授在談論狗的時候特別強調「狗的存在跟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為什麼會特別把這放入紀錄片中?
Raye:我想要釐清一件事情是,狗數量這麼多,我想要把它跟「自然」分開。
我在影片很前面的時候就給出這個觀念——原來狗跟人的關係是這麼密緊密,就是沒有人類資源的挹注,牠是會死的、牠混不下來。
反過來說,今天狗會變得那麼多,是人的問題。不是什麼物競天擇的自然繁殖,那是人類的力量造成的。所以當(電影)講到中段,這個教授再出現的時候,他跟你講說:「有些人會說這是牠們的命,或是這就是物競天擇,其實這一些動物跟人類活動是息息相關的。」
人的存在就是一直在破壞這個自然界、還有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全世界的動物,只要是野生動物,都是在減少數量,但是只有人身邊的馴化動物,數量是在增加的。
這是一個有點需要思考和理解的事情,我不確定在紀錄片這麼短的時間之內,觀眾有沒有辦法去理解到我點明的這一層,但是我覺得我已經盡量簡化,讓觀眾可以理解了,因為這是一個對一般人來講沒有想過的事情……對一般人來講,他覺得有動物就是大自然,我去有綠綠的地方就是接觸大自然,所以狗也是自然。
現在對於放生這件事情,大眾已經多少覺得是不對的,但是在街上餵的流浪狗,大家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它需要一點時間去讓你理解這件事。
問:針對流浪狗問題,你認為台灣現在最迫切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Raye:如果要排出優先順序的話,我會覺得第一順位是結紮。所有跟結紮相關的資源是第一優先的。因為這東西有卡住,其他事情都動不了。我會把絕育認為是首要是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數量太過龐大。
當數量太過龐大的時候,收容所裡面的動物福利很難維持,數量太多、一直要進來,然後送養也變成很難要求飼主責任,因為收容所裡面壓力大成這個樣子,能(送養)出去趕快出去,這時候你有餘裕、或是有這個空間去要求飼主嗎?其實你沒有,你是拜託他們把牠們帶走,這樣飼主責任就不會在這邊出現,你沒有這個教育的空間。
然後外面的流浪動物因為多,所以繁殖的量也很大,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流浪動物一多,餵養的人你就很難叫他們視而不見。
浪犬數量一大,牠就也會影響到野生動物的生存條件,或是其他的像是公安問題等等的。
所以所有的問題、一切問題的主因,都跟數量有關。所以我才會說,如果要在這一些所有我們認為重要的事情裡面,排一個優先順序的話,減量是目前台灣的第一要務。
但是減量必須要搭配其他事情,不是減量了問題就會解決,它必須要搭配教育、好的收容、收容要怎麼轉型,怎麼建立民眾的觀念,這些全部都要進行。
問:您拍攝流浪狗議題至今將近10年,你在這段期間有看到什麼變化嗎?
Raye:過去和現在其實沒什麼兩樣。我一直覺得在街上的流浪狗有非常多的生存困境:車禍、毒殺、驅趕、有沒有食物吃、然後有沒有人照顧、有沒有反對民眾?都是重複的故事。
或許要等到全台灣家犬絕育率達到90%、流浪動物整體開始下降的時候,才會看到這些野生動物跟流浪動物有減緩的一天。但是目前,沒有任何人或方法可以解決眼前的困境。我認為它是一個無解的循環:無論是餵養、人犬衝突或是野生動物和流浪犬的衝突都是。
唯一的止痛針,就是過去用的安樂死。但是如果有用的話,當年也不會拍《十二夜》。撲殺就像是你把眼前的水量撈掉、但是讓水繼續灌進、再撈掉、水又灌進來......的無限循環。
因此,真正的解方在把家犬全部絕育完之後,整個狗的族群數量降下來,養狗的取得方式變得比較不容易,養狗的責任也建立起來,這件事情才會有真正解決的一天。

問:你剛剛提到數量控制的重要,你對TNR(捕捉-絕育-回放)的看法是什麼呢?
Raye:我們在紀錄片裡面,幾乎沒有正式的跟你解釋什麼叫TNR,就是因為我覺得它不是我想討論的重點,我想要把它的存在感壓到最低。
原因是,你要解決流浪動物問題,不是只有結紮流浪狗就可以,這些流浪狗總共14萬隻,可是全台灣養狗的可能有177萬隻。懷生相信動物協會執行長郭璇在電影提到:「我們現在講TNR都在結紮這14萬隻,但是家裡面的那些狗,生一生丟一丟,就整個白做了。」
先前有動保團體希望推動TNR入法,剛開始看的時候我是會贊同的,但是我聽了很多其他動保團體的意見之後,我開始理解為什麼他們反對。TNR在解決的是野化犬或是流浪狗,但是這個法令會跟飼主責任起衝突。
比方說,我的狗在這裡,我有餵牠但我不覺得牠是我的狗,牠也結紮了,這算TNR還是我有養狗?你餵牠餵了十幾年,牠住在你家門口,牠就是你家的狗,不要再跟我講他是流浪狗……它是一個灰色地帶,你在法令上沒有辦法直接定義他是不是飼主。
這一類的主人,TNR入法就會讓我們很難去處理他,因為他就可以去規避飼主責任。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的目光可以放在這裡……真正應該做的事情是整體結紮率提升。這個整體結紮率是包含所有跟人有關係、人在養的家犬:不管你是野狗有人餵養、還是最大的大宗人養的家犬。
我們必須要回到更上層的源頭,而且是所有人注意力都要回來這裡,就是家犬的結紮是最首要的。我們希望的是每一個人養狗,都可以有責任的觀念,為牠去負責任、去做這些種種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在講源頭是飼主責任,TNR它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而是一個階段性不得不的處理方式。
問:現在有些團體想要推動校犬,在學校中做生命教育,你認為這對飼主責任的養成會有幫助嗎?
Raye:其實我非常擔心,很多學校老師看了這部片就會覺得想要養校犬,這就是一個很差勁的生命教育。
因為片子的最後有講到說,我們要創造的是一個人與動物和諧共生、共生共存共榮的環境,這邊指的人,也是指不同想法的人。今天我們拍這部片並不是要所有人都愛狗、所有人都去養狗,而是我們要知道彼此尊重,還有要怎麼樣做、才是對所有人都好。
我不是反對養校犬,但是我為什麼會反對「每一間學校」都強制要養校犬,或者變成教學評鑑的項目。
這不是一個很OK的作法,這連在一個家庭裡面這都是一個很不OK的事情——負責人是誰?這隻狗最終的依靠是誰?這隻狗最後是不是變成一個工具、變成是為了完成一個教育的項目而出現在這個學校,卻沒有獲得任何保障?這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校犬不是沒有美好動人的故事,發生過很多很好的校園裡面的小故事,然後是師生都很和諧的,也會讓人非常的感動。但是牠不見得需要出現在每一間學校,因為一間學校要做一個好的、有品質的生命教育,還有很多方式可以做,而非強制性地養一隻狗。
為什麼我會對這件事情那麼確定,認為這是一個後續會有很多不可抗力的事情,是因為我跟拍高雄動保處很久,從(民國)105年開始接觸,一直拍到現在。他前面有一段時間就在推校犬,然後他很快的一兩年之內把這個計劃停止,已經養了的就養了,但是不再推動,就是因為他在這20幾間學校裡面,看到很多後續無法解決的問題……有一些學校就是不適合,因為你等於是在鼓勵一個還沒有準備好要養狗的人去養狗。
問:你民眾看了這部紀錄片以後可以有甚麼行動呢?
Raye:我覺得這是民眾自己要去想,我當然有點出一些大方向,紀錄片之後我們自己也有規劃很多教育推動的計畫,未來三年要去執行。
但是我們紀錄片不會觸及一些養狗觀念不對的民眾。可是我們的紀錄片觀眾裡面,有非常大的層面是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或者已經是中堅分子了,畢竟跟前者比起來,他們社經地位就是比較好,那這些能力有沒有辦法去影響前者?應該可以想辦法,或者是找什麼資源,去把有問題的飼主找出來,還有幫他們的狗結紮的民間團體。
我會拍攝這些團體,也是因為他們在面對的是這些民眾。他們的工作也同時顯示,政府在面對、要解決的,就是困難。它需要一些時間,也需要資源,所以這不是說我們想零撲殺,就可以零撲殺。
這群養狗人的觀念,還停留在你阿公阿嬤或爸爸媽媽的時代。我們在現在這個時代,也正在走過來。走在前面的人其實要帶著後面的人,你不能把這些人排除在外。
這些人就像第一部《十二夜》所拍攝的收容所那樣,沒人注意到他們。許多的教育宣導、資源無法觸及,但是如果我們要往前走,就不能不看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