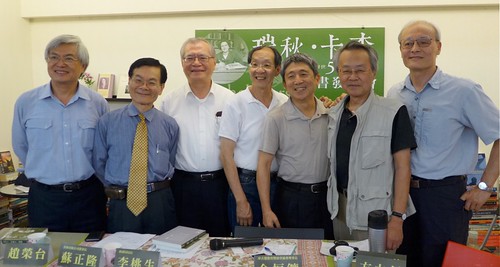卡森不是一個「世界末日」的悲觀者,她太愛自然,太愛這個紅塵了,當她重病的時候,天空的歸雁,遠航的皇蝶,都使她燃起生之希望,死前一個月,她寫:「星期天,一個溫暖的星期天,池塘的青蛙已開始叫了,我也聽到了知更鳥的第一首歌,春天不可能寂靜呀!」
過去五十年,生物界有兩件大事,一是一九五三年華特森和克立克發現的DNA分子構造,一是一九六二年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前者暢通了大河堤口,浩浩蕩蕩,有人賺了大錢,有人出了大名,今天的基因工程、分子醫療、分子農業都始源於對DNA的了解;後者引起了環保的社會運動,改變了現代人的歷史觀。很多人兢兢業業,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整個地球的健康,和人類的前途。DNA和環保來自不同方向,用了不同方法,到頭來一定會漸漸靠攏,保護自然,須要DNA研究,譬如加拿大政府剛剛成立了科學委員會,檢查「基因改變農作物」對「環境」的影響。基因和環境兩者關係雖然仍是矇矓,但一是微觀,一是宏觀,兩者的步伐漸漸一致了。
卡森生命的最後兩年是在死亡的陰影中渡過,榮譽從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飛來,給了她無限喜悅和憂傷,她說:「我只能放棄那些國外邀請的機會了,如果這些發生在十年之前會多好!」張愛玲是不是說過:「成名要早」?死前數月,她終於去加州看了紅樹林,也參加了一些重要的會議,拜訪了一些舊友,她回憶說:「曾有一個黑夜,在一片波浪濤濤的沙灘上,我看到一隻孤獨的小蟹,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這一霎那,啟示了我生之意義。」又說:「我很高興知道,在陌生人心中,我會繼續活下去,只要他們喜愛自然之美。」
瑞秋‧卡森,一個有詩心的少女,成長於苦難,像千萬人中任何一人,平凡的,簡單的,越走越高,越走越遠,但她沒有停留在山頂,她一直浪跡紅塵,高高站起,站成個天心的戰士。
後記:卡森死後三十七年,有成百的專書寫她的事業,寫她的生命,其中兩本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布魯克〈Paul Brook〉,一九七二,作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 the writer at work〉,我這一篇短文多取材於此書。〈二〉力爾〈Linda Lear〉,一九九七,瑞秋‧卡森,自然的證人〈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這一本書長達六百多頁,是最有權威的一本傳記。卡森生前未發表的書信、講稿和專文也已有兩本問世:〈一〉好奇的感覺〈一九六五〉;〈二〉失落的森林〈一九九八〉。一九六四年卡森逝世;那一年我也有很大的意義: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讀完博士〈海洋生物〉;我的雙胞胎女兒出生;負債八百元;離開西雅圖到加州一所大學任教。三十七年來,東奔西跑,驀然回首,昔日一個慘綠少年,垂垂老矣,對環境惡化越來越痛心,嘮嘮叨叨,明知不可為,也不能停下來,人總是要活在希望中,豈可無夢!今天時令冬至,才下午四點,已是晚霞滿天了,大地回報以皚皚白雲,一隻松鼠正在啃我掛在楊樹上的玉米,幾隻黑額鳥從樹枝跳到地上,再從地面飛到樹枝,是取暖還是覓食?一頭啄木鳥在幾棵枯死的樹幹上巡邏,它的紅頰被夕陽染得又年輕又滑稽……這樣一個可愛的冬天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