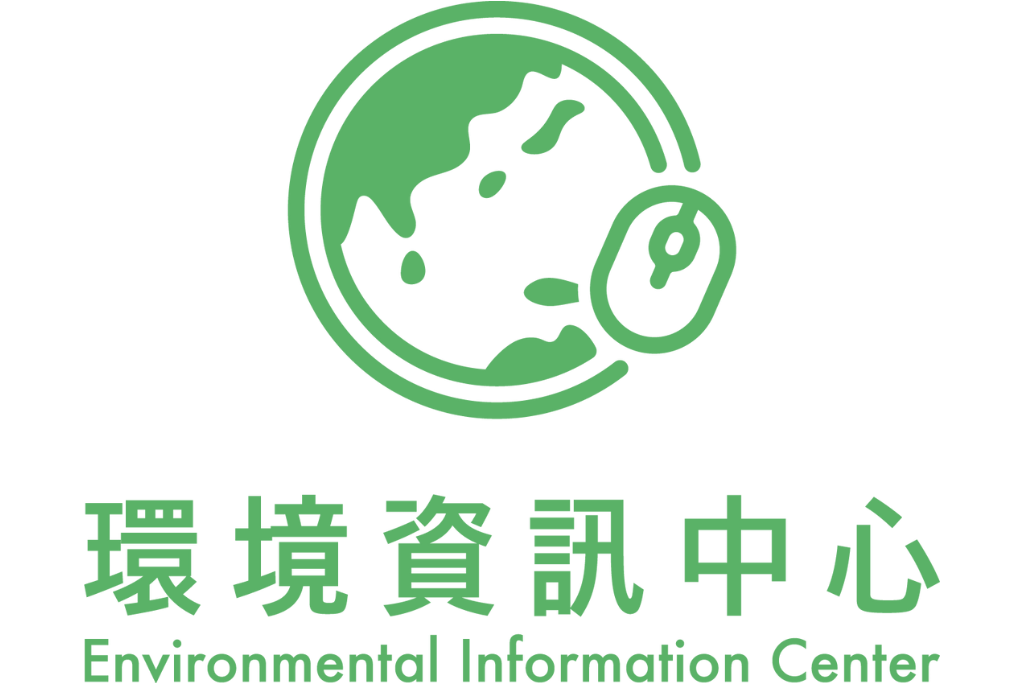東京的零皮草遊行正在行進中。參加遊行的人們,時而面向馬路上的車輛,時而高舉起貼滿了宣傳標語、圖片的看板,向人行道的路人喊話。還有幾個人不在行列裡,他們有的人身上掛著廣告板,有的則用左手握著一大疊傳單,彼此之間隔了十幾公尺的距離。由於他們的打扮並無奇特之處,在澀谷快節奏的人行速度中,並不引人注目,卻由於始終和隊伍保持著相同的速度和方向,因此能夠被輕易地辯識出來。
我也是遊行大隊旁邊的一員。遇到面善的、向遊行隊伍或傳單好奇地多看一眼的,或是穿皮草的路人,我盡可能地掩飾尷尬,將傳單遞出。記不清是第幾次參與這樣的活動,但那回向兩個穿著皮草飾邊外套的白人男性遞出傳單的印象卻很清晰。
他們友善地接過寫著「請不要穿皮草」的傳單,禮貌的低頭看了一會兒。不知是否也懂日語,但是他們的目光很快地回到遊行隊伍身上。隊伍中幾位與我相識但不熟悉的行動者正巧盯上了他們。一時之間,行動者們反覆高呼「不要穿皮草」,同時把廣告板上上下下地搖晃。老外不知是感到下不了台,或僅是兀自談論自己的事,他們依舊談笑的神態似乎讓行動者更為惱火,夾雜著英、日文不斷歇斯底里地嘶吼著「反對皮草」、「你身上的皮草是怎麼得來的?」令在一旁的我尷尬無比,彷彿和陌生人之間剛剛建立起的一點信任或友善,徹底煙消雲散了。

正如每次東京的動保遊行過後,總會有幾個對「不要吃肉」、「不要喝牛奶」等宣傳口號提出異議的成員,認為這種訊息「簡單粗暴」,不僅與呼籲公眾省思動物處境的訴求背道而馳,而且根本上無法達到效果。然而,關於宣傳話語和方式的論辯,卻被不在少數的行動主義者認為是「分化」運動的行為。這樣的反應,自然又引起另一方的不滿,行動者們被批評是「不讀書」、對社會運動缺乏戰略性思考,僅僅是受到來自網路等淺顯訊息的煽動。
在中國大陸、台灣或日本的動物倡議(經常被稱作「動物保護」)運動和學界之間,我都時常聽到兩個領域對彼此的不滿。學者雖被譏為象牙塔裡的居民,但仍舊還有點菁英的味道;相較之下,社會大眾對「動保人」的褒貶不一,「跪求善款」、「高速公路攔車救狗」等行為舉止甚至引來訕笑。動保人經常批評學者「坐而論道」、不願意投入到艱難的行動中;知識分子對行動者則有著「反智」、不可理喻的評價。在我看來,行動者和學者有著不同的特質及社會分工。本文關注的是,以動物倡議為例,活躍在第一線、充滿能動性的「行動主義者」,是否真的是一群缺乏理論和思考的烏合之眾?

「反智」:不容質疑的意識形態
在此所謂的「動保行動主義者」(animal activist),包含所有以不同形式去積極地參與動保活動的人。他們可能是餵食流浪貓狗的愛心媽媽,也可能是遊行隊伍中的一員,或是發起網路連署的活動家,其共同特質在於試圖以實際行動為動物爭取更多關注。而「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一詞則有兩種意思。一種是如「文化大革命」中對知識分子的打壓;另一種則是本文關注的,對知識、智識和思考的否定。實際上,「反智」經常表現為一種不容質疑的意識形態,在宗教團體中常常出現,這也和人們身處在群體中時,容易喪失判斷力和提出異議的勇氣,傾向於「從眾」的心理不無關系。
行動主義者群體雖然在發心之初,旨在對主流社會提出新的觀點,卻同樣存在「反智」現象,圍繞此問題的衝突亦不鮮見。「反智」不只是非理性、訴諸情感、不經考量等行為表現,它更為顯見的是教條化、反對理性辯論,嚴重缺乏思想深度。除了是一種現象,「反智」甚至是許多宣傳策略的組成部分。一位歐美動保界領袖曾公開表示「我們的目的是讓人們做好的事,但他們不需要知道為何而做」;另一位媒體大亨則認為,「人是不理性的,永遠不要對公眾有所期待」,而試圖將動保打造為一種新意識形態,以資本力量植入媒體渠道。凡此類放棄與公眾「講理」的行動者,在一定程度上,予人留下「反智」的印象。
動保人「反智」表現的背後:意識形態的衝突
動保行動者真的缺乏思想嗎?以動物倡議為例,我們仍可將其理論基礎,歸結於對兩種問題的思考,即關於「本質」的問題(「動物是什麼」、「人是什麼」),以及「倫理學」問題(「我們應該怎麼做」)。可以說,大多數圍繞著動物的爭議,都和這兩類問題相關。動保人的信念,不僅試圖影響大眾改變對待動物的態度、將動物視作資源的習慣,還可能牽動社會制度的變革、進而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批判。
進一步言,每個人對這兩類問題所得出的答案,反映了背後的世界觀,還有不同的動保目標。即使是動保界內部,也存在許多極為不同的觀點。比如主張「動物擁有權利(animal rights)」的「動物權利派」,和不反對利用動物,但提倡保障動物的基本需求(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之「動物福利派」,兩者有著極為鮮明的差異。在一次私下交流中,某國際知名的動保組織的研究部門主管,毫不掩飾地稱「動權派」倡議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行動和思維經常需要互相調整、消長、磨合。當兩者不相稱時,一者將會有所犧牲。一個堅定的行動者,思維可能因此易趨向簡化。他很可能不斷地重複其理論信仰的核心,來強化自身的信念和行動力。當複雜的理論被簡化為一兩句口號時,就算它本來很有道理,也可能被認為是由行動派所揮舞的「道德大棒」。雖未能一概而論,但是某些動保人士之所以給予公眾「反智」的印象,很可能和他們「去脈絡化」的語言方式直接挑戰了主流的意識形態有關。

如何避免成為狂熱的信徒
任何一種觀點要被社會接納,總是要經歷從提出、反覆驗證、新舊觀點博弈,最後勝出等過程,待其被社會接受、默認,才能逐漸被人們內化,甚至成為「潛意識」。對於許多行動主義者而言,他們很容易會急不可耐地略過社會論證的必要過程,直接將其觀點以一種意識形態的方式,對抗還處在初始階段、搞不清楚狀況的公眾。簡言之,行動主義者與社會公眾處在不同的步調中,當普通民眾還處於懵懂之時,他們已經跳躍到了最後一關。此時,如果不能對自身的觀點多加反省、經常回顧其信念產生的背景,以及理論和現實環境互動的脈絡,並檢視自身推論的合理和嚴謹性,行動者就可能變得僅剩「激進」,表現得相當「反智」。
期待一個行動主義者,必須同時身兼傳道和解惑的思想家角色,在清楚的傳達出複雜的思辨過程之餘,還要和不斷變動中的現實達成一致,實在是一種過高的要求。但是,行動主義者雖不負有提出新觀念或理論的義務,卻離不開自省的責任,如此才能避免成為狂熱的信徒。透過表達練習以提升思維能力,增進與人溝通的技巧和意願,對於避免予人留下「反智」的印象,也可能有一定幫助。

行動者的社會角色
蕭伯納曾說,「一個一生中不斷犯錯的人,不僅比無所事事的人更可敬,而且這樣的人生也更有意義。」行動主義者,即使經歷了不斷「試錯」的人生,這或許亦是以行動進行思辨的方式。
正如字面上的意思,行動主義者將「行動」視為第一要務,相較於「坐而言」,更強調「起而行」。然而,「願望式思考」(wishful thinking)氾濫,許多人僅僅選取符合既定認知的訊息。亦有研究指出,人們的思考會傾向去配合既有的行動,也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凡此種種,皆為行動主義者需要時常自我警惕的問題。相反地,多思多慮的思想者,若習慣反省或自我調整,就比較不會輕易說出各種斷言。古往今來,行動主義者和思想者擔任了不同的社會角色。二者雖不能被斷然二分,但具備思想者特質的人,大體而言仍是少數,相較之下,或許理念的信徒才是新體制的推動者。
最後,「為動物發聲」或許一如哲學家康德所說,善良的行為是清楚自明的,不需要太多的解釋和辯護。除了哲學式的理性思辨,也有許多人出於宗教或情感而行動,對他們而言,理論僅僅是用來與人進行辯論的工具。然而,也許我們仍舊要相信真理能被「越辯越明」,鼓勵大眾對重要問題進行深度論辯,擴展公民社會裡的爭論場域,以期共同制訂社會議題的解決方案。下次遇到「有理說不清」的行動者時,不妨靜下心來多多傾聽,透過對話了解動物議題的困境及行動者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