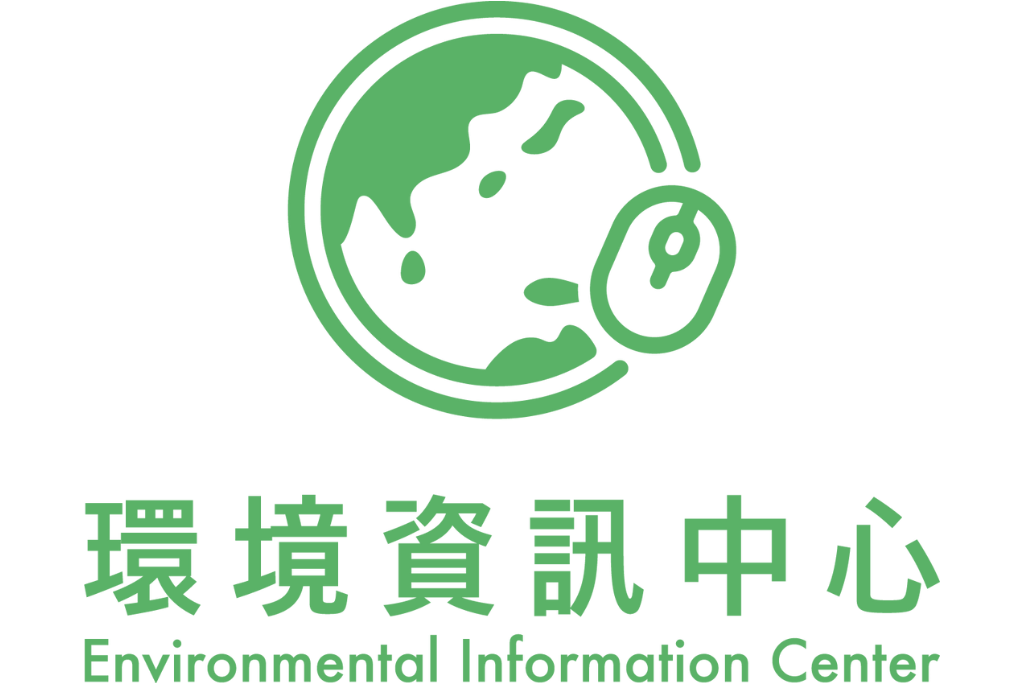無論是人人喊打的蜘蛛、公園裡的鴿子,或者是外來物種,在面對這些都市常見的「被厭惡動物」時,人們應該怎麼自處或與牠們共處?難道註定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或者人類有可能接受「讓大自然保留她所有我們覺得可怖之物」?這個複雜、困難的議題,卻常被人們以簡化的方式理解,也難怪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黃宗潔說,「這是個萬箭穿心的題目。」
本文整理自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講座「保留所有可怖之物?談都市中的「(被)厭惡動物」。希望能帶領讀者從不同的脈絡重新思考,或許你將發現,所得到的答案不只一種。

「蜘蛛就像鬼魅」 令人難以釋懷的恐怖
黃宗潔在一開場就從分享知名漫畫《瀨戶與內海》的故事開始,兩名高中生的日常閒聊,巧妙生動地呈現出人對特定生物的恐懼。
瀨戶希望能讓一點也不怕蜘蛛的內海理解,他恐懼蜘蛛所承受的痛苦。「蜘蛛就像一直在角落的鬼魅,或一雙從衣櫃露出一半、血淋淋的手。」
瀨戶接著表示,他理解蜘蛛其實很乾淨,更是會驅逐害蟲的益蟲,卻仍無法解除對蜘蛛的恐懼。「就像鬼在角落一直對你說,我很乾淨、我不會飛,也不能改變鬼很恐怖這件事情。」
當內海提出,「只要把蜘蛛殺了就能解決問題」。瀨戶卻看見,蜘蛛被擊中後掙扎扭曲的樣子——這只會使一切更恐怖。

恐懼與厭惡是人類的自我保護機制
這段對話呈現出,雖然每個人恐懼和厭惡的生物不同,但這些感受都是真實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死穴。」黃宗潔說道。
就連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在動物園中隔著玻璃,面對眼鏡蛇出擊的瞬間,仍然還是用連自己都大為驚訝的速度往後跳了兩碼。
達爾文寫下他的觀察:「在面對一個我未曾親身體會,僅是單純想像的威脅時,我的意志和理智根本無能為力。」
恐懼是生存的本能,而與恐懼連帶的情緒「厭惡」,同樣是一種帶離危險的自我保護機制。
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厭惡感與腦中特殊部位「腦島」有關,只要刺激這個部位,都會引發強烈的噁心感,畢竟所有動物都需要排出危險的物質和寄生蟲。
而嫌惡感可分為三種,包含毒物靠近嘴巴時引發的「核心厭惡」、靠近導致感染風險的人或地方帶來的「污染厭惡」,以及看見皮開肉綻、不符合常態的身體而使人連結到死亡的「身體外型毀損厭惡」。
穢物是不在適當位置上的東西
然而,黃宗潔告訴我們,厭惡與恐懼是可以拆開的。「人們不一定會厭惡恐懼的事物」,人們對於特定事物的「厭惡感」,也不能完全歸因於自我保護的生物本能,而可能在文化的介入下,產生因時因地的差異。
按照文化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說法——「穢物是不在適當位置上的東西。」

黃宗潔舉例,在人類眼中需要被保育的野生大象,卻是斯里蘭卡村民心中的厭惡動物。人類在大象棲息的森林旁設置了垃圾場,使大象逐漸習慣在人類活動的範圍中覓食,甚至直接進入村落尋找食物,導致人象關係變得相當緊張。
鴿子則是另一個例子。鴿子在人類文化中象徵著和平與美好,然而鴿子卻也是最適應都市的生物,龐大的族群數量,使牠們成為「最被鄙視的都市僭越者」。尤其在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威脅下,鴿子的群聚出現,造成人們更多的焦慮。
那些我們還沒愛上的事物
從古到今,人類對待環境問題的邏輯都很類似——透過不斷革新武器,消滅對自己有害或最看不順眼的生物。
以驅逐蟑螂的漫長歷史為例,人類不斷革新殺蟲藥劑,嘗試消滅牠們,卻適得其反的使蟑螂更加耐受,適存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對人類有益的生物。
這些上百種經過長期演化、適應居家環境的物種,早已是人類歷史中的常態,遠比民主、自來水系統或文學都來得更明確。想要趕盡殺絕,可能只是徒勞無功。
黃宗潔認為,選擇較為人道的移除手段或與之共生,亦不失為解決方法。例如在澳洲墨爾本的一座公園裡,就設計了專門管理鴿子的建築,提供鴿子巢箱,引導牠們到此下蛋,之後會有人把真的鴿子蛋換成假蛋,藉此控制鴿子的數量。

最後,黃宗潔節錄作家阿奇科・布希(Akiko Busch)《意外的守護者》書中的文字:「尊重那些我們還沒愛上的事物。」
也許人類能給予被厭惡動物一個出路,讓大自然用這樣的方式走向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