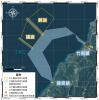§ 天龍故事
2005年9月12日我首度下榻天龍飯店,9月13日我在台20-179.5K附近困思,一一檢視自鋸山以下,大溪深谷乃至絕嶺突巔的林型,整理數十年來的歸納經驗,我所熟悉的展讀地文、生文等天書,從而抽離出原型觀。
整條南橫公路堪稱天險景觀者,一在最高海拔段落,一在東台峽谷。所謂峽谷地形,指的是溪流快速下切,將山體切成俐落的V 字,且通常是在岩山石壁上作用,以致於千年萬年的的營造,張羅柔弱與剛強的對比哲學,人在此間只能贊嘆。而最是出奇段落,殆自利稻隧道之後,特別是台20 -179.2K處以降,公路在此大轉角,此一山稜尖古稱「伊巴諾」,日治時代關山越嶺路自此,之字型急降至天龍吊橋,但公路闢建只能沿溪斜走。
伊巴諾至天龍吊橋頭的海拔落差237米,地圖上的直線距離只有400公尺,公路卻花了6,810公尺來鋪陳,可見地勢之陡峭,也在此間,形成素負盛名的天龍峽谷。
我們丈量天龍吊橋,長度101.8公尺,恰與1928年始建的數據一模一樣,至於距離水面高度則下降了1.3公尺,或說這條溪流,平均每年下切了1.73公分。準此粗略數據推知,從伊巴諾下切至今溪底,大約花了1萬8千年。
古代禪師面壁內化,我由天龍飯店客房直參這片天地,整理一周天來的心情,自然史部分我漸分明,人文史卻令人黯然神傷。
南橫前身的關山越嶺路興建於1921~1930 年,乃日本總督府為「理蕃」及國防所闢建的警察道路,其與八通關古道、能高越、知本越等橫貫天路齊名,且同樣是血跡斑斑,而關山越線及其支線大崙溪流域的抗日事件,原住民拉馬達星星、拉荷阿雷等事蹟,正是全台最後一批歸順日本強權者,人才之外,地理、地勢也是主因之一,今人不妨前往霧鹿新村,該村係 1938年之後,日本人將近鄰部落集團移住的新社區,而霧鹿國小後方,兩尊鑄於1903年列寧格勒的3吋鐵砲靜佇於此,它們來自日俄戰爭的戰利品,卻輾轉來台成為「理蕃」威嚇的利器,其中一門,原係安裝在摩天砲臺,今供展示於此;又,沿著步道走上山尖、涼亭制高點,正是日人砲臺遺址地,該地聳天拔萃,俯視昔日部落,更可透視歷史的紛紛擾擾。涼亭旁太魯閣櫟、青剛櫟、金毛杜鵑、呂宋莢迷等等灌叢蔥蘢,這是英雄、將士們曾經作過夢的故居。
不得不承認我不敢翻閱頁頁滄桑,因為地土上滿滿是種族群、異文化的悲情,愈是釐清史實愈是叫人瘋狂,之所以令人瘋狂,乃因我成長於清平世,活在台灣文明史上最富裕、安定的時代,在此,我只交代欠缺血淚的平版史實。
1915年日人在鹿寮溪以迄玉里設置通電鐵絲網,圍困布農人,截斷軍需、食鹽及日用品的交換,布農族硬挺千把個日子後,不得不假歸順,統治者更進一步於1921年起,開鑿關山越警備道路,並藉助軍機投擲炸彈等恫嚇原民,1927年開抵今之霧鹿,也就是說,由海端推進至霧鹿或天龍,費盡最艱困的7年,平均1年僅推進4.6公里,但往後3年則完成全線貫通。
因此,天龍的強權統治史肇自1928年,約在該年度,由警察後村助吉、城戶八十八等11人,率領助手30人,構築橫越新武呂溪大支流上空的大吊橋,且由當時「地方警視支廳長」富永藤平,命名為「天龍橋」,但正式公文書上記載,皆為「霧鹿.霧鹿鐵線橋」。
今之天龍飯店興建於1994至1998年間,座落於天龍吊橋頭,獨據天險,坐享峽谷菁英段落而得天獨厚,除卻岩相、地形、獨特林型、人文史蹟、溫泉、清澈溪流、鳥獸蟲蝶、季節彩衣之外,允稱一奇者氣象萬千。
蓋因日出後峽谷增溫,氣旋自谷地上送,形成所謂谷風。晴朗日谷風強烈,溼氣湧升,上溯中海拔而形成雲霧帶;日落後空氣下注,是稱山風,山風、谷風循環吹送,攜帶諸如台灣蘆竹之帶芒種子、蕨類孢子,或利於乘風遊走的繁殖體,上下來回投石問路,形成峽谷物種傳播的重點機制。1930年代,日本人利用氣球測試氣流活動,也形成在天龍吊橋上拋擲紙飛機的遊戲,據稱,乘著谷風的翅膀,可飛行數百公尺,甚或不知所終。
其實,峽谷勝景在狂暴天候,例如颱風豪雨之後,雲霧宛似遊龍戲鳳;而晨昏或變天,濃妝淡抹各有殊勝,不可言傳。
回顧三十年山林路,我循地文變異對應生文繁華,所有生界故事無論如何不可說,內因外緣總有蛛絲脈絡,即令逢機、巧合,亦不致於不可理喻,因為,所有植物緊緊依賴地土而生,依據地文尺度之放大或縮小,總可以找出詮釋或待詮釋的種種可能,畢竟研究自然生界,幾乎都是由果溯因,由事實歸納,而後論證、實驗、建立假說、理論,漸次逼近一套人類特定時代的特定典範,然後,再一一否證、顛覆、重建與新創,其實,凡此過程也是躍動的風景。
當我整條橫貫路調查接近尾聲之際,卻回到了台灣植被的襁褓期,我的心境、思慮,也被限制在一線天之間,特別是在谷底,昂首四探,只能擒住游線如龍的窄隘蒼穹,好比老年闔眼前的視野。或許這只是簡化的譬喻,也就是人生後一階段的更年,我想起1936年關文彥,由東向西走過關山越之後,回首山林寫了段話:「荖濃溪因連日豪雨而湍流滔滔,它若無其事地流逝,碰到岩石就避岩石,遇到高地即就低處,一直隨順地,流到應到的地方,而達成其目的。我回憶曾經三次關山越的足跡,仰望著令人懷念的山中寂靜」。
然而,我在當下已了,卻永遠懸念著來處與去處背後的,生命長河的意義與無意義。我很清楚,新武呂溪的終端是茫茫無垠的太平洋,是去處也是來處,但這身臭骨頭還背負著未了心志,非關來去,只是呼與吸之間的本願力,我知道,祖先想過、兒孫想過,所有鳥獸蟲蟻想過,直到未來、過去與現在,定根的天龍二葉松依然冥想著美麗與哀愁。(全文完)
※ 原文刊載於「文學台灣」2006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