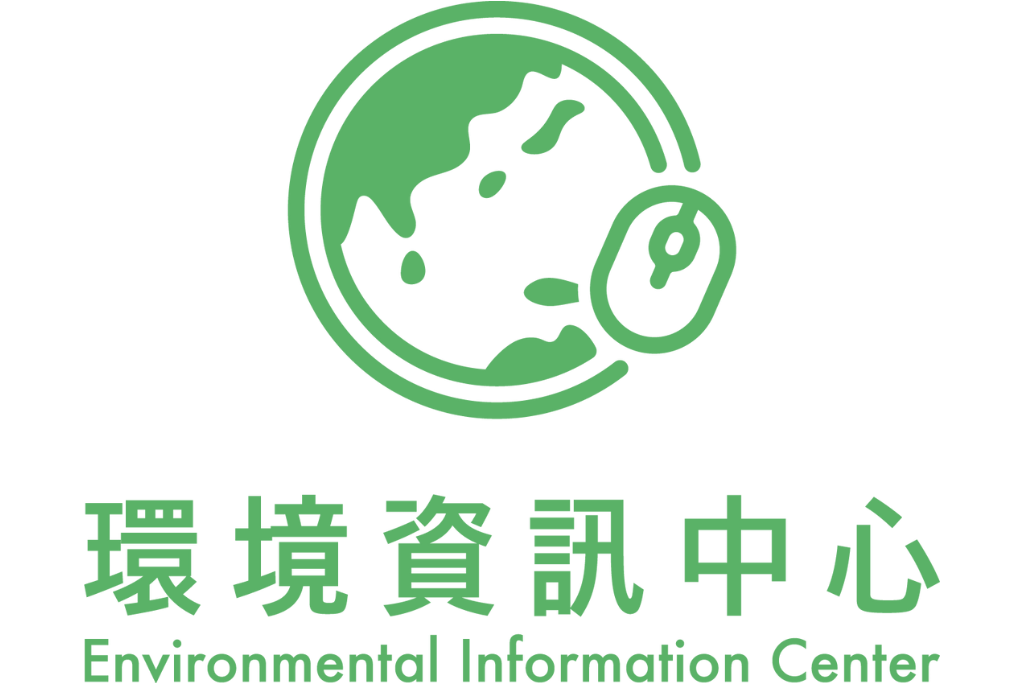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公民社會的沉寂】系列導言
而在這個時間點,我回到北京重遊,陸續聯繫了一位資深的公益人、兩位中生代機構負責人,還有兩位長期關注公益NGO行業發展的媒體從業者,試圖理解自2013年底我離開北京後,整個行業的走向與趨勢。
【公民社會的沉寂】這一系列文章,乃基於這五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寫作而成。特別是在2017年3月19日,台灣NGO工作者與人權志工李明哲在澳門入境中國遭秘密逮捕之後,被控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遭長期拘禁調查。
【公民社會的沉寂】試圖去回應這幾年來,對中國民間組織力量的彈壓與治理。讓台灣公眾了解到,官方如何透過《慈善法》、《境外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立法對民間組織形成治理與掌控;如何透過辭彙的改變無形去影響民間活動性質的改變,使民間力量成為配合官方政策的補充力量而非對抗力量;這一些措施,如同新設的防火牆,而在這牆內,中國民間人士的努力與其抱持的希望。
NGO(非政府組織)概念的形成
在中國,對NGO或NPO稱呼有一個演進過程。從1992年起,透過國際扶貧或性別教育機構在中國投入資金,國際組織開始進入中國並與本土機構合作。同時間研究型和環保NGO組織也开始出现。

1992年,中國第一個本土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在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等人共同發起下成立。
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舉辦「NGO論壇」,NGO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的言論當中,以前所有的組織都是隸屬於官方管理,非政府組織的概念第一次在媒體正式亮相。
一直到2000年左右,為了申辦北京奧運,中國積極向世界上展示中國的自信與進步。NPO或NGO這些概念,那個時候都還有空間,「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定義概念都可以說。
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來自各省市的志願者以及車輛癱瘓了所有前往四川的交通,國際組織以及各種民間力量第一時間都投入救災,也有大量組織投入災後重建。從2008到2012,可以說是民間組織大面積萌發的高峰時期。
在2012年底習近平在18大之後上台,對內部的民間組織及國際組織的活動空間開始一步一步約束收攏。
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這些都不在說了,沒有非政府NGO這個詞、永遠都不會再提了。非營利組織、NPO這些概念沒有了,有陣子叫做社會組織,但是後來也不在提了,官方的文件裡面全部都叫做公益組織。 然而「公益」這個概念實際上很模糊,找不到定義,比如慈善這個定義,中英字典裡面找得到,但是公益這個概念你找不到,新造的詞。頂多charity、philanthropy這兩個詞的區別。 然後大陸開始就全面去使用公益這樣一個說法跟概念。(匿名受訪者KA口述)
《慈善法》頒布、官方詞彙改變、指涉官方所設定新的合法空間

我覺得這個語言詞彙是很有意思的指標,詞彙某方面是指涉了社會的某一個發展階段的狀態,或者說這個一個局面。因為他不能說NGO不能說公民社會,他必須要順應這個說法……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機構負責人,你要去跟基金會談也好,你去跟政府說這個購買項目服務(政府標案)也好,你都必須用「公益組織」這種說法。 這種種狀態或者說這是一個新局面,民間不能說NGO、也不能說公民社會,必須順應官方制定的語彙,有趣的現象是大家都有一種默契去跟隨政府的風向轉變,去跟基金會談資助,或者政府採購項目,都必須用「公益組織」的說法。 你如果是機構的負責人,你或許是清晰知道這些語彙的改變背後所牽涉到的脈絡,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方案跟新的變化,背後是有我的價值觀跟我希望推進改變的社會議題。 但是這樣的詞彙話語用久了,慢慢都容易模糊那個初衷,機構負責人如此,更別說那些團隊裡面的工作人員,執行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往往會忘記這樣的發端。 。(受訪者KA,底線為筆者強調所加註)
透過辭彙的屏蔽效果,建構社會的記憶與遺忘
受訪者資深的行業人士KA前輩,為我生動的闡述了官方治理民間組織背後思維邏輯之精準與清晰,透過對一個「NGO名詞」的屏蔽,對於社會建構的規劃效果。
對民間組織發展的理論與定義的編造與再生產,官方設定好一個符合中國式法治社會與維穩/發展情境民間,然而這個概念底下「公民社會」理想是必須符合官方論述所設定的「透過民間組織具備的創新能力與效率,去補足既有政府體制之不足」的補充政府職能的角色。
我覺得這是統治當局很清晰慣用的一種手法,不斷的變換語彙,非常高端的一種統治手段,他能夠想辦法不斷的去變化語彙,然後讓你就無法保證你原本精神性的產品能夠延續下來。 在這個行業裏面獨立思考的人是少數,而具有清晰思路觀察的朋友更少。但是總有些思考深刻的人能夠清楚地看到,解讀這個新形成的語彙指涉的意涵。 語言文字、標誌沒變但是它在背後的內涵,人群關注的點在不斷的演進。而且這個透過語彙設定去影響概念的演進,任何人來提出這個(公民社會)的初衷,是無法的去扭轉概念的演進走向。而且我們也討論,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統治者樂見的結果。 你剛才提到NGO不應該只是一個服務者的角色,但是現在所有政府的法律制定和管控手段,都是朝向「你們這些NGO規規矩矩地去做服務,你們把各種各樣本來應該政府負擔的工作、責任全部都給我做好。」 這種趨勢,包括在資金的導向上,現在政府大量的預算要灑下來了。包括現在這種公益組織的資源,他自己都會去想,如果我不趕上這班列車,真的是天理難容(笑)。(受訪者KA)

官方的NGO治理方式是設立一道新的防火牆

而由於《境外NGO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立法,設定了境外組織所能提供的資金、活動空間與官方(以公安部為監管單位)能夠直接管理權限,實際上是將境內組織與境外組織設定了一道新的防火牆。
本土機構原本可以取得境外的國際組織資金,透過《境外法》限制也被約束,變成更多必須仰賴境內籌資,或者直接透過政府採購(標案)取得活動資金。
《慈善法》實施之後的改變是,未來可能有一定的組織,或許它們不需要通過國家公募的基金會才能夠來籌款,假使它願意遵照政府的監管與治理規則,它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募資渠道。
然而這樣由官方認可,而得以獲得合法的募資管道,對於KA這樣的資深行業人士而言,無形距離自主的公民社會理想,更加遙遠:
現在這個形式某方面來說,民間社會已經被鼓勵、被資源引導到官方認可的方向去發展。這意味著無論《慈善法》或者《境外法》都會加重NGO的偏離,而民間社會的發展,將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會越來越遠。 學理上來說,大陸的NGO數量確實是上漲了,但是基層去看,很多NGO並非自下而上的社會群體。有一部分社區組織是那種帶大媽們搞廣場舞、愛好者那一類人。有另一部分是體制內去安排去做的,只是充個名字。 真正屬於「Civil Society」的那一類,坦白說一點都沒有改變那種艱難的狀態。政府的錢你還是拿不到,然後國際組織、境外基金會都撤了。 國內的這些基金會,它是那個叫做資本在後面的話語權主導者,於是會趨向於去找那些已經有成效的老牌機構、規模大的組織去支持,這就形成馬太效應了嘛!要不然嘛就是這一類敏感性議題我不沾,我最安全。 你知道有個敦和慈善基金會……他曾經支持過一些NGO項目,也跟南都(公益基金會)支持過一些NGO項目。他們理事會決定把這些都撤掉了,以後主要支持國學,國學推廣最安全。 因為他們那些理事都是做投資的,非常聰明、非常精明的人,這批企業界人士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把握是很準確的。(KA口述)
公益行業鼓勵市場性格與專業化,初衷卻日漸模糊
對於KA這樣從事行業18年的老資格公益人而言,面對現在的制度正在逐步強化管理控制民間組織,當年中國民間社會萌芽的理想性格與改革性一步一步被清洗,對中國整體民間社會發展而言,很難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在2004年的時候,我們在行業討論問題,還會區分倡導性的組織和服務性的組織。但是現在已經徹底沒有倡導性組織這個概念了,你現在去問公益圈內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知道倡導性組織這個概念。 你試試看問90後剛剛進入公益領域的年輕人,他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概念。就這種語言、語彙上的屏蔽的作用還是很強的。過不了多久,就沒有人知道「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了,沒有人知道「益仁平」。 益仁平取名在於公益的益、仁愛的人、公平的平,所以它名字起的就已經看得出來那個,他把人權公平作為使命的,但是他完全被封殺。 他的發起人叫做陸軍,陸軍是回不來的,相當於把他流放了。是回不來的、是回不來的、你聽過嗎?你聽過嗎?儘管互聯網這麼發達,但是年輕人他很多人、事、概念都不知道(感嘆)。 他把這些完全無法馴服的組織關掉,人抓起來,或者驅逐出境。然後剩下的,用資金的方式,語言、文字、污染、或者屏蔽的方式,讓你全部都導向乖乖的來聽我(體制)的,拿我的錢,做這些你理應是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者服務的工作,現在大陸的傾向是這樣。(KA口述)
隨著被關停的機構,被捕入獄或監視居住控制行動的公益人,還有那些遠赴他鄉回不來的流亡者。KA的眼神流露出一絲絲悲愴的哀愁。
他告訴我有一些公益人士已經絕望了,心灰意冷索性移民外國,這一些人他沒有道德上的責備,因為他知道這些人已經盡力了,生命最精華的時間都消耗在中國的民間社會發展。
像KA這樣一個資深行業人士、公益人,見證過中國民間組織的起步,大面積萌發的輝煌年代,在走到沉寂與漸漸失去批判性格與改革理想。然而筆者相信,還是有一些像是KA這樣的公益人的存在,他們並未放棄中國的未來,而且持續努力著。(系列專文,未完待續)

※ 註:每年9月的深圳慈展會全名為「中国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是中國一年一度的公益行業最大盛事,幾乎不分類別,扶貧、教育、醫療、文化、環保各個領域的NGO從業機構都會派代表出席,但由於主辦單位的舉辦方式,或者配合官方政策撤除掉某些展出單位的資料,每年也都引發不少人的吐槽、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