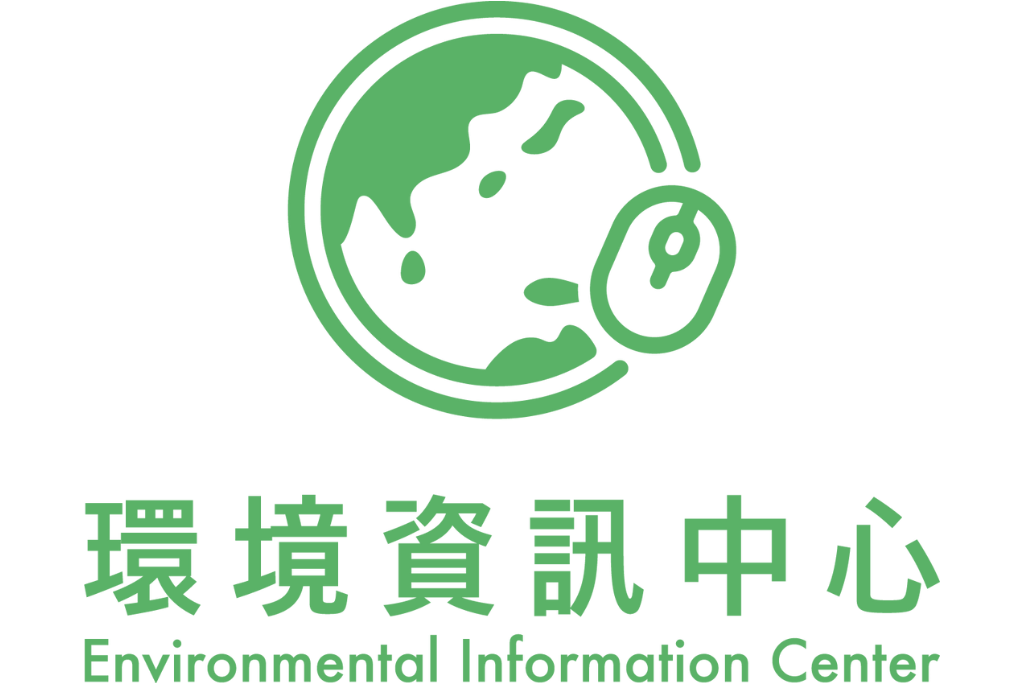2019年,加拿大國家藝廊「全球原住民當代藝術五年展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contemporary art」中,共有來自全球各地70位藝術家受邀參展,而台灣唯一參展的原住民族藝術家,是擅長以複合媒材雕塑與環境裝置進行創作的魯凱族安聖惠(峨冷‧魯魯安 Eleng Luluan)。她的作品《夢與夢之間》,以雪白色的保麗龍條、包裝袋、包裝紙等編織成一座有如母體的大型裝置藝術,現場震撼了許多人。
這個看似建築物,又形似動物與植物間的作品,是安聖惠透過部落女性擅長的編織文化,交織而成一場穿梭部落早期與當代社會的夢境。她不只是唯一台灣代表,也是亞太地區唯一受邀的原住民藝術家。
來自屏東縣大武山舊好茶部落的安聖惠,生於魯凱族的頭目家族。作品常以一種如夢似境的潛意識感,展現強大的內在情感,漂流木、植物、綁著檳榔荖葉的塑套鐵線、包裹水果釋迦的套袋等,都可以成為她的創作素材。2016年,她獲得第三屆Pulima藝術獎首獎,近年來,作品陸續獲邀至國際知名的藝術村及美術館、畫廊展出,備受矚目。

原鄉文化是養份,也是女性的桎梏
這幾年,她知名的作品都採用鈎織呈現。很難想像,鈎織這種向來被用來做成衣服、小物件的技法,會用來做成宛如建築結構的大型創作,令人驚豔。
「因為作品都很大,我需要很多人一起幫忙,每次在教他們時,我都會跟他們說:『放輕鬆,剛開始鋪路,千萬不要編得太用力。』有些人習慣做事非常紮實,後來才發現在編第二圈時會變得很吃力。我總笑他們說:『我不是跟你們講過嗎?每一種繩子的個性都不一樣,只要懂它,它就會把你帶到無限自由的地方去。」
這鈎織的技法,千變萬化,且是她的獨創;最初的啟蒙,來自生長的部落。

她出生於舊好茶,小學三年級後搬到霧台。在部落,尤其女人,一輩子有很多編織的機會,這語言她從小就再熟悉不過,只不過,生性叛逆的她,在高中家政課時,從不按照老師教的技法去做;而國小三年級,她就會問大人:「為什麼那些公共設施或藝術品,要一直模仿過去的作品?」
她心裡永遠有「還有什麼可能性」的質疑,她喜歡上山採集花草回家佈置,喜歡四處奔跑及爬樹…只不過,這樣富有創造性及冒險性的特質,並不符合魯凱族對端裝保守的期待,尤其,是對一個具有「貴族」階級身份的公主。
愛好自由的她,從小便感受到內心對身份的抗拒。從內埔農工畢業後,她就選擇離開家鄉,到台北發展。在台北十多年,她什麼都做,美髮、看護、攝影助理、鐵工木工,喪葬花藝⋯⋯台北打開了她對自己的各種想像,她在此開始也結束了婚姻,28歲,她再度回到了故鄉。
從貴族峨冷,到移居海邊的藝術勞動者
那年,她和三個女人,在舊好茶附近的水門橋,開了一間結合化妝、攝影、花藝的「秘密花園工作室」。 除了接案外,這神祕而自由的地方,還吸引了許多藝文人士、宗教人士、甚至政治人物,時常進入空間交流對話。
1998年,她正感覺到,人來人往的工作室,似乎讓她少了許多獨處的時間,便思索是否要把工作室給關了。於此同時,剛好有個朋友,從小看著她動手創作,便邀請她參與北美館《1998當代原住民藝術展》,從此,她一腳踏進藝術創作的領域。
2002年,台東的金樽部落,剛好聚集了幾位藝術家一起在海邊開創了「意識部落」,在金樽海灘自己搭屋生活、就地創作。安聖惠因緣際惠地加入,原以為是在此待上兩、三個月,沒想到,後來直接落腳都蘭,一待就是20幾年。
「那時整個都蘭的藝術能量剛開始聚集,有點像無政府狀態,我感覺在這裡完全可以做自己。」

她移居到都蘭,重新在自由的泥土上生長。她笑說,曾有幾次,部落的親友到都蘭,遠遠看到正在工作的她,都會先哭一會兒。「他們沒辧法想像,那個在部落原本謹慎保守的貴族峨冷,怎麼在這裡吃起檳榔、衣著隨性、還睡在廂型車上…他們有的還會帶牙膏和口紅來給我,說看我這樣很心疼,覺得我受苦了。」
她總笑笑地回應,她明白,到台東時,她早已決定把過去的自己整個拋掉、預備重生。
離開了山,海邊的漂流木成了她的啟蒙老師。2003年,她在都蘭糖廠有個名為《穿越》的作品,便以大量的漂流木組件而成,線條如土石流般地流動、又像條生猛的龍,反映著她的實境與夢境。
在舊好茶的山上,她看到的是一棵棵活的樹木;而在台東海邊,每每看到漂流木,卻像是一具具屍海般的殘駭,她想:「它們從哪裡來?哪裡的山又崩落了?」漂流木不只引領她思考土地議題,更喚起她回首自己從原鄉遷徒到異鄉的命運,而她從小常做的夢裡,她總在一大片森林中穿梭,她記得,在夢裡,她仰望天空,陽光就從頭頂撒下…
夢裡是活,海是邊是死,而在撿拾與重組的過程中,她又進入夢境中舊好茶水源地,看見它是活的,看見母親揹著童年的她在舊好茶水源地游泳…完成作品過程猶如一次次帶她穿越時空、重返原鄉,「我才發現我好舊好茶的連結好深、好深,創作過程一次次把我帶回原鄉。」
歷經失根之痛 她一次次用作品重返舊好茶
離鄉再遠,她從未想過,有天會再也回不了家。然而,2009年,一場八八風災,讓原鄉完全消失,山崩土落、路毀橋斷,族人大舉遷村,被安排進入山下的永久屋,再也回不去故鄉。
那時開始,她再也不去海邊撿拾漂流木,只要一看到,她就聞到屍臭味,久久無法平復。她幾乎停擺了創作,即便這些年她名聲漸起,邀約很多,但創作總讓她花盡積蓄、有一餐沒一餐地過;而失去了故鄉,那種漂浮無根的感受太過強烈,族人間原本緊密的關係,一下了山,開始因利益而發生的變質,更讓她痛心…
2016年,她終鼓起勇氣跨越,以《消失前的最後嘆息》一作,回應這份創痛。這是個有多個組件的複合式作品,有攝影、燈箱和編織雕塑。安聖惠以扭曲向上的一具具黑色編織物呈現,像是頻頻在惡夢中出現的變形物件。在組件之一〈分享、獵人、母親〉中,以三張圖片組成,第一張是一雙手撫摸著頭髮,第二張以雙手捧著獸骨,第三張則是將獸骨遮住了臉龐。象徵魯凱族媽媽會留住頭髮給女兒作頭飾的文化,也在反應獵人在分享的同時,也面對著死亡,交付出生命與部落分享;另一系列影像〈母親的花園〉訴說的是母親與土地的關係。
部落是回不去了,但,透過作品,她能一次次重新去咀嚼這土地曾帶給她的美好,如回到子宮裡被療癒一般。

這創痛與療癒交錯的能量一路帶著她,11年後,她鼓起勇氣,決心從部落新址,徒步走回部落應在的地方。她一路慢慢地走,從已被沖毀的地方出發,尋著記憶及可能是人走過的路,去閱讀她生長的土地,一路哭得亂七八糟,11年後變化很多。
途中,她看到遇到維修古蹟的族人,正在崩裂的山坡上敲打採集石板屋的材料,她非常震撼,那是隨時會崩裂的所在,也是要重建家屋必須的採集所在⋯⋯是否,崩裂與重生,必得是一體兩面的命運之途?
當創作不只為了自己,還為了留給未來的一點觸動…
下山後,她創作了《Ali Sa be Sa be/土石流,我在未來想念祢》。一樣以其擅長的複合裝置結合影像,將過去部落的影像與編織作品互相呼應。她永遠記得,父親在她小時候常跟她說:「你『未來』一定會知道。」當時她不懂,經歷失根的創痛,她想著,她有未來嗎?11年後,她開始明白,「現在」在做的每件事,都不再只為了自己,也是為以後的孩子和族人。
「如果能藉由這些作品,對現在或未來的孩子,能產生觸動,哪怕是一點都好,或許,正是我創作的價值。」

2017年,她曾到凱道及228公園支援原住民歌手巴奈的抗爭。當時,她看著巴奈和那布在公園裡飽受日曬雨淋,而某天有個老師拿了一堆巧拼來送給他們。他看著這些巧拼,覺得非常溫暖,她突然知道自己可以為此做些什麼。
她把她們拼成一個像石板屋的作品《光與黑暗》,像個家的庇蔭,更是把部落的溫暖帶給曝露在外的巴奈,成為黑暗裡的光。

離那個當初因質問「還有什麼可能性?」、第一次離鄉的叛逆年少,峨冷已走的很遠很遠了。從離鄉、返鄉、再離鄉、到故鄉成為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她說,她從不後悔離開,遷徒本是原民的命運,一生都要接受各種轉換,一如她在《夢與夢之間》第一次放棄了自然材質、改用人工的繩子去編織作品,這個媒材的轉換,就像她抽離原生的環境,面對新的環境生長,儘管如人工材質般的有毒,但也給了她追夢的能量與空間。
她知道,不管是走到哪裡,她都會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與作品,她的作品就是她的根,不只為了自己,還為了在未來,留給孩子與族人的那一點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