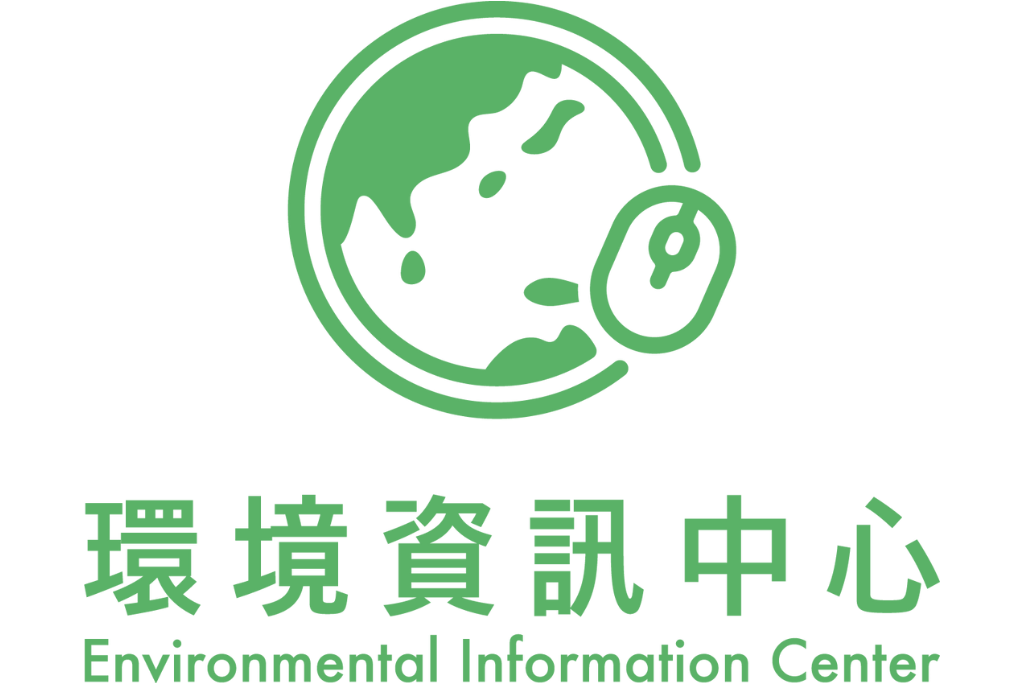2002至2003年冬天,台江國家公園發現73隻黑面琵鷺死於肉毒桿菌中毒。肉毒桿菌中毒是遷徙海鳥的主要傳染病。由於在遷飛路徑上,牠們會在濕地集中棲息,這又加劇了該傳染病的傳播。因此台南野鳥協會舉辦了一場為黑琵接種肉毒桿菌疫苗的運動。
他們用仿誘黑琵訓練工作人員,讓工作人員了解在為黑琵接種疫苗時該如何確保安全。此後,學會便定期安排演練活動,用假鳥教導護鳥人員如何謹慎操作。為了用GPS追蹤黑面琵鷺的遷徙途徑,仿黑琵還被用來引誘真黑琵。在捕鳥陷阱附近,學會也安置了一些木製黑琵,漆上黑白色用來仿誘。

2013年4月29日一早,我看到三隻黑面琵鷺。牠們在前一晚遭捕獲,旁邊還有十隻立在濕地上的木製仿誘黑琵,用來吸引牠們進入陷阱。台灣的賞鳥者說我很幸運,過去幾個月他們一直都沒能捕捉到黑面琵鷺,而那天他們竟然一次捉到三隻。
那天上午日頭很烈,賞鳥者便在濕地堤岸邊的道教廟宇遮蔭。他們放了一些佛經音樂來安撫鳥兒。一名女士溫柔緊捧著一隻黑琵,另一名戴手套與口罩的男子則輕輕把衛星追蹤器縫掛在牠的胸部。其他五名賞鳥者興致盎然地看著他們,一邊拍照,一邊評論黑琵的反應。突然間,黑琵試著掙脫,逃到了廟的角落,還在那裡拉了一坨大便。但他們重新抓住牠,並且繼續縫掛追蹤器。
這位先生向我解釋,因為這是一隻年輕的黑面琵鷺,所以必須非常小心縫掛追蹤器,避免追蹤器的重量妨礙牠的成長,或者造成飛行不平衡。他們用同樣的方式為另外三隻黑琵裝上追蹤器並繫上彩色標籤。之後,便把牠們野放到最近的池塘。黑琵們慢慢走到池塘中央,展翅飛走了。
身為觀察者,這一刻真的令我非常感動。我看到科學與宗教融合在一個保護環境的動作裡。正如我在第四章提到的,放生在道教和佛教儀式中很常見,但也引發人們對放生動物健康的關注。不過,當台南的賞鳥者把模擬實作加入一場儀式裡時,他們考慮到了這些倫理問題:他們照顧這幾隻個別黑面琵鷺的福祉,而牠們又成為整個物種的哨兵。在香港的演習中,志工交替扮演行動者(actors)和假人的角色,同樣地,在野放的模擬中,黑面琵鷺也交替扮演著被動的仿鳥和具抵抗性的活體生命。

在談論檢傷分類的人道問題或者追蹤環境狀況的時候,人們常使用犧牲的語彙:為了照顧必須急救的人,症狀不那麼緊急的病人便成為犧牲;為了保育整個物種,個別動物因為戴上衛星追蹤器而死掉則是不得不的犧牲。
但我所觀察到的模擬實作,卻避開了這樣的區別。它們使用仿誘裝置創造出非尋常的情境。在這種近乎儀式的秩序裡,誰是行動者(actors)的問題——鳥或人?——遭到了擱置。在模擬的時空中,常規生活裡病人與醫師、動物與人類的緊張關係都被懸擱,因為在模擬之中,具仿誘作用的人造物負責處理這些緊張關係。如同我們在第四章所見,哨兵並未被犧牲,而是打開了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認同空間,而在這裡,我則將其描述為禽鳥儲體裡的倒轉情節。
黑面琵鷺的野放與我未能觀察的其他演習產生共鳴。在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脈絡裡,這些演習混合了軍事與公共衛生的考量。自從911後發生的炭疽信件,台灣的疾病管制中心便一直在預測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物恐怖攻擊,並舉行了多次演習,模擬在公共空間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形。
2003年3月到7月間的SARS危機似乎確認了這種恐懼,當時台灣有668人遭此來自中國的冠狀病毒感染,其中181人因而死亡。當時,SARS危機被視為台灣衛生部門的一次挫敗,儘管在這之前,台灣衛生部門曾成功控制了瘧疾、肺結核、登革熱等傳染病。因此2004年9月22日,台灣的疾管局在台北市政府舉行了SARS病毒的生物恐怖攻擊演習,此外也分別於2005年4月14日和同年12月8日在台北捷運舉行了天花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生物恐怖攻擊演習。
2005年10月,時任疾管局局長郭旭崧告訴台灣媒體:「就預備工作而言,台灣目前的狀況比2003年SARS來臨時要更好。」2005年後,郭旭崧又依據美國疾管署的模型,會同台灣的國防部舉行了數次演習 ── 台灣的國防部之前便會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模擬人民解放軍進犯的情況。
長期以來,台灣海峽一直是人們進行模擬與盤算的地方。17世紀時,明朝將領鄭成功(又稱國姓爺,華人台灣的奠基者)準備從福建沿海侵略當時被荷蘭人佔據的台灣。在福建,他為士兵發明了一種改編自傳統擲骰遊戲的「中秋博餅」。遊戲裡,不同的骰子組合對應到特定獎品,用以顯示士兵的好運道。廈門的一座鄭成功像至今仍在紀念這一遊戲的發明。
位於廈門兩公里外的金門島也曾是模擬與演習的場所:從1949年蔣介石的軍隊侵入該島,將金門視為反抗人民解放軍的基地,到解嚴後台灣軍隊於1992年撤離該島為止。此後,金門成了保存自然與文化遺產的空間,尤其深受賞鳥者喜愛。
就此脈絡來看,在這同一個海峽的黑面琵鷺野放活動就變得很有意義了:它所傳遞的不是敵我間的潛在戰爭訊息,而是鳥類棲息地變化的信號。這信號既關乎鳥類,也牽涉到人類。透過這重新發明出來的儀式,鳥類疾病的模擬實作把哨兵職責指派給某些生命,監測南中國海上將至的危險。
因此,禽鳥儲體裡的模擬實作包含了幾種邏輯:安全(防止來自邊境的威脅)、科學(透過計數生物而生產知識)、宗教(透過集體物〔collective objects〕在人類與非人類之間建立認同)。流行病的模擬串接了兩條系譜:一條是冷戰時期的演習,另一條系譜則更為久遠,牽涉到獵人與動物打交道的實作。
本章的最後兩節便將考慮禽類疾病的這個雙重系譜,探討在裡頭,遊戲、虛構與儀式有怎樣的關係。相對於前面幾節以民族誌的方式描述公共衛生官員與賞鳥人士的模擬實作,後面兩節則更為理論性一些。我將從比較的視角去看演習的各種面向。

作者:弗雷德里克.凱克
譯者:陳榮泰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12月20日
ISBN:9786267209646
1957年亞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2003年SARS危機,直到2019年Covid-19,伴隨養殖產業的密集發展,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且很可能仍然是)下一波人畜共通傳染病「震央」。
面對中國的資訊不透明,處於震央邊沿的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如何因為地緣政治的條件,發展出不同的預備技術?當公共衛生危機出現,除了把動物及養殖者當成不得不的犧牲,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想像與做法?
作者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這三個哨站進行為期或長或短的多點民族誌調查,走訪病毒實驗室、醫院、家畜試驗所、養殖場、賞鳥者的社群,觀察這三個華人社會應對禽流感威脅的各種預備工作,包括突發疫情的監測、病毒變異的模擬、病毒資料的儲存與疫苗和藥物的儲備等。
本書透過人類學對牧養社會與狩獵社會的討論,開展一連串的視野轉換,以批判的眼光分辨大流行病預警工作裡經常混雜不同的語言,如為了維護多數、優勢者或者人類的安全而犧牲少數、弱勢者以及動物的維安話語。
面對將會一再侵襲人類社會的病毒,我們需要借助其他生命形式的察覺能力,以及人類社會與動物一同生活的多樣經驗,發揮其他想像和實作的可能,警覺可能發生的改變。
作者介紹
弗雷德里克・凱克(Frédéric Keck)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資深研究員,法蘭西公學院社會人類學實驗室成員,研究主題涉及哲學史、科學人類學、風險社會學、環境研究等,著有《流感的世界》(Un monde grippé, 2010)、《預警信號:病毒傳染、社會正義與環境危機》(Signaux d’alerte. Contagion virale, justice sociale, crises environnementales, 2020)、《以備不測:列維-布留爾與警覺的科學》(Préparer l’imprévisible. Lévy-Bruhl et les sciences de la vigilance, 2023)等。本書曾獲2020年法蘭西學術院頒發的羅森(Léon-de-Rosen)獎,表揚對促進環境意識有貢獻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