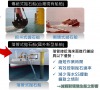四
 在昆蟲的世界,性交的姿勢勉強可以作為種類區分的參考。蜻蜓是浪漫的「心」形,椿象則以尾端相接、頭各東西的「一」字形。蟬呢?蟬以特有的「V」字形,勝利之姿交尾。
在昆蟲的世界,性交的姿勢勉強可以作為種類區分的參考。蜻蜓是浪漫的「心」形,椿象則以尾端相接、頭各東西的「一」字形。蟬呢?蟬以特有的「V」字形,勝利之姿交尾。
交尾後的雌蟬究竟是如何在植物上產卵?卵孵化後的若蟲又是如何回到土裏將自己囚進黑暗呢?我沒有幸運目睹,或者說我還不具備足夠的耐心與敏銳的觀察力得以幸運目睹。書上的確可以找到一些「蟬如何……」之類的解答,但這些解答通常過於簡單、片段。有助於滿足考試需求,卻無法安撫自然觀察者的好奇心。蟬的產卵與孵化的連續過程,有太多失落的環節,在我腦中打著問號。就像地質層與層之間出土的化石,在物種演化的歷程,呈現不連續演變(或說跳躍式改變)。古生物學家找不到一個物種演化到另一個物種的中間型物種。好像老鼠是一夕之間就變成了飛鼠,飛鼠一個縱身滑行,竟拍翅成蝙蝠。
我像看著一部每隔5分鐘只撥放10秒的電影,中間的4分50秒斷訊,靠著一個個不連續的10秒,我要拼湊出整個劇情。如何補齊蟬的產卵與孵化後落土的失落環節,變成一種渴望。直到法布爾的《昆蟲記》才安撫我的一顆心。法布爾用了約一萬個字描述「蟬的產卵與孵化」,射入眼中的字句一旦填補了渴求得知的失落環節,我就會有一種驚歎「原來如此」的領悟。至今我仍記得翻閱書頁時有一種微微顫抖自指間流向書頁。那種感動不知道會不會輸給實際觀察到的那一刻。法布爾的《昆蟲記》,對於喜愛觀察昆蟲的人,幾乎有一種令人感動的「天啟」,以詩般魔力。至少,對我而言。
「交尾後的雌蟬,會擇一較乾的枝條,以約一公分長的產卵管穿刺樹枝。由下而上約刺孔30 ~ 40個,一個刺孔產6 ~ 15個卵不等,每一個刺孔要工作約十分鐘。「蟬喜歡陽光,選擇的都是最容易曬到太陽的方向,只要牠的背部沐浴在陽光中,對牠來說就是莫大的樂趣。」30 ~ 40個孔合計花費六個小時左右。於是孔洞隨太陽移動呈螺旋形而非直線排列。雌蟬產卵同時,寄生蜂也忙著幹起消滅蟬卵的勾當。為了看見卵孵化出若蟲,法布爾觀察了百束蟬卵枝條卻悉數失敗。終於在一個冬日早晨,就著火爐的溫暖,不抱太大希望的法布爾觀察著一束蟬卵枝條,竟喜出望外,看見一隻蟬的若蟲鑽孔而出,在洞口脫皮,沐浴陽光,強壯身體,「等待一個微風,搖晃擺動,在空中翻個跟斗降落。」接著,法布爾安排了鬆軟的土壤讓若蟲得以鑽入土裏,但想要觀察到若蟲吸食根部汁液的等待卻落空了。或許是若蟲需要冬眠,等待春暖才開始進食的緣故,也可能是食草不對。總之,春回大地,法布爾搗碎土塊,找到的卻是已然死去的若蟲。這是法布爾對南歐熊蟬產卵與孵化的觀察。」
以上,是我在閱讀完法布爾一萬字的描述後整理的筆記。這份筆記只能記錄蟬產卵與孵化的「原來如此」,「驚歎」則夾在書本,等待下一回再被翻閱。至於流向書頁的「微微顫抖」,也流入記憶,常駐在腦葉的某一章節,等待被再次閱讀。
五
若蟬在土裏一直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以刺吸式口器插入植物根部,飲汁為餐,深居簡直不出,直到終齡。擇日出土的終齡若蟲,攀岩般爬上一棵樹,等待禪機,胸背一聲響裂後,隨即開出佛性,然後羽化,升天。
蟬,在晉人陸雲的《寒蟬賦》中,成了五德兼備的君子:「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古人對蟬的生態習性,不但觀察細微,更將這些特徵、特性有所對應,想像力豐富。
曹雪芹在《紅樓夢》說女人是水做的,蟬何嘗不是,一生只飲植物的汁液。羽化後的成蟬,更是每飲必醉,醉後則詩發歌狂,唱的是李白的調。
蟬聲唱過一個個暑假,陪伴昔日童年的歡笑。也辛勤邁力如同頂著烈日的農夫,為延續蟬脈而聲嘶力喊,直到氣斷。如果你同我一般曾試著徒手捉蟬或以鏡頭近拍一隻蟬,你大概也嚐過蟬的孤傲與對人的睥睨,撒一泡尿,然後一走了之,留下尷尬的你,瀟灑有如自由奔放的李白。
孤傲與自由註定不幸的命運。天寶三年,李白不得已離開長安,蟬也被迫漸離了都市。道路、校園、公園的樹,像是從水泥地長出來的,樹下沒有土,只有水泥。土地無法呼吸,終齡若蟬無法爬出土表。離去是命,也是一種解脫。都市從此沒有李白醉後奔放的詩歌,蟬則隱入山林,從此唱空靈的調。
空靈的調,是我第一次到雪山坑山蘇林聽到蟬聲時的陶醉。那麼靜、那麼靜的林子,樹冠群撐住天,林下則缺乏灌木,是一片空曠的視野,山蘇在樹腰間附生,有一種原始的況味。好靜的林子只聽見蟬聲誦唸如台語發音的「知了-知了-知了──」,有一種莊嚴,更多是空靈。這裏是台灣難得的淨土。
沒有蟬聲的地方,好比校園不再教授李白的詩。當李白的詩,不再成為可以繼續傳衍的「瀰」,我們的文化就少了一個可以美的基因。如同我們的生命將遺忘某一種色彩,聽覺將失去某一頻率的感知區段。當蟬聲遠逝,生態的喪鐘隨即敲響。那將是一個逐漸邁向黑白、死寂無聲的夏天。
六
隻蟬,可以摧毀一個宇宙,以蝴蝶效應。這是人類參不透的禪機。
七
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像是兩個極端。但真的沒有妥協的餘地嗎?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地帶嗎?我們肯定回不了原始自然,人類也並非真的想要返歸蠻荒,即使真的想望著狩獵採集的生活,也必然是古老而遙遠的夢,回不去的鄉愁。
保留原始棲地作為生物的原鄉,不是我們對其他生命的施捨與恩惠,是生命之間彼此的、最基本的尊重。即使是都市化的環境,也該文明,而非野蠻地獨佔土地,完全不考慮可以或願意與我們共同生活的其他生命。一隻蟬,也是一個生命。如果可以的話,他們願意在路樹、校園、公園繼續歡唱夏日情歌。
如果可以的話……
吳明益在《蝶道》有段文字說:「人類本身也是自然的一員,我們所改變的世界,不需以回歸荒野為唯一的依歸,但至少至少,可以在進行任何『改造』自然的行為之前,把其它生命考慮進去。比方說,將步道稍稍架高,讓印度蜓蜥可以不必時時被腳步驚擾;比方說,在屏鵝公路架一座高架橋,讓擬相手蟹降海繁殖時,不必帶著被來往車輛碾斃的悲壯;比方說,種一株路樹時,考慮是否能讓都市裡的其它生命共享。」
蟬就是需要一株路樹的生命,不只如此,他還需要泥土,僅僅一小塊可以讓終齡若蟲爬出的泥土。水泥無疑絕了蟬的生路,也絕了夏日如李白一般醉人的詩唱。設若台灣熊蟬這類標記著台灣特有種的生物,因棲地的消逝而滅絕,意謂著我們的地球將永遠失去台灣熊蟬的野唱狂歌。每一個台灣特有種都是台灣最珍貴的瑰寶,他們以台灣作為唯一的家,世世代代。台灣之所以美麗,正是豐富的棲地孕育多樣的生命。誠如賈福相說的:「不同就是大同。」
「不同就是大同」是賈福相教授生物多樣性多年後思考而得的觀念,看似簡單,卻蘊含深刻的禪思。不同生命間因著食物網的關係,充滿生存的衝突,如何能夠和諧相處,達大同境界呢?這需要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彼此「尊重」。畢竟,對任何一種生命的趕盡殺絕,都是對生物多樣性的傷害,也是對生態系穩定度的一種瓦解。最終,仍會反撲自身。吳明益在《迷蝶誌》的一段文字更提醒,若我們「遺忘與其他生命交往的能力,終有一天,人類也會寂寞的死去。」
八
帶學生出遊,我鮮少解說。而是要他們睜大眼睛,敏銳觀察。我要他們看見生命,而非背誦知識。自然的知識早在未被名詞定義,未被學理實證以前就存在於大自然。有時,我會覺得不停以倍數出版的自然書籍,像是悼念生物的一篇篇祭文。當生物倍數死去,關於他們的書卻倍數增長。我們的下一代少了與生命的真實接觸,卻多了藉由書本與這些生命隔著時空而交會。這是一種反智的悲哀。
一個不曾和我們生命交會的生命逝去,不會引發我們悲傷。家養的寵物死去,傷心必然更勝一個陌生人的過世。台灣黑熊多舛的命運,比不上動物園外來的無尾熊之死令台灣人傷悲。並非台灣人不願意關心台灣黑熊,而是我們對台灣黑熊的認識太少。如果蟬與我們有生命的交集,我們也願意尊重蟬與我們共享這塊土地的權利,我們會願意為他們保留一棵樹,以及樹下的一塊泥土地。
我不知道一棵樹,一塊泥土地和一小批因此而生的蟬能帶給生態多少實質的貢獻。但我相信,學生與蟬交會的時刻隱藏著參透生命的禪機。
一隻破土而出的若蟬,有永生不朽的秘密;
一枚蟬蛻,如一朵蓮花,隱含佛性;
一泡蟬尿,閃現無所不在的道;
…………
九
一隻蟬,也可以撐起一個宇宙。這禪機,人類是否參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