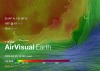本月初,意外受邀與過去的一位老朋友,目前剛自「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的項目總監離開的環境運動工作者盧思騁,對談中國環境運動與台灣環境NGO角色的題目。
作為一個沒去過中國的台灣環境工作者,原本應該少發點言,並請像「環境資訊協會」這些幾年來一直辦理兩國環保團體交流實務經驗豐富的朋友,出席主要 與談人。但因盧是大學時代特地來台灣「學習」環境議題行動而與我認識的朋友,加上彼此的國際主義觀點以及環境議題立場都很接近,尤其從2008年開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就有一位資深成員常駐北京,透過「綠色和平中國分部」,就近觀察中國環境議題和主要組織的發展,所以就先由我擔起與談人的角色。而參與座談的多位環境資訊協會幹部的踴躍發言,也消除了原本的擔憂。
不出台灣的「國家鄰避型環境抗爭」?
我與盧的對談,意外地變成他報告自己對台灣環境NGO拜訪後的觀察。這位來自香港,幾乎是「綠色和平」進入北京等中國城市的奠基者,認為台灣的環境NGO活力十足,但思考的前瞻性與全盤性沒有過去吸引人了(我對他的說法的詮釋)。
我想,對環境行動者來說,國籍、國界與社會規範雖然是既存的社會構造,但是生態環境體系的鏈結絕對不受此限制。照理說,受限制來源不可能沒有,但卻 是社會本身建構出來的,來自於行動方案和解決方案的各種資源裡有部分會受限於國籍、國界與社會規範。問題在於,環境行動者是否沒有必要意識到這個矛盾,是否可以將感動和理性的關懷侷限於感官可及的範圍?
或許,盧思騁想提醒台灣NGO團體的是:台灣夥伴團體,是否發起和結束都仍未徹底擺脫鄰避效應的環境意識?答案如果不是,那麼環境行動者對造成生態受破壞的生產與消費行為,就不能避免回答這個簡單問題:為了迴避在我國社會所應承擔的環境與社會成本而外移的污染性產業和高耗能產業,是不是因為出了我們 的社區(國界),就不再是我們應該主動監督或約束其生產行為的對象?
有感於他和同事這趟來台觀摩的感嘆,我因此直接回應,盧思騁領導的「綠色和平中國」,給我們最有深度的啟發,在於其環境議題行動策略不是著眼在污染 的在地因素,而是污染的資本所有者因素。換句話說,台灣民眾面對的污染性產業即使離開了這塊土地,仍然是那個有污染前科的企業移到中國土地上,如果其生產過程不變,利潤來源不變,不管所污染土地的「國籍」為何,都是地球生態體系的損失。
我們或許也可以由此再反省,民眾用地域劃分而無持續行動的社會慣習,或許是台灣環境NGO組織成為一小塊一小塊各自經營成長受限的互動影響。
中國生產與污染增長模式 台商貢獻不小
會參與這場座談的聽眾與環境行動者一定都意識到,不管就台灣還是世界這20年來的企業動態來說,中國是全球產業鍊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節點。其重要性也已從之前的製造基地,很快在未來可能正式成為主要消費市場。如果中國不能擺脫按照傳統的發展模式,成為污染與碳排放大國的可能性當然就在眼前。據說中國國 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都這樣說:「中國的污染狀況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上。」
排名前三的中國發電集團,其2008年燃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總和,已經超過了同年整個英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水平。世界銀行在已公開的報告中說,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1千億美元,大約是GDP的5.8%,這相當於中國全年的GDP增長的一半,也就是說,全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半被環境污染浪費損失了。過去世界銀行曾有一份報告指出,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獨佔16個;排首位的是四川的攀枝花市,還包括北京、上海 和香港等。
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製造了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而其中台商與中國各地政府的友好關係也扮演一定角色。譬如,2007年引起廈門和漳州兩地居民集體抗議的PX化工廠的投資者,是台灣的落跑商人陳由豪,也就是說,台灣的東帝士集團跑到中國變成廈門翔鷺集團。於是有毒的PX化工廠不在台灣建設,而在 中國大陸建造。
可以說,中國大陸現在的所有環境污染,很多都是引進外國的嚴重污染生產系統,都是外國不要在本國建造的污染工廠,整批整批地轉移到中國大陸來。我們 曾為了鹿港、麥寮,為了高雄潮寮鄉而憤怒,但那些離開的企業資本到中國去,當地民眾打出「寧願自己死,不願子孫亡」這樣台灣環境抗爭常見的訴求,我們的同理心卻出不來了?未來我們還是選擇低調回應?
不管我們自己的立場是傾向台灣繼續獨立還是與中國統一,台灣的環境NGO夥伴也都知道這樣一個事實早已發生──中國因素,已成為台灣目前許多企業和政府官員施政裡的所有思維。
台灣NGO需要的新行動框架
台灣NGO如果要與政府以及企業交手,必須有一套清楚的思考脈絡。例如我們反對在台灣繼續設置石化、鋼鐵廠,但是當這些廠家一旦是出走到對岸,我們反而好像失去了繼續氣憤或行動的理由。試想如果東帝士陳由豪引起的對岸抗爭被重視,社會大眾不就能更清楚看到,台灣社會真的沒有對不起陳由豪,他到對岸去 也沒有鹹魚翻身,那個大搞財大氣粗、利益政治、不顧民眾環境權的企業所有者,從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再者,台灣NGO對台灣政府的政策影響力,在陳水扁執政後期以及目前的國民黨全面掌控下,已日益下降。原因之一也在於企業西進的中國因素,政府與企業將對岸的廉價環境成本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籌碼。這幾年環境影響評估對企業監督的不符期待,可能就是受到「吸引資本續(回)留台灣」這個優先前提的影 響。若能找到中國進步的NGO,共同合作,對中國政府與中國設廠的企業先形成壓力,或許已是值得不斷嘗試修正的NGO大方向。例如把「綠色和平中國」對主要電子業廠商的製程和排放污染的監督,轉化為台灣NGO回向施壓給台灣政府對同一企業台灣廠區不得放水的籌碼。
環境行動者善用台灣、中國「雙重標準」這個槓桿,或許反而能擺脫依賴環評對生產開發資本限制的無力感。譬如台商在中國必須遵守的部分資訊公開的法 律,可能比台灣法律嚴。所以透過合作關係,讓台資或中資企業不能純粹靠政治裙帶關係和法律標準差異東飄西走,鑽縫靠污染成本低而假裝成成功企業。簡單地說,像陳由豪這種利用兩國民眾在社會相關資訊上的不對等,利用政治把戲漠視污染源的環境責任與社會期待的化工企業,屆時才會真願意正視民間力量。
中國因素下的NGO合作基礎萌芽
上述策略評估中有一個必須注意的變化是,中國政府或許為了民族形象,或許是正視環境污染的責任,口號上確立了世界上最為積極的耗能減低目標,要求在 2006年至2010年間,該國的單位GDP能耗減少20%。如果這一目標真能實現,短短5年內,中國必須減少15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較歐盟在 《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從1997至2012年15年間承諾的減排量3億噸高出許多。此外我們也應該要意識到,中國政府面臨的環境危機與環境技術市場的壓力或許是等量齊觀的。也就是說,中國政府與企業也注意到搶進綠色產業市場的利益,因此中國開始有許多政府默許下的環境資訊和諮商型NGO團體出現。以上這些都可能是兩國NGO組織合作機遇。
台灣環境NGO要在行動上跨出新局,徹底擺脫「鄰避型環境行動」的侷促體質,透過合作監督有污染前科的兩地資本而形成政策壓力,讓跨國集團承認兩國的環境監督機制。當然還有首先必須克服的行動障礙。就如我在對談裡順帶指出的一點,因為兩岸間的政治不透明度與社會運行機制的差異,目前常見的經驗是,透 過偶一聯繫拜訪建立起來的夥伴關係,的確要面臨信任關係不足的反動力。為了克服這個初始的可能障礙,一個綠盟嘗試中的合作議題與方式或許可先拋出作參考(這個經驗分享也是在與環境運動工作者盧思騁的公開對談裡,我試著鼓勵在場會眾,提出第一步行動的可能性一點都不難)。
垃圾危機與政策的翻轉:民間先行
大家或許還依稀記得上世紀90年代在台灣上演的鄉鎮垃圾大戰。在那個極度依賴傳統掩埋處理的年代,為了垃圾的去處,不同行政區與社區居民間因為掩埋場處理量的爆滿,多次爆發垃圾進場的攻防戰。當年環保署(郝龍斌任內)解決的對策,是鼓勵補助「一縣市一焚化爐」做為解決垃圾問題的政策。綠盟的前身「環 盟台北分會」時期,則從不斷參加各地反垃圾進場的民眾抗爭經驗中意識到,串連各社區反對力量,不能只是在降低垃圾鄰避效應的消極層次(這樣只是垃圾處理選址時間的消耗),而是可以、也必須整合成進步垃圾政策的提出動力。於是在綠盟於2000成立後,反焚化爐反垃圾掩埋場的民間動員,轉變成「垃圾減量就能解決垃圾問題」此一觀念翻轉的先驅。
比較鄰近香港、中國的狀況,台灣家庭廢棄物政策的變革(尤其是反焚化爐及垃圾減量)是華人世界(這裡我不想用種族畫分,而是從飲食習慣和乾濕家庭垃圾的結構的近似性)寶貴的經驗。
例如最近,綠盟同仁參訪了反對在北京市海淀區六里屯興建垃圾焚化廠的議題參與者。他們的處境,類似於當年反焚化爐,但還未確定垃圾減量此一觀念翻轉 可以達成的台灣社區。因此當地人士都很感興趣,希望進一步藉由資訊交流及未來來台實地參觀,學習該運動中的垃圾危機程度、時間點、政策施力和民眾反對意識教育等幾個環節如何與何時搭配的技術。
更重要的,當年綠盟的社區結盟操作模式,例如聯結「看守台灣」和邀請的戴奧辛專家,結合社區居民全國經驗分享(例如北投焚化爐居民監督團體等),更 是我們提醒中國環境NGO,要達到政策共識軸線翻轉前必經的歷練。當然,綠盟在中國垃圾議題的合作上,透過社區結盟這個模式,也提醒自己應該多了解當地的家戶廢棄物處理特性的社會脈絡,未來才比較能精準一點的提出建議。
從社區不鄰避到國境不鄰避
環境行動必須累積與轉化成社會具體支持度的實力(綠色和平中國在香港有1萬5千名固定捐款認養者),看穿結構性限制而提出戰略評估,也是行動者集思廣義的必修功課(跨國企業與鄰避效應的環境對策),兩個課題依賴和互補。這是我從當年來台取經環境運動、如今已經能大膽指出台灣環境NGO組織侷限的演講者所具備的思考脈絡裡,得到的最大刺激。願與環境運動前輩和同事們共享。
※本文轉自苦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