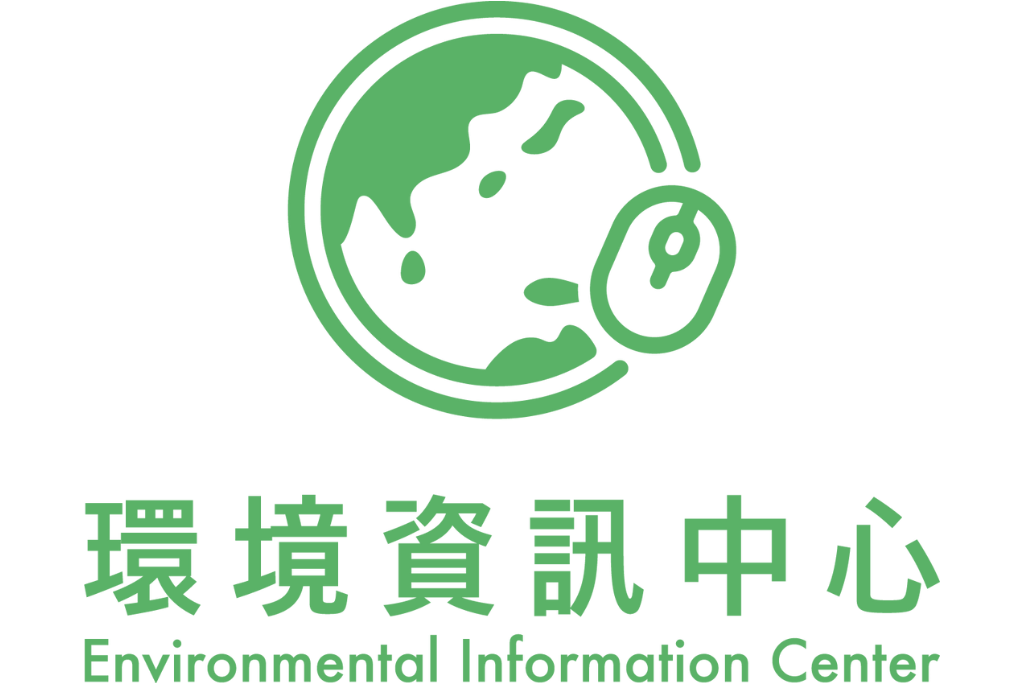但會議結果難以否定鯊魚生存普遍受到威脅的處境。作為一種傳統美味,全世界有一半被消費的鯊魚魚翅,或者最終消失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或者在這裡停上一段時間,隨後去往最終的目的地。這些魚翅,大多來自易危甚至瀕危的鯊魚種群。 3月底,「中外對話海洋」在香港這個全球海洋瀕危物種貿易樞紐之地舉辦研討會,探討瀕危海洋物種保護之道。

會上,專家認為推動物種加入CITES名錄只是第一步。要實現對物種的有效保護,還需要更多貿易相關環節的有效協作。
海洋生物進入「搶救名單」
CITES是管制瀕危物種跨境貿易的國際公約,於1975年生效。它的三個附錄,列入了因受貿易威脅需要專門跨境貿易管制的物種,其中附錄一物種完全禁止國際貿易。
海洋物種在CITES框架下受到管制是相對近期的事。除了石首魚等在1975年第一批列入的物種,直到2002年,在CITES公約生效二十多年後,才有新的海洋物種海馬被列入,更多的海洋物種要到2010年之後才會被CITES和各國關注到。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教授薛雯琦(Yvonne Sadovy)認為,將受威脅物種加入CITES公約名錄,限制其貿易,對該物種保護十分重要。薛雯琦研究海洋生物已有數十年,她主要研究的珊瑚礁魚類有不少面臨過度捕撈的威脅。
不過,確認一個物種受到威脅並不容易,尤其當它一直被當作「食物」看待。中國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主任助理曾岩指出,FAO會參與CITES提案物種的評估,但它對經濟性魚類列入一直不太支持。 「原來有提案要把黑鮪魚列入CITES名單,但是後來沒有通過。」薛雯琦說。黑鮪魚是日本壽司原料,隨著日本料理在全球風靡,這個公認的「頂級食材」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追捧,種群數量也隨之下降。一些黑鮪魚亞種雖然在IUCN紅色名錄中被列為「極危」,但並未進入CITES名單。
而在中國,「除了列入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名錄的物種,其他的水生物種都是在《漁業法》下作為經濟性資源進行管理的。」曾岩說。中國《漁業法》現有版本中沒有要求對上岸漁獲進行登記,導致根本無法確認某些魚類的存量,更無法進行永續管理。 「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管理這塊資源方面存在很大挑戰,因為這涉及到很多漁民的生計。」薛雯琦說。
執法難題
一個物種進入了CITES名錄,是不是就進入了執法者的雷達範圍?理論上是這樣的,因為按規定接受CITES管制的物種進出口,受到進出口國家嚴格的管制。但這仍難擋非法販運。
「大概只有10%(甚至更少)的非法販運會被罰沒或截獲。」ADM Capital基金會(ADM Capital Foundation)環境項目主任古素芬(Sophie Le Clue)介紹說。那些「過關」的非法商品,有些是沒有被發現,有些則是沒有被認出來。
走私方法多樣,其中有幾個問題比較難處理。一種是運輸公司本身並不知道運輸的是走私品,而無法協助管理部門執法,另一種是假藉其他合規商品名義運輸非法商品,這在集裝箱運輸中最為常見。至於借助小型漁船繞過正規口岸上岸,就更難監管了。
被非法販運的物種活體或物種製品,有一部分通過肉眼可以識別它是否來自一個被管制的物種,有一些則無法識別,其中就包括各種各樣的魚翅——「你也許能用肉眼識別它們的成體,但是不同的幼體很難識別。」古素芬說。
還有不少走私品比魚翅更難識別,例如鯨魚牙齒、海龜殼製品、乾魚鰾、以及乾魚鰓,通常對執法人員來說,都需要藉助專門技術來來識別。曾岩和同事曾經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識別膨魚鰓。
膨魚鰓是蝠鱝的魚鰓乾品,在亞洲部分地區有將其入藥的民間習俗,用於治療麻疹、乳汁稀少等。 2012年CITES提案要保護前口蝠鱝,並指出其主要貿易地在中國。由於它沒有載入中國藥典,中國協助履約的研究人員也對其了解不多。為了給執法人員進行培訓,他們到市場上採購了200多個樣品,通過形態結構判斷、DNA檢測、並藉助電腦分析判斷特定種的特徵,幫助執法人員判斷哪些魚鰓來自需要管制的蝠鱝。
另外,執法力度的不同也會影響貿易路徑。販賣價值約兩百萬的石首魚魚鰾,在中國內地判刑高達八年,而類似案件在香港最高刑期不超過兩年。量刑差異,會讓一些不法之徒選擇避重就輕,走風險更小的地方走私。 「只要堵上一個法律漏洞,就可以解決很大的問題。」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韋凱雯(Amanda Whitfort)說。
根本問題
由於履約不到位,很多CITES名錄中的物種仍然在減少。例如墨西哥加州灣的石首魚,雖然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列入了附錄一,仍然持續減少,導致其最大兼捕受害者——同樣生活在加灣的小頭鼠海豚現在只剩下不到30頭,瀕臨滅絕。
一直幫深圳海關鑑定走私品的汕頭大學海洋生物學鄭銳強博士認為海關執法不是問題的終極解決方案。因為事情一直在變,包括執法的對像都可能發生變化。 「有海關人員透露,象牙貿易被禁止之後,在海關查到的鯨魚牙齒突然多起來了。」鄭銳強說。
這不是孤例。 BLOOM Association香港分部海洋項目總監佘國豪(Stan Shea)參與的一份調查發現,香港魚翅消費經過多年環保倡議開始下降後,許多消費者認為可以把花膠、海參等納入到宴席菜單中替代魚翅。花膠(即一些魚類的魚鰾乾製品)和海參,都同樣存在瀕危物種貿易問題,不過很多消費者並不知道。他們可能也不知道,為了滿足亞洲市場的花膠需求,遠在東非肯尼亞維多利亞湖的尼羅河鱸魚現在也面臨過度捕撈的威脅。

曾岩認為一種被管制的物種有替代品是正常的,但比起一個接一個地追著保護特定種群,更應該關注貿易和消費的根本目標——什麼樣的需求是合理的和永續的。 「我們需要的是更大層面的策略和框架,找到漁業和永續保護之間的平衡點,找到更合理的解決方案。」她說。
「很多時候,大家認為中國幾百年上千年的飲食偏好沒有辦法改變,但我覺得並不是這樣的。」悉尼科技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邁克爾.法比尼(Michael Fabinyi)發現,不論是關稅政策,還是市場宣傳,或者人為造勢,都可能會影響到一些海鮮的消費,比如中國政府的反腐行動就使得北京市場奢侈海鮮消費顯著下降。
佘國豪認為,是文化決定了我們會吃什麼,也決定了我們的未來。 「年年有魚」是中國人的文化。 「我不希望我們這一代被後人記住,是因為我們把魚都吃光了。」
參考資料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打擊瀕危海洋物種貿易,難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