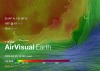車子離開秀巒進入新光部落,山裡頭的燈光越見稀少。大部分時間,窗外是一片墨染漆黑,圍繞在莫氏樹蛙的鳴聲中。今年最大最圓的月亮早已經隱沒在山稜線的那頭,羊腸山徑緊緊地夾擠在黑壓壓的森林間,車窗外的聲響透露著鎮西堡荒山的神秘。唯一的光亮只剩車燈,時而橫掃向樹林、時而照射在芒草叢。零星的野狼機車從遠處斷續打燈過來,與我們交會。
他們親手打造夢想家園
黑暗中的阿道家外頭懸浮著一卷白茫茫的寒意,在車燈的照射下噴湧翻捲。車子熄火後,耳朵又重新浸泡在四周黑暗的聲音裡頭清洗乾淨。新建的二層樓民宿,是主人與部落鄰居一起親手打造的。寬闊的空間、描繪泰雅傳說草稿的高牆、精美的草蓆刻花天花板、樸拙的原木樓梯、完全以樹幹、年輪橫切面、木屑、竹篾,一點一點地鋪排、裝飾、拼湊、雋刻。我們跟隨著主人的解說參觀,心中不斷發出喟嘆,也忙著以相機記錄下眼前所見。
主人說:第一次蓋房子,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用木頭的原因只是因為山上木頭便宜。可是我們舉目所見,卻是自他心中浮現的理想,醞釀而成的一份藝術作品。想想山下的室內設計,此時也相形見絀、顯得呆板與匠氣。這份粗獷自然的氣息、這份屬於山林的特質,又怎麼是過慣物質文明的城市人所揣摩得出?
從鳥鳴聲中揭開序幕
聽見鳥叫聲就睜開眼,似乎是上山工作的人很快就培養得出的生活習慣。鷹鵑的怪叫從昨晚就一直沒停過,不知道是在傳遞晚春的訊息,還是尚未找到可寄生的白耳畫眉巢。收拾好背包、套上雨鞋,迎向綠之海的洗禮。
從昨天晚上起,聖傑儼然已成了鎮西堡部落的代言人。宗以、小P不斷地發問,熱烈討論起原住民、部落與土地的關係。我和阿德則認真地當個聽眾。事實上我已經有整整兩年沒能上來鎮西堡,兩年間也都不曾著雨鞋行走調查路線的崎嶇山徑,一切記憶得重新喚起與適應。當初隨聖傑上山是他樣區調查的初期,而現在已是他的調查實驗接近收尾的階段。
學長用了一個早上的時間不疾不徐地帶著我們走進林間,巡迴樣區。他說:樣區調查的進度事小,未完成的都可以留待下一次進行。希望我們跟一次調查上山不只是學會了幫忙調查該學的事務,而能夠對樣區的概況、檜木林生態、以及鎮西堡部落,有更深的了解。從瑣碎的物種辨認、雜交現象、發現新種、植物與地形演育的交互關係、到地球上最古老的森林形成與更新;我看到一位樂於分享他發現和領悟的研究者、一位未來的植物生態學者,不厭其煩地帶著我們在森林裡來回穿梭。
伴隨崩塌而生的生命更新
樣區中一片很典型的自然崩塌地,已經成為檜木林自然演替更新的溫床。不要小看這片土石夾雜崩落、林木傾倒的不穩定裸露地,我們行走時可需要步步為營;不只是顧忌個人安危,一個不留意,恐怕就一腳印踏扁了一株萌芽一年、兩年的小紅檜、小鐵杉了。
紅檜從種子萌芽的時候,葉子呈簇生的針狀葉,不仔細看還以為是比較大棵的土馬鬃,兩三年以後才開始出現鱗片狀葉漸漸取代針狀葉,(學長說這是一種植物界有趣的「重演」現象,幼年時的樣子像它演化早期的祖先)一年、兩年、三年,高度不過一兩公分、兩三公分。這樣微小脆弱的生命生長在這片破碎的崩塌地上,卻有足以橫度超越數千年時空的能力;當週遭的闊葉樹、灌木、藤蔓、草本、地被… …輪番枯槁、世代交替,它們卻日復一日以極緩慢的速度茁壯拔高、蔓生根系、延伸枝條,也目睹這一片因河流上源侵蝕新崩壞的土地,經過漫長光陰重新填滿綠意、披覆綠衣。它們的生命已與土地長久地緊密相連、生息相通、牢不可分。在這兩三千年的歲月裡,從成熟以後就年年結果,灑下為數不少的細小種子,帶著一點點的薄翼隨風飄送,等待的只是數十年至幾百年為週期的另一次大規模崩塌地出現。從此陽光又灑滿土地表層,為它們撫育小苗,另一個兩三千年的新生命週期於焉重新開始。
調查紀實
我們在古老的檜木與樟殼闊葉混生的混淆林下行走,踩著年復一年編織的大地衣裳、落葉、枯枝,與檜木林優勢的地被植物、瘤足蕨、赤車使者(一種類似樓梯草的蕁麻科)。野外經驗豐富的宗以一路上隨時為我們播報鳥的叫聲和行蹤,頑皮的書德則認真地撿拾葉片,在手中觀察把玩。
早已過了春雨霏霏的清明,水晶蘭的花期也過了,林下只餘晚開的一兩株。陽光滲入林間空隙,樹冠層傳來一陣比一陣熱鬧的鳴叫。我們在帽沿和衣服上噴上一點樟腦油,以驅逐惱人的蚊蟲荼毒。在這片生機盎然的森林底下,先找到樣區標旗、拉起樣區繩和中間線,展開一塊十公尺見方的樣區調查。記錄板上畫好樣區方格、座標,以S形掃過樣區中的每一棵樹,在方格紙上分別標上胸圍超過三公分的每棵樹的位置,並記錄樹種、胸圍、高度、冠輻、枝下高、傾斜角、地下分枝、地上分枝,掛上編號牌… …,最後記錄地表覆蓋率以及地被植物。
如果只是把調查當作這些記錄與標號的工作反覆,任誰都會很快地感覺枯燥無味。
展讀林間意趣
在林子底下鑽來鑽去的時間這麼長,不難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比如說:觀察一棵樹,我不免思量著:樹木如何適應環境,取得更多的日照?如何克服崎嶇陡峭的山坡地形?一棵可以穿出樹冠層的樹、一棵在茂林下生長的樹、一株藤蔓、一棵蕨類… …它們似乎各有自己的生存哲學。
曾經看過一棵森氏櫟,它的種子在一棵阿里山櫻的根部上面發芽。為了接觸土壤,森氏櫟伸出長長的根,包住阿里山櫻的樹頭。若非仔細觀察還真難看出誰纏繞著誰。這兩棵森氏櫟與阿里山櫻都已分別長成二十公尺高的大樹,並且同時歪向一邊再向上展開樹冠,爭取更多陽光。隨著兩棵樹越來越粗大,重量不斷增加,不知道會不會有那麼一天,阿里山櫻再也承受不了森氏櫟的重量而漸漸枯槁?這又需要多少年的光陰,我們才知道它們彼此是相互競爭、還是合作共生的關係呢?
八角金盤在檜木林陡峭的地形中,常長出一些延伸很遠或往下生長的地上分枝,樹高為零或負值;細枝柃木幾乎都長出好幾個地下分枝,每個分枝沒長多少葉子,我和阿德每次都得為冠輻與枝下高的估計討價還價一番;毽子櫟的葉子長得像毽子上的羽毛,樹皮表面會塊狀剝落,但是又該如何與可以雜交的森氏櫟區分開來;有時樹木長得太高看不見葉子,得要觀察它低處的萌蘗、或以望遠鏡觀察高處的葉…。
一棵大紅檜的新生得仰賴傾倒死亡的老檜木讓出林間空隙,站在枯倒的大樹上成長,根系再向下延伸深入泥土;而枯倒的大樹還同時孕育了其他多樣的生命:各種耐陰的闊葉樹在倒木上、從倒木底下,發芽、開枝展葉;藤蔓依附著倒木攀爬向上;苔蘚植物、蕈類、地衣、也紛紛以倒木為家,並以極緩慢的步調使大樹殘軀漸成沃壤…。
我們在林間穿進穿出,解讀著這些樹木的生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