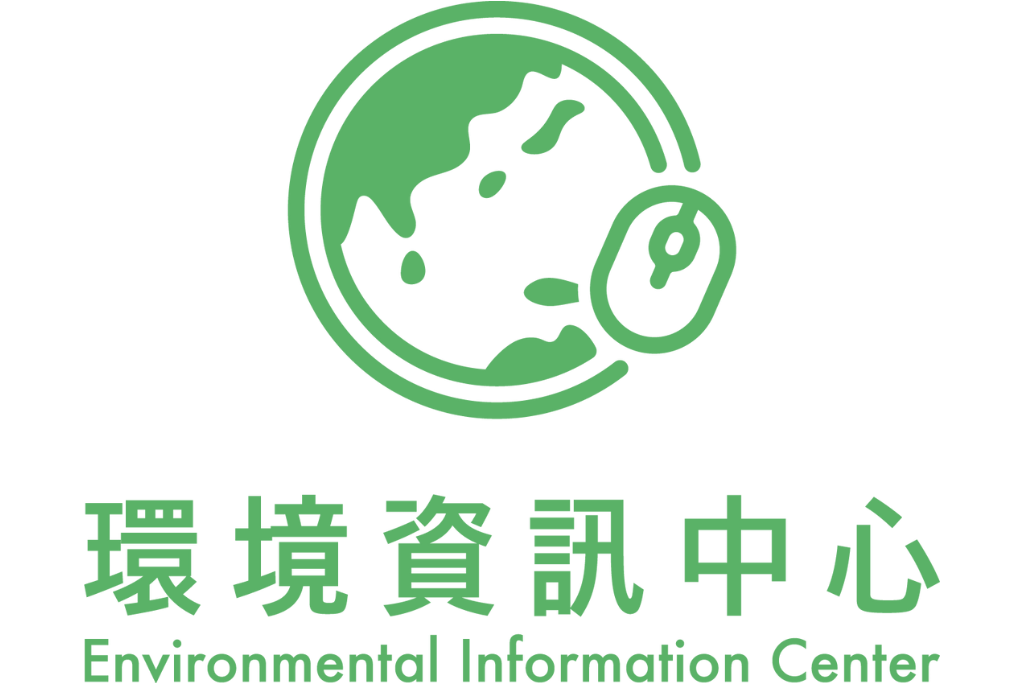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遠古沒有田,從前沒有穀。前人吃草根,後生啃茅草。山里有野谷,穀棵長得稀。穀子生在遙遠的紅水河,穀種長在天邊的彩虹下。是遠古的祖母,是從前的首領,把它們找回來。」
《穀源歌》從幾十米外的一丘稻田裡傳來,那裡有二十多位盛裝的壯族婦女正在收割稻穀。遵守之前的約定,我們不能與她們搭話,不得干預她們的勞作,甚至不能靠近那片稻田。這個禁忌不容置疑,是我們得以參與期間的前提條件。空曠的田野間偶爾有嗚叫的小鳥飛過,伴著潺潺的河水聲,婦女們的歌聲像是從遠古飄來。古老的稻作民族都在講述稻穀起源的神話:大洪水時代,萬物絕滅,祖先重新找回了穀種。

九龍山神祭
「雞年屬羊的那一天,狗年屬鼠的那一日。水稻難栽培呵,穀子要水田。開田那天祖母死了,栽秧那天首領去世了。稻穀難栽培呵,不死這棵死那棵。種了一代又一代,才有今天的種子。」
她們遵循著祖先的禮儀,唱著穀種起源的古老歌謠,在收割一種紅色的糯穀。這是為來年春天祭祀九龍山神而準備的祭品。有些不可思議,婦女們正在覆行著不知延續了多少個世代的農耕祭祀手續,那是一部自野生稻馴化以來的數千年間,稻作文化中所保存的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的歷史。那一刻你會忘了外間世界正在發生著的糧食危機,忘記正在發生的河流與土地的污染,在婦女們的吟唱中回溯我們早已遺忘的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那是在神穀收割的前兩天,雲南文山州古籍辦公室的王明富來電話,那貝村的村長通知他,神田馬上就要收割了。我連夜趕往文山,與王明富一道換了三次車趕到者兔鄉,再趕到村裡。者兔在雲南東南部的山谷間,它鮮為人知,卻是雲南壯族的神聖之地。一條清澈的河流從狹長的壩子間流過,從進入山谷,四周山巒滿目蔥綠,彷彿進入另外一個世界。這一帶是野生稻的發源地,壯族亦是中國南方最古老的稻作民族。
典型的壯族村莊格局是依山而建,不佔用珍貴的河谷平地。寨前是稻田,寨後有山林,田間流淌著清澈的溪流。壯語稱稻田為「那」,村莊大多以「那」命名。傳統的力量守護住著九龍山的森林河流,也守護著山下的稻田。儘管商品經濟的影響正在進入山谷,但九龍山下仍然保存著傳統農業社會的寧靜和美麗,這在今天的中國鄉村已經不多見了。
神山祭儀
九龍山是滇南壯族地區地位最高的神山,儘管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九龍山依然是不容外鄉人涉足的禁地。神山面積約一萬畝,名字源於山中流出來的九條河流。在壯語裡,九龍山叫「賽傑金洪傑旦」,原意為:「遍布黃金的大地之王,流淌著瀑布的山之王。」它主導著風雨雷電,關照糧食的豐欠和人畜興衰。
山下的12個村莊守護著神山的寧靜,小心維護著神山的禁忌,不得驚擾山里的動物和植物,不得砍伐山里的一草一木,亦不能污染了水源。每年春天,12個村莊的男人們會聚集到山上祭祀九龍山神。祭禮至今延續著禁止外人參與的古俗,甚至附近的壯族亦不得參與,只能在自家遙祭。近些年,古俗引來許多人的興趣,祭禮主持者們也絕不讓步。
去年雲南省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部門希望與村裡溝通,對祭禮進行拍攝和調查。地方政府出面做了許多工作,村裡長者都沒同意。最終,主持者無奈,只得讓由摩殺雞占卜。占卜通過了,拍攝者也如願參與了祭祀,可後來聽說,外人離開後,村裡對外鄉人介入的這次祭禮依然心存不安,開天闢地以來都沒人做過這個決定。他們開了這個先例,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災難,他們擔當不起。最終,祭祀重新進行。
稻種的魂魄
祭禮九龍山神所需的酒和糯米飯的來源,就出自我們前面的這丘稻田。緊鄰一條清澈的小河,神田面積不到一畝,形似一隻飛翔的小鳥。在周遭稻田的包圍下,它一目了然,因為神田裡的稻穀區別於所有的稻田。它是一種淵源古老的神秘稻種,神田不能被外人耕種,神穀的種子亦不能為外人栽種。壯語稱:「那訇(ㄏㄨㄥ)、扣訇」,意思是稻田之王與穀種之王。在人們心目中,那是大地上最神聖的稻田,穀種中最大的種子。那是在春天的祭祀裡專為九龍山神準備的食糧。甚至雲南壯族地區的送魂路線,都與這片古老的神田有著密切的關係。

「扣訇」是一種淵源古老的紅色糯穀。中國自商周時代起,祭祀使用的就是糯米,但連科學家都不知道糯稻從何而來。栽培稻是從亞洲多年生野生稻馴化而成 ,但野生稻中沒有現成的糯質野生稻。神田由神山下12個村莊裡姓陸的人家輪流耕種,壯語「賀那訇」,即種神田。陸姓是當地最古老的居民,輪到哪家,哪家就得盡心盡力去耕作,栽秧和收割的時候,主人發出邀請大家會去幫忙。從栽種到收穫,神穀都要尊從一套密不示人的儀軌,其中就包括著我們不能與收割的婦女們說話。穀種絕不能讓外人耕種,否則會有災難發生。
我們趕到神田所在的那貝村的那個早晨,參與收割的女人們正在做準備。女人不得參與春天的祭祀,但是為九龍山神栽種收割做祭品的穀子卻是她們的責任。10月,山間一片金黃,被主人邀請來收割的鄉鄰親友頭一天就要沐浴更衣,第二天一早就帶著全身的銀飾從各村趕來。這是一次盛裝的勞作,與栽秧時一樣,收割者需要無病無痛,家裡也要無災無難。那天早上為了打包頭,花了不少時間,傳統的包頭方式蠻複雜,打不好就纏不穩。由於平時已經不用包頭,中年以下的婦女已經不會打了。最後把村裡的老奶奶們請來,才把問題解決了。
我們見了一位83歲的老奶奶,她是一位通靈者。民間稱她們為「乜滿」或「乜洪」。與其它通靈者不同的是,老奶奶能看見九龍山的諸神,諸神後面跟著山中的生靈,如馬鹿、飛狐、猴子、麂子、野豬、野雞、兔子、蛇和禽鳥。九龍山的神靈透過夢示告訴她祭祀的禮儀。她說:「九龍山的神,個子跟我們差不多一樣高,從很遠的地方來。」老人家甚至還能看見稻魂,「它們像蝴蝶一樣會飛,有時會飛到家裡來。哪家對它尊敬就在哪家,不愛在又飛走了,它飛走就會把糧食也帶走。」在傳統裡,稻魂也承載著人魂,稻魂走了,這個家庭是不會興旺的。

守護神山的子民
且不論民間信仰中超出我們認知範圍的部分,然而,正是傳統的力量守護住著九龍山的森林與河流,維護著山中一草一木,也維護著人們的生態安全。水稻是高度依賴水源的農作物,水稻耕作系統與水的複雜關係,決定了森林和水在文化傳統中的地位。稻作者對環境本能的認識,通過神話固化了他們的生態倫理觀。
那臘的村長說,神山周圍到處有神蹟,每年都有許多的祭禮。那臘村旁的「石祖」,就是他們每年3月間,屬龍或屬羊的那天就要殺一隻雞和一頭豬去獻。問他那個石頭立了多少時間了? 「哦,立了很多代人了。作用是保福保佑我們寨子,田地不好,水會沖垮。年年都要供。不供不得。不供就會烏風暴雨,人就不好在了。即使在文革期間,他們悄悄來祭。」村長說。
神山由山下的12個村莊共同守護。護林隊是民間的,每個村莊出的每個家庭輪流擔任,由村裡出150斤穀子做酬勞。雖然政府也有護林員,但年輕的巡山隊員說:他們不希望由政府來保護,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真正守護住神山。

當然,者兔不是世外桃園,者兔的田園牧歌也面臨危機。農耕生活展現的不僅僅是的田園意境,還有稻農生活的困境和危機。人口的增加,在土地面積不改變的情況下人們便轉向產量更高的雜交稻。耐病蟲害的本地稻種被拋棄了。本地稻種包括糯穀在內約有七八個品種,只要不再栽種,它們就面臨著滅絕的危險。與其它物種不同,只要它們被碾成米煮熟了,這個存在了千百年的物種便消失了,包括那些陪伴著人的生命旅途在召魂中使用的特定稻種。
農業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常常在高科技的幌子下被忽略,傳統稻種所蘊藏的豐富基因,恰恰關係著人類未來的食品安全。雜交稻需要大量的化肥和農藥。為了對付病蟲害,人們使用很毒的農藥,如樂果、甲胺磷,甚至被禁用已久的敵敵畏。老鄉們也知道,農藥打多了,秧雞沒有了,青蛙和蛇少了,也傷害到了許多野生動物。這兩年鼠害成災,他們也知道其中的關聯。
深陷於外來稻種包圍之中的神田,與周邊的稻田相比,生長並不茂盛 。在新一代年輕人那裡,種神田漸漸成為負擔。眼下,神田和神谷還按照傳統的耕種,但未來會怎樣?古老的稻穀之神是否會因為現代科技而走下神壇?在今天中國的鄉村社會,美麗與貧困,富足與污染,似乎成了一個悖論。
神穀收完了,唱著古老的《穀源歌》,婦女們挑著神穀回家了。她們要把稻穀送到來年九龍山祭祀主祭者家裡。這些關係天下安危的神穀,將待在那個小閣樓上,被謹慎地照看著,等待著來年開春的時候,被釀成米酒,蒸成糯米飯,烹調成獻給九龍山神的盛宴。然後是另一戶人家接過種子,繼續它們的生命和文化旅程。九龍山下的眾生百姓亦在其間承繼古老的傳統,從中獲取對生活的力量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