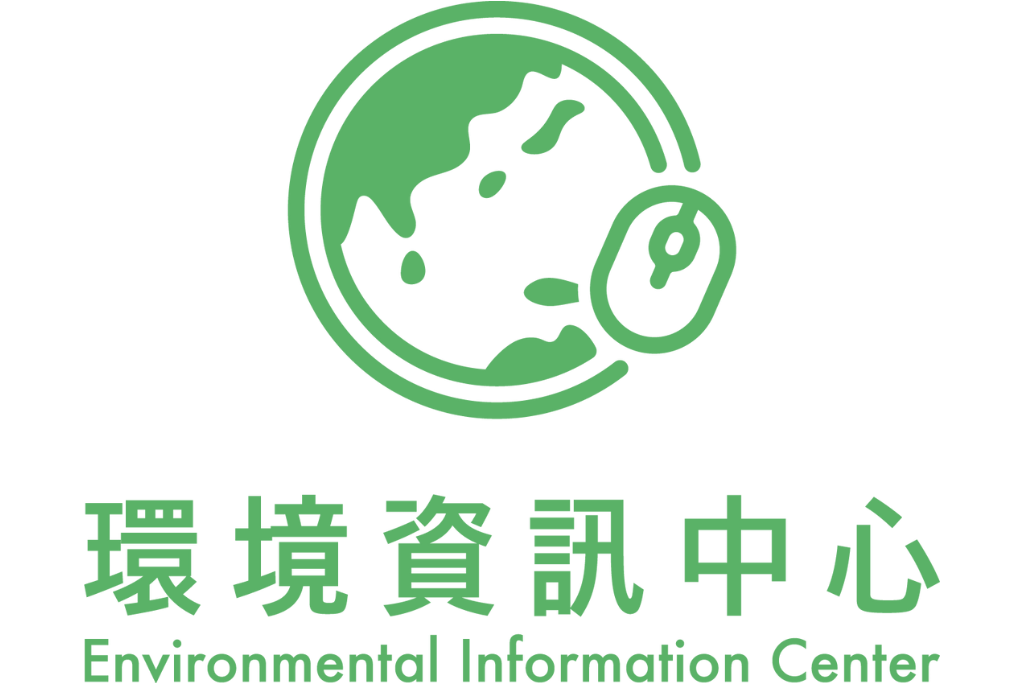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如果對土地沒有愛、尊敬與讚賞,
或者不重視大地的價值,
人與土地的道德關係也就不會存在。
當然,我所指的價值遠比經濟價值還要廣泛,
我指的是哲學層面的價值。」
李奧波
一、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保育生物學家時常把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對許多外行人而言,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並不這麼明顯。由於保育工作需要廣大的民眾支持,保育生物學家必須能夠很清楚地向一般人陳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為什麼我們要關心生物多樣性及其價值?
環境哲學家經常把價值分為兩大類,並使用兩組相應的詞彙,即:工具性價值或功利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 or utilitarian value),對應於固有價值或原生價值(intrinsic value or inherent value)。工具性或功利性價值是指某物成為達到其他事物的目的時的工具,因而具有的價值,而內在或原生價值則是指成全某物本身目的的價值。人類的內在價值很少引起爭論。但非人類的自然實體和整個大自然本身的內在價值,則經常引發許多爭議。也許正因為非人類的自然實體和大自然本身也具有內在價值的觀念,不但非常新穎,而且具有爭議性,所以一些傑出的保育學家(Myers 1993)都寧願從純功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為何要保存生物多樣性。這種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純粹建立在只是為了要達到人類目的時的工具的觀點,我們稱之為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即:以人類為中心,human-centered)。另一方面,生物多樣性存在的本身就具有價值,而不是因對人類有用才具有價值的觀點,則稱為生物中心主義(biocentric)。
工具性價值
從人類中心主義為出發點,生物多樣性的工具性或功利性價值可分為三大類:商品、服務和資訊。生物多樣性的心理-靈性價值則可能被列為第四類功利性價值。
第一種是商品的價值。人類消耗許多其他的生物,把它們當作食物、燃料、建材等等。但在所有的生物當中,才只有一小部分已經被調查過,確認它們在食物、燃料、纖維和其他商品上的用途。許多潛在的食用植物和動物,可能尚待發掘。這當中有些是可以用園藝或農業方法的規模來種植,有些則可以直接在野外採收。這樣,至少可以使人類的飲食具有更多變化,甚至當傳統作物發生無法治療的植物疾病或無法控制的蟲害時,還可以使人類能夠免於飢餓(Vietmeyer 1986a,b)。熱帶森林中可能有快速生長的樹木──可當作木柴或木炭,或用來製造紙漿或木材──但尚未為人發現。有些植物可能具有製造新有機殺蟲劑的用途,只不過人類尚未發現而已(Plotkin 1988)。在這一大類中,有些尚未被發現或分析的動植物可能具有醫藥潛力,似乎成為在保存生物多樣性時,最受歡迎和具有說服力的原因。自馬達加斯加長春花(Madagascar periwinkle)提煉出來的vincristine,是治療孩童白血病的最佳藥物(Farnsworth 1988)。這項在1950年代末期發現的療效,經常被用來當作例證,說明最近從生物中提煉出來的藥物,對癌症具有驚人療效,但這些植物的原生地卻正遭到全面性的破壞。無疑地,還有其他許多未經分析、或甚至尚未被人發現的物種,也可能具有同樣重要的療效──前提是我們要先拯救它們才行。
如果我們任由物種滅絕則可能會失去潛在醫藥的論點,經常為保育學家所引用,這種情況值得我們深思。它反應出當代西方文化對醫葯持有高度的尊崇──這種文化具有憂鬱症的傾向。我們要不計代價地拯救它們,因為尚未探勘的生態系中可能存有能治療人類疾病的解藥!Meadows(1990)曾指出,「有些生態學家對這類推理極為厭惡,甚至稱之為『馬達加斯加長春花論點』...〔這些〕生態學家厭惡這種論調,因為它既自大又陳腐。它假設地球上數百萬種物種,都是為了提供人類經濟用途才存在的。即使你相信這種論點,它仍然會忽略掉大自然對我們所提供的其他更寬廣更有價值的服務方式。」
這牽涉到第二大類,即服務的價值。對於那些主要把自己視為「消費者」的人,其他物種在複雜但協調的自然經濟中辛勤工作所提供的服務經常是被忽略掉了(Meadows 1990)。綠色植物補充大氣中的氧氣、吸收二氧化碳。有些能替開花植物、甚至許多農作傳授花粉的昆蟲、鳥和蝙蝠,正以可怕的驚人速度步入滅絕(Buchmann and Nabhan 1996)。土壤中的黴菌和微生物,能分解死去的有機物質,在植物養份的循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根瘤菌能把大氣中的氮變成植物可利用的氮肥。如果蓋婭假說(Lovelock 1988)是正確的,那麼地球的溫度和海洋的鹽度就是由有機物來調節的。人類經濟只不過是自然經濟中一個小的子系統而已,如果在較大的自然經濟中,重要的環境服務系統瓦解的話,人類經濟也會立即崩潰。
第三,資訊價值。無知地摧毀「不關心或未知」的物種──套用Alfred Russel Wallace(1963)的話,他跟達爾文同時代、且是自然選擇演化論共同發現人──就像在大型圖書館的某一區中放火,燒掉還沒有人讀過的書一樣。每種物種都是一個資訊寶庫。在可隔離的基因中可能藏有我們想要的特徵,可以利用基因接合的方式移轉至可食用或具療效的資源上,但這些原本找得到的「書」,卻可能被「燒掉」。換句話說,基因資訊是一種潛在的經濟商品。這種資訊還有另一種很難描述的用途,但Meadows(1990)卻闡述的很清楚:
生物多樣性中涵蓋許多大自然所累積的智慧,也是攸關大自然的未來關鍵所繫。如果你要摧毀一個社會,最好的方法就是燒毀其圖書館,以及殺死它的知識份子,亦即摧毀它的知識。大自然的知識存在生物細胞的DNA內。各種不同的基因資訊是促進演化的動力、也是生命的免疫系統、以及適應力的來源。
目前世上有一百五十萬種生物已經被正式命名並加以描述。最保守的估計顯示,地球上的物種總數約在五百萬至一千萬之間,這代表科學界才發現其中的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而已(Gaston 1991)。根據最寬鬆的估計顯示,地球上的物種總數約在三千萬種左右,這代表科學界已知的物種只佔百分之五不到(Erwin 1988)。根據Raven(1988)的預測,若是潮溼的熱帶棲息地遭到大量破壞,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內,導致百分之二十五的未知物種滅絕的話,科學界的損失必定很大。
這些受威脅的物種中,絕大多數不是維管束植物或脊椎動物,而是昆蟲(Wilson 1985b)。Erwin(1988)認為世上有這麼多無脊椎動物,是因為許多是特有種或寄生物種。大多數瀕臨滅絕的昆蟲,可能都無法當做人類的食物或醫藥──無論是當做有機體、化學萃取物的來源或基因片斷的來源──許多在區域生態系的功能上,也並未扮演重要的角色(Ehrenfeld 1988)。雖然我們很難以這種無情的觀點來看這件悲劇,但我們可以用純粹的功利價值主義來解釋這些損失──視其為潛在非物質類商品的損失,即人類在動植物知識上的損失。
第四,心理-靈性資源。Aldo Leopold(1953)希望,民眾可以透過科學培養出「對自然物體的精緻品味」。一隻甲蟲也許又小又平凡,但它可以跟任何藝術品一樣美麗。Soule(1985)認為,幾乎所有人都會喜歡自然界的多樣變化──豐富多元的動植物──而不會喜歡單調性。Wilson(1984)發現在大自然中充滿奧妙、敬畏與神奇,──他稱這種感覺為「親生命」(biophilia),對他而言,這幾乎就是自然史宗教(a religion of natural history)的基礎。Norton(1987)認為,因美麗的生物和健康的生態系而感動,或是對大自然中無盡的奇蹟感到讚嘆與敬畏時,能使人變得更好。
如果從資訊價值的觀點來看──遺傳等方面──無知地毀壞生物多樣性,就像燒書一樣,從自然美學和宗教的觀點來看,它就像故意破壞畫廊或褻瀆教堂一樣。現在一般人大多相信純科學知識的價值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而自然的美學價值和靈性價值,則被視為是一種比較誇大的功利主義價值。Ehrenfeld(1976)認為,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美學和靈性原理,「仍然根植於人類中心和人本主義的世界觀,這正是使包括我們在內的自然界,成為現在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然而,有些人認為自然的美與神聖,是一種內在價值,而非工具價值。Sagoff(1980)就曾提出,「我們喜歡一樣物體,因為它是有價值的;我們不因為自己喜歡它們,才認為它們具有價值──美學經驗從以前就一直是對於某種價值的認知。」
內在價值
內在價值跟工具性價值不同,它無法被區分成不同的類別。有關內在價值的討論,一直是以另外兩項議題為焦點:那些東西有可能具有內在價值,以及內在價值是否為客觀存在的、亦或是主觀賦予的。
鑒於目前對人類破壞非人類生命的憂慮日益高漲,一些當代哲學家已不再遵循西方的宗教與哲學傳統,而把內在價值──或其他不同的名稱──認為是下列各不同領域的屬性:有強烈意識的動物(1983);有感覺的動物(Warnock 1971);所有生物(Taylor 1986);物種(Callicott 1986;Rolston 1988; Johnson 1991);生物群落(Callicott 1989);生態系(Rolston 1988; Johnson 1991);以及演化過程(Rolston 1988)。Leopold(1949, 1953)把「哲學方面的價值」──這裡他所指的只可能是哲學家所謂的「內在價值」──視為「土地」的屬性,土地的定義為「居住於空中、地上、地下的所有生物」(Callicott 1987a)。Soule(1985)肯定地斷言「生命多樣性具有內在價值」,而Ehrenfeld(1988)亦確認「價值是多樣性本質中的一部分。」
認為內在價值是客觀地存在於人類和其他生物中的環境哲學家認為,有機體跟汽車或吸塵器等機器不同的地方,是在於「自行製造的」(autopoietic)-自我組織與自己指導的(Fox 1990)。汽車是被製造的;換句話說,它無法成長,也不受本身的DNA調整。汽車的目的-運送人類,以及賦予車主一定的社會地位-是由外界所設定的。機器不具有本身的目標或目的,這跟有機體不同-機器既不會有意識地選擇目標,也不會由基因來決定目標。有機體本身設定的目標是什麼?答案可能很多,而且很複雜。對我們人類而言,這些目標從贏得奧運金牌、到儘量看電視都包括在內。但是,所有有機物都會努力(通常是在無意識狀態以及在進化的意涵下)達成一些事先設定好的基本目標-成長、達到成熟、繁殖。(Taylor 1986)
因此,顯然有機體才會有利益,機器是沒有的。例如擁有充分的陽光、水和肥沃的土壤,對橡樹有利,雖然橡樹可能不是主動對擁有這些東西感興趣,就好像吃新鮮的蔬菜對孩童有利,但孩童可能只對垃圾食物感興趣。有些人可能會提出反論,認為以此類推的話,定期換機油也是對汽車有利的事,但是由於汽車的目的並不在其本身,所以保養良好也不是對它有利,而是對它的使用者有利;汽車只為滿足使用者的目的而存在。會努力追求或興盛繁衍的有機體才有利益,換句話說,它們本身就具有好處。但是「好處」其實就是「價值」。因此,承認有機體有利益-本身具有好處-就等於承認它們具有哲學家所謂的「內在價值」。
內在價值和工具性價值也可以同時存在;許多事物的價值,可以同時從它們的功利和其本身來判定。例如,老板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評定員工的價值。同樣地,本質上就具有價值的生物多樣性,也可以從不同的方式來判定它具有工具性價值。
有些環境哲學家和保育生物學家宣稱,生物多樣性具有內在價值(或在本質上是有價值的),但Norton(1991)認為,這種論點對保育的傷害比幫助還多。為什麼呢?因為內在價值的問題,使保育學家分成互相猜疑的兩派:人類中心主義者和生物中心主義者。後者把前者視為「膚淺的資源主義者」,而前者則認為後者已走到無法自拔的深淵(Norton 1991)。如果生物多樣性很重要,是因為它能確保生態服務能持續下去、代表許多潛在的資源、滿足我們的審美需求、在宗教上啟發我們、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其實際結果就跟我們認為它具有內在價值一樣:我們應該保育它。根據Norton的觀點,從工具性上評定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跟從內在上評定其價值,最後都會「趨向於」相同的保育政策;因此,我們不需要以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做為制定保育政策的理由。所以,Norton認為根本不必再討論生物多樣性是否具有內在價值,並認為涵蓋廣泛且歷史淵源長久的人類中心主義,已經可以做為保育生物的理由。
然而,Norton沒有考慮到,將內在價值賦與生物多樣性時,的確會造成非常實際的基本上的不同。如果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跟人類的內在價值一樣,廣為大眾所認可,那麼情況是否會有所不同?由於內在價值很容易為人忽略,因此,任何可能會危害生物多樣性的自然資源開發形式,都不可能完全禁止。畢竟,承認人類具有內在價值並無法完全使人類免於危險,特別是當這麼做能為一般民眾帶來極大的福祉(或稱為集體功用)時,我們往往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內在價值。例如,在1990年時,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士兵被送上戰場,有些因而喪命或受傷,他們的目的不是要保護自己和同胞,使其免於被滅亡的立即危險,而是要確保中東的石油供給,以及達成地理政治上的目標。
因此,如果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受到普遍的認可,那麼,當它受到威脅時就必須要能夠提出正當的理由-這就像我們要送士兵上戰場時,一定要有正當的理由一樣。視生物多樣性具有內在價值實際上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把舉證責任從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保育人士,轉移到可能會危害生物多樣性的開發業者身上。Fox (1993)明確有力地陳述了這一點。
認為非人類世界具有內在價值的論點,會對有關環境的爭議及決策的整個架構造成劇烈的影響。如果非人類世界僅被視為具有工具性價值,那麼人們只要想出各種他們所要的理由,就可以被允許去利用或是任意干涉它們。但是如果有人反對干涉,那麼根據此論點,這些人就必須說明為什麼不干涉非人類世界會對人類比較有利。然而,如果非人類世界被視為具有內在價值,那麼要去干涉它的人,就必須負責提出可合理干涉的理由。
生物多樣性價值貨幣化
使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貨幣化,是經濟學家的技術性工作。在這裡,我們只討論使生物多樣性具有金錢價值的基本方法,以及這麼做所引起的哲學問題。一般人會認為只有生物多樣性的工具性價值,才能夠從金錢觀點來探討。因此,有些環境經濟學家明確支持人類中心主義(Randall 1986)。但稍後我們將看到,在評估保育目標的經濟價值時,甚至連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也可以列入考量。
一些瀕臨絕種的物種具有市場價格:惡名昭彰的例子有:象牙、犀牛角、鬚鯨肉、骨和脂;孟加拉虎的皮等。在一些例子中──例如藍鯨和抹香鯨──貨幣價值是物種瀕臨滅絕的唯一原因。但在其他的例子中──例如孟加拉虎和山地大猩猩──棲息地遭破壞也是其瀕臨絕種的原因之一。但是,Myers(1981)建議,利用其貨幣價值,可能是保育許多物種的關鍵。Holmes Rolston則提出另一個觀點(參看 Our Duties to Endangered Species by Holmes Rolston)。
根據現代經濟學理論,要將一物種的市場價格,從保育負債轉移至保育資產,就是要把它從經濟學家所謂的「公共財」(commons) 的情況,轉移至「圈圍」(enclose)的情況。這裡的「圈圍」指的並不是真的建一道籬笆,把生物族群圍起來,而是要分配宰殺權。在財產權未受到合法保障或維護時,具有市場價值的野生物種就會遭到過度捕獵,這就會導致公共財的悲劇(Hardin 1968)。如果一項資源能被擁有(私有或公有),其財產權也能受到法律保障,該物種就得以保存,此理論能成立,是因為財產所有人不會想「殺鵝取金蛋」。
其他的因素也會使情況更加複雜,例如物種的繁殖率及生長率,和利率、折扣率等的關係。Haneman(1988)指出,「利率水準、淨利益功能的本質及其隨時間的變動、以及資源本身自然成長過程的動力等,都可決定最適合的開發時程途徑──當其他條件保持相同時,未來結果的折扣利率愈高,就愈適合在現在耗盡資源。」
藍鯨就是最佳舉例。國際捕鯨委員會有效圈圍藍鯨族群,把捕鯨的份額分配給捕鯨的國家,不過偶而還是會發生偷捕事件。然而,Clark(1973)卻認為,比起坐等藍鯨族群恢復、並以永續方式捕鯨,直接把藍鯨獵捕殆盡,並把收益投資在其他產業上,所獲得的收益將會比較高。Clark並不是要建議採取這種行動,相反地,他的論點是要強調,單靠市場力量,並不能夠達到保育的目標。
藉由圈圍和永遠捕獵的方式,來保存具有經濟開發價值的瀕臨絕種物種,可能對保存高繁殖率和高成長率的物種比較有用,例如有蹄動物,但是用在低繁殖率和低成長率的物種身上則可能完全沒用,例如鯨魚。因此,藉重市場的力量來保育動物時必須非常謹慎,也要以個案方式來進行。
潛在的商品-新的食物、燃料、藥品等-顯然不具有市場價值,因為它們尚未被發現或被開發。然而,不管怎麼樣,當物種在資源潛力尚未被發現或分析之前就已經滅絕的話,代表未來將無法利用可能由它衍生出來的商品。因此,生物多樣性可以被標上「選擇權價格」,其定義為「人們願意事先付出一定的價錢,以獲得在未來使用此選擇權的保證」(Raven等人,1992)。任何未發現或未分析的物種所具有的選擇權價格,可能非常小,因為特定物種在未來會很有用的機率也非常小(Ehrenfeld 1988)。數百萬種或以上的物種目前有因大規模破壞而滅絕的危機,若把它們的選擇權價格相加的話,數目將會相當龐大。
市場賦予生物多樣性的金錢價值,跟大自然所提供的實際與潛在商品的價值不同。例如,民眾付錢去參觀國家公園,到荒野健行。這類費用-不比牛羚肉排的價格低-多少可以代表生物多樣性的貨幣價值。然而,由於使用者付的費用通常很低,所以若是光看這些費用,心理-靈性「資源」真正的貨幣價值,經常會被低估。在評估心理-靈性「資源」的貨幣價值時,地方、州和聯邦稅捐的補助也可以被列為評估因素之一。民眾到特定地點參觀所花的錢-例如為汽油、住宿和露營設備所花的錢-也可以採用「旅行開支法」記入資源的貨幣價值內。(Peterson和 Randall 1984)。「偶發的價值」(Contingent valuation)也被用來計算心理-靈性資源的貨幣價值(Peterson和Randall 1984),它可對民眾進行抽樣調查,詢問他們是否願意為享受特定經驗的機會而付費,例如到美國黃石公園聽狼嚎。
現在就連經濟學家也確認生物多樣性的「存在價值」(existence value)(Randall 1988)-當然也嘗試使其貨幣化。有些人即使本身沒有品嚐奇異動物肉品的意圖,或是不喜歡荒野的經驗,但是只要知道生物多樣性受到保護,就感到些微滿足。存在價值是有價格的;確定其價格的方法之一,就是計算民眾實際捐獻給保育組織的金額,例如自然保育或雨林行動網路。此外,經濟學家現在也確認「遺贈價值」(bequest value)-為了確保未來的人類能繼承具有生物多樣性的世界,民眾所願意付的錢(Raven等人 1992)。
大自然的休閒、美學、知識與靈性功能雖然經常是免費或被低估其價值,但是,要使這些價值貨幣化的嘗試,遠多過將自然經濟提供人類經濟的服務價值貨幣化。這有部分可能反應出經濟學家所受到的生態教化的程度而已,他們可能愈來愈習於替心理-靈性資源進行「影子定價(shadow pricing)」(有時也稱為「偶發的價值」)。由於他們偶而也是生態觀光者和戶外休間的消費者,所以已可了解這些資源,但是授粉作用、營養循環等細微之處,對他們可能仍很神秘。他們沒有把自然經濟所提供的服務價值量化,可能也反應出,大多數由其他物種免費提供人類的重要服務都很常見,但經濟學家只計算那些罕見服務的價格。(也請參考Buchmann和Nabhan 1996)
Meadows (1990)曾提及一種使自然服務貨幣化的方法:「你喜歡在五月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替數兆朵蘋果花進行授粉工作嗎?」她問道。「我們可以想像發明一台機器來做這件事,但卻很難想像這台機器能做得跟蜜蜂一樣優雅和便宜,更不用說還要生產蜂蜜這種副產品了。」要把自然的服務經濟價值貨幣化,可以計算用人工服務來取代自然服務的成本。從稀少性和選擇權的觀點來看,如果由於目前的經濟習慣(例如使用過多的殺蟲劑),使得未來能進行授粉作用的生物變得愈來愈少,那麼雇用人類勞工或機器來為植物授粉的成本會是多少?
然而,Ehrenfeld(1988)指出,就如許多物種潛在的商品價值很低一樣,許多物種可能在自然經濟的服務上不具有什麼重要性:「數目最少、最罕見、分布範圍最狹窄-簡言之,最可能滅絕-的物種,顯然是生物圈最不需要的物種。這些物種中,有許多很少見或是不具有生態上的影響力;無論我們多有想像力,也無法使它們成為生態機器中一個小但又不可或缺的東西。」
有些哲學家和保育生物學家極力反對經濟學家想把所有價值貨幣化的傾向(Sagoff 1988; Ehrenfeld 1988)。有些事物雖然是有價格的,但其他事物所擁有的是尊嚴。而且,正如大家所熟悉的,我們經常會努力地把具有尊嚴的事物排除在市場之外-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認為這些事物具有內在價值。認為生物多樣性具有內在價值的一項可能動機,就是不要替它進行經濟上的價值評估,從而使它不致於受到市場變動的影響。例如,我們藉由立法禁止奴隸制度,使人類脫離市場。我們也立法禁止賣淫,把性關係排除在市場之外。為何不藉由立法禁止破壞環境的人類活動,來使具有內在價值的生物多樣性置於此市場之外呢?
Sagoff(1988)認為我們有兩個平行且無法比較的系統,可以用來決定物體的價值:市場及其代理人、投票箱。就個人而言,我們絕大多數人會拒絕賣掉父母、配偶或小孩-不論代價有多高。而當所有市民集體投入政治時,我們可能會拒絕為了符合效益成本分析中的「利益」,而出賣生物多樣性。事實上,1973年美國瀕臨絕種物種法,就是把生物多樣性排除在此市場之外的政治決定。
經濟學家提出反駁,認為我們經常必須在把可耕地開墾成農地的需求、和保護瀕臨絕種的動物的棲息地之間做困難的抉擇(Randall 1986)。我們可能會虔誠和善意地相信,具有內在價值的人是無價的,但人類生命的價值卻經常被貨幣化。例如,人類生命的金錢價值可以反應在一家汽車保險公司願意為撞死人的客戶理賠多少錢,或是產業界願意為保護雇員的健康和安全而付多少錢(或是依法需付多少錢)。同樣地,確認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並不代表它是無法定價的。我們要做有智慧的選擇,唯一的方法是用可進行比較的詞-即金錢-來表示從「商品」、「服務」到「存在」都包含在內的自然價值。
《瀕臨絕種物種法》在1978年修正,以建立一個高階機構間委員會,即所謂的「God Squad」(在警局的神職義工),若是一瀕臨絕種的物種具有極大的經濟利益,此委員會即可將這個物種的受保護層次提高。這項立法確認了我們的確有兩種無法比較的價值決定系統-一種是經濟的,另一種是政治的。它也確認了原本的政治決定,是把生物多樣性排除在例行的貨幣化之外,也不得為了更大的經濟利益而進行買賣。但它也承認了,由政治與經濟決定的價值,在真實世界中經常會互相衝突。當保存生物多樣性的機會成本,超過並未特別指明的門檻時,God Squad會允許從經濟考量因素為出發點,不接受美國一般民眾的意願,這些民眾可能經由民意傳達管道,例如國會議員等,來表達想保存美國現存本土物種的意願,這就是現況。
Bishop (1978)將美國瀕臨絕種動物法God Squad修正案背後的理由形之於文字形式。他支持安全最低標準法(safe minimum standard, SMS),這種方法不是把生物多樣性的市場價值、影子價格等都集合在一起,然後套用效益成本分析法(benefit-cost analysis, BCA),並選擇在經濟上最有效率的行動。相反地,最低安全標準法假設生物多樣性具有無法計算的價值,而且應該受到保存,除非這麼做的成本高得令人做不到。就如Randall(1988)的解釋:
效益成本分析法是從零開始,辛苦地建立有關保育效益和成本的證據,但最低安全標準法卻是假設任何物種的最低安全標準的維護,都是具有正面意義的。在經驗上的經濟問題是:「我們負擔起嗎?」或者是更技術性的問題:「達到最低安全法的機會成本有多高?」最低安全法的決定規則是,除非機會成本高得無法負荷,否則就必須維持最低安全標準。換句話說,最低安全標準法所問的是,我們達到生物多樣性的最低安全標準,會使我們在人類關心的其他領域損失多少?在此情況下,舉證責任將是在不支持最低安全標準的一方身上。
就如本章先前所說的,確認某樣東西的內在價值,其實際的效果並不是要使它變成不可侵犯,而是要把舉證的負擔、或使之合理化的責任,轉移到會造成負面影響的一方。因為把生物多樣性貨幣化的最低安全標準法,會把舉證責任,從保育人士轉移到開發業者身上,所以等於默認了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同時也把它包涵在經濟評估之內。
二、保育倫理學
李奧波(Leopold,1949)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倫理,倫理代表「對行動自由所施加的限制」,也就是說,倫理學是對自利行為的一種約束,以尊重其他事物的發展。
人類中心主義
西方宗教與哲學的傳統中認為,只有人類才值得我們去作倫理學上的考量。所有其他生物只不過是為要達成人類的目的時所使用的工具而已。聖經似乎是開宗明義地就以肯定的語氣主張人類中心主義。只有人類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所創造的,被託付管理大地及其他受造物的權力,最後更被命令要去征服整個受造界。懷特(White, 1967)也指出,幾個世紀以來,猶太教和基督教徒都相信人類對萬物所擁有的主宰權,不只是上帝所賦予的權利,也是正面的一種宗教責任。於是,西方文明因而獨特地發展出科學,以及最終造成具侵略性且嚴重破壞環境的科技。
諾頓(Norton, 1991)表示,以西方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作為基礎,就足以建構一套有效的保育倫理學。生態學所展現的世界,其系統性整合的程度,遠超出聖經作者所能夠想像的,因此抱持征服大自然的心態的話,將會造成生態環境的浩劫。任何主張以人類為中心的保育倫理學,都必須要求個人、公司,及其他利益團體,以公正的心態來思考自己的所作所為將會對自然環境造成那些直接影響,以及對其他人類所產生的間接影響。以砍伐熱帶森林為例,伐林可以生產上好的木頭,供給有錢的消費者使用、為林木公司帶來可觀的收入、提供就業機會,並為債台高築的貧窮國家創造外匯收入。相對地,這也會迫使當地的原住民無家可歸、喪失傳統的謀生方式,使全球人類無法享有親近尚未開發的資源、珍貴的生態系統、感受美學經驗,和拓展科學知識的機會。若未加以管制,伐林可能使我們的後代子孫生存在一個貧瘠的世界,造成世代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在西方道德思維的根本架構未經改動的情況之下,伐林和其他破壞環境的資源開發,就可能會被視為有悖人情倫理。
猶太教─基督教的管家保育倫理學
猶太教─基督教的世界觀是造成現代環境危機的罪魁禍首這樣的指控,刺激了一群關心環境的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他們對懷特解釋的聖經環境態度與價值觀提出質疑。上帝在創造人類之前,也都讚揚了他在前五天所創造出來的每一項東西是「甚好的」(good)。因此上帝其實已賦予每種生物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而非獨厚人類而已。聖經也說明上帝的旨意,是要整個大地充滿無窮的活潑生命:
「上帝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上帝看著是好的。」(創世紀1:20-21)
再者,「主宰」(dominion)其實是個語意不清的語彙。由「人」來主宰整個大自然是什麼意思呢?懷特認為,至少在過去,基督徒認為這意味著人類可以為所欲為地主宰自然界。但是在創世紀比較後面的經文裡的記載,上帝把代表人類的亞當放在代表大自然的伊甸園裡,「使他修理看守」(創世記2:15)。這表示人類的「主宰」角色,應該是像個看護者──管家──,而非蠻橫的暴君。但是為什麼只有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被造呢?這可以解釋為上帝賦予人類獨特的責任,而非特權。由於上帝關愛人類,因此我們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被造,所以也必須要關愛大地。
猶太教─基督教的管家環境倫理學簡潔而有力,同時也能與保育生物學的倫理觀配合無間(Baker, 1996)。猶太教─基督教的管家環境倫理學以最明確而清晰的方式賦與大自然客觀的內在價值 -來自上帝的神聖命令。但是內在價值是由物種傳遞下去,而非個別的生物個體。因為在上帝的造物過程中,祂是創造了物種,而非個別的動、植物。因此上帝所謂的「甚好的」,是指物種而非個別生物而言。所以人類只要不危及物種生存,而且也不破壞生物多樣性,還是可以自由地利用其他生物。誠如伊仁費德(Ehrenfeld, 1988)所言, 猶太教─基督教的管家環境倫理學,要求人類直接向上帝負起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責任:「多樣性是上帝的財產,身為陌生人和客旅的人類,無權破壞生物的多樣性。」
非西方的傳統環境倫理學
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回教和佛教也是一樣。其他主要的宗教,諸如印度教和儒教,雖然有地區性的限制,但是也有數百萬的信徒。一般人會在宗教信仰的驅動之下,受到強烈感召而從事某些行為。因此從目前世界上既有的宗教理念中抽取出的環境倫理學,對於全球保育工作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猶太教─基督教的保育人士根據聖經所努力建構的猶太教─基督教管家環境倫理學,提示了一個重要的新思考路線:「如何從其他宗教的經典來建立有效的保育倫理學?」針對這一點,柯倍德(Collicott, 1994)曾經作過全面的調查研究。在這裡即使僅列出綱要都不太可能,不過,能夠摘要式的介紹非西方的保育倫理學應該會很有幫助。
回教徒相信,回教是西元第七世紀,由阿拉透過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傳遞旨意而成立的,穆罕默德則認為自己是傳承了來自摩西和耶穌的先知傳統。由於希伯來人的聖經和新約聖經,是建構回教信仰當中屬於較早期的神聖天啟,因此,回教徒的基本世界觀,多與猶太教─基督教雷同。尤其是回教對人類是大自然中的特權階級的想法,甚至比猶太教和基督教更為強烈,回教認為,其他生物的存在都是為了服務人類。因此回教徒認為以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方法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至於在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方面,在回教的羽翼之下,阿拉伯的羚羊也就快被那些坐擁石油、手持武器的酋長給獵殺光了。但是這種對其他生物無情冷酷的態度,在現今的回教國家裡,已經不再受到宗教上的認可了。
回教界對於宗教法與世俗法並不加以區分。所以回教國家新設定的保育法規,必須以穆罕默德的天啟──可蘭經,作為根據。八○年代初期,一群沙烏地學者試圖在可蘭經裡面搜尋與環境保育相關的經文,草擬了回教自然環境保育原則。除了重申「為了人類的好處並滿足人類的利益所作的利用、發展與征服自然的關係」,這份歷史性文件也清楚闡述回教版本的管家環境觀:「人類只是地球的經營者,而非所有者﹔受惠者而非處置者或命令者。」(Kadr et al. 1983)這群沙烏地學者同時強調公平的分配「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不僅現代人類應公平享有資源,後代子孫亦然。諾頓(Norton, 1991)也認為,當後代子孫的權利也獲得與現代人同等的尊重時,保育目標就達成了。沙烏地的學者們甚至在可蘭經裡發現隱含生態意識的經文,例如:上帝「創造出萬物並使它們處在均衡的狀況下。」
北美保育哲學的先鋒思想家—愛默生和梭羅,都均受到精妙的印度教哲學性教義影響。印度思想也啟發了奈斯(Arne Naess, 1989)提倡的當代保育哲學「深層生態學」。印度教徒認為,宇宙萬象之中,只有唯一一個真實的實體或存有(Reality or Being)。換句話說,上帝並不是像猶太教─基督教─回教傳統所說的,是存在於其他較微小且為附屬的存有當中的一個至高無上的存有。相反地,所有的存有都只是所謂的婆羅門(Brahman)—唯一存有的顯露而已。所有的多元,各種的差異,都是錯覺,只是表象不同罷了。
這樣的觀點似乎並不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一個具有前景的起點,因為多樣性真實的存在,不論是生物上或其他方面,似乎是遭到否定。但是那斯發現,印度教的婆羅門觀念,與各個有機體因為生態依存關係,統一於一個系統化的整體的方式,有雷同之處。不論那會是什麼,印度教明確地邀請人類要去認同其他的生命形式,因為所有生命的本質都是相同的。由於相信每個人內在的自我(atman)都與其他生物的自我是相同的,同樣都只是婆羅門的顯露,因此,人類應該要憐惜萬物。因為某種生命形式的痛苦,就是其他生物的痛苦,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這種思維方式啟發了當今最成功的保育運動之一─Chipko運動,該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印度喜馬拉雅山的森林,免於遭受商業性的濫砍濫伐(Guha 1989; Shiva 1989)。
耆那教的教徒人數不多,但是在印度卻有很大的影響力。耆那教認為,每種生物的體內都住著一種無形的靈魂,跟人類的靈魂同等純潔與不朽。前世的惡行會在今世因果報應(karma-matter)。不殺生(ahimsa)與禁欲苦修是跳脫物質輪迴,達到涅盤之道。因此耆那教極力避免殺生,並禁止縱慾。最嚴格的修行人只吃別人的剩飯剩菜,並且盡可能降低用水量,這並非基於健康的考量,而是害怕吃進水中的有機物﹔較不嚴格的修行人則是素食主義的忠實信徒,只保有極少的生活必需品。耆那教因而堪稱全球環境保育倫理學的領袖。他們對食物鏈的低度倚賴與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被推崇為生態學所提倡的生活方式的模範(Chappel 1990)。<耆那教的自然宣言>作者宣稱該教裡中心的道德教訓不殺生「正是不折不扣的環境主義」(Singhvi n.d.)
佛教雖然現在在其發源地印度,可說是已經衰微了,但在亞洲其他地方卻已興盛了數百年之久。佛教創始者──釋迦牟尼佛,先藉由打坐禪修,體驗生命本源的婆羅門(Atman-Brahman)的唯一實體,再苦修禁欲以求使靈魂可以逃脫肉體,但是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他後來體悟到,他所遭遇的苦惱,包括靈性上的苦惱,都是因為欲望無法平息的結果。因為人要證悟、獲得真正的自由,並非是藉由努力追求外物,滿足欲望,因為那會導致更多欲望的產生,而是應該要止息欲望。況且欲望會扭曲一個人的觀點,誇大某物的重要性,而削減他物的重要性。當一個人能戰勝欲望,他就能接受宇宙萬物的原始面貌。
當佛陀體悟到這一點時,他渾身沐浴在喜悅之中,他接著慈悲地關愛周遭的人。他跟弟子分享證悟心得,並建立道德戒律供弟子依循。許多佛教徒都相信,萬物都面臨相同困境:我們都受到欲望驅使,所以生活中會不斷產生苦惱,只要能夠證悟,大家都可以獲得真正的解脫。因此佛教徒把其他生物視為成佛道上的同修。
佛教徒與耆那教及基督教徒一樣,都承擔著全球保育運動領袖的角色。最有名的可能應屬西藏流亡政府的領袖達賴喇嘛。一九八五年,佛教界推動一個名為「佛教徒自然觀」的計劃,目的是將佛教經典中,凡是與環境相關的篇章全部整理出來,由此希望證明佛教與現代保育哲學的關係,以及提昇佛教寺院、學校和組織的保育良知和良心(Davies, 1987)。巴地(Bodhi)為佛教的環境倫理學作了一個言簡易賅的註解:「佛教的萬物脣齒相依哲學﹔以禁欲追求真正快樂的主張﹔放下、入定追求證悟的目標﹔慈悲萬物的倫理,均是尊重、慈愛大自然的根本要素。」
全球人口有四分之一是中國人,所幸中國的傳統思想擁有非常豐富的保育倫理思想資源。中國的「道」,代表「方法」或「道路」。道家相信自然有其道,自然的流程不只井然有序,而且也和諧共處。人類可以將「道」視為自然界彈奏的和諧樂章。人類的活動可以順道而行,或是逆道而行。依循前者,人類的目標能輕鬆且高雅地完成,而不破壞大自然環境﹔後者,人類將難以達成目標,且必須犧牲大量的社會和自然資源。資本密集的西方科技,如核電廠和工業化農業,在精神和動機方面,都是與道家精神背道而馳的。
現代的保育人士發現,道教的精神,跟今日的抗衡運動(counter movement)中,朝向適切科技與永續發展的方向相似。一九九三年,密西西比河峽谷的洪水氾濫,就是一個明例。該河川系統並沒有依循「道」的精神管理。因此河堤和防水牆反而助長了洪水的氾濫。其實,我們應該把城市與鄉鎮建立在沖積平原之外,讓奔騰的密西西比大河偶爾就有氾濫的機會。河水沖積而成的平原沃土,可以在較乾燥的時節耕種,但是其上不應建照任何永久建物。如此,洪水方能週期性的淹沒土地、豐富土質、補充野生動物所需的溼地養分,而居住在高地的人類,也才可以過著安枕無憂的生活。也許美國官員也該讀讀道家思想。我們也期望中國的官員能揚棄新興的毛澤東主義(Maoism),而就傳統的道家,這樣他們就會瞭解,跟楊子江的相處之道,不應該是圍堵政策,而是需要彼此共榮共存。
中國另一個宗教觀是儒教。對大部分的亞洲或西方人而言,儒教提倡的是保守主義,恪尊風俗禮教、孝順父母,並接受封建制度之下的不平等。因此看起來似乎並不是一個培育保育倫理學思想的「沃土」。但是阿密斯(Ames,1992)反駁了這種普遍的想法﹔「傳統的儒教與道家學說有一種共通的基礎,兩者都關切「今世」當下經驗的具體細節而非只是空談抽象、不切實際的理想。兩者都重視個人的獨特性、重要性,及卓越性,以及個人對世界的貢獻﹔同時,也強調人與所依存的環境是彼此相關且相互依賴的。」
儒教認為,人的身體並非只是一個臭皮囊,另外有一個不朽的靈魂存在﹔相對地,每個人都是一個關係網絡的獨特中心。由於一個人的身分就是由這些關係構成,若是破壞其依存的社會或自然環境的脈絡,就等同於自我毀滅。因此,殺害生物(biocide)就等於自殺。
西方通常並不認為個人需要強烈倚靠周圍環境的脈絡,不論是為了生存或認同皆是如此,所以西方人可能會以為,他們在犧牲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後,自己依然可以毫髮無傷,或者能過更好的生活。但是對儒教徒而言,要將個人從環境抽離是難以想像的。如果將環境脈絡(context)的意涵由傳統的社會觀擴大到自然環境觀,我們可以說,儒教其實為中國現代的保育倫理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基礎。
生界中心主義
在環境倫理學問世之前,西方傳統的道德哲學家只承認唯有人類才具有道德身分(moral standing)。當他們作這種承認時,並非訴諸於上帝的形像這類神秘的特質,而是訴諸如理性、語言能力這類可觀察到的特性。他們堅稱,由於只有人類才能夠論理和說話,因此,只有人類才配得倫理的對待。以18世紀的康德(1959)為例,他便主張,由於人類是理性的,因此,我們本身就是具有內在價值的目的,而動物和其他形式的生命只是具有工具性價值的工具而已,因為它們沒有理性的能力。當代的環境哲學家試圖建構一套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但他們並不訴諸於神秘信仰的概念,諸如上帝、道或普世的佛性。有些人認為以理性及語言能力作為判別道德身分的資格並不適當,應該有其他更為合適的一些可察覺的特性。
Singer(1975)和Regan(1983)揭示古典的西方人類中心式的倫理有如下的矛盾:如果倫理身份的資格── 或是技術性的稱為「道德考量的基準」──其定位高到足以將非人類全部排除在外的話,那麼,人類中未達此一標準的個體如嬰兒、極度智障、和年邁的人等,也都將被排除在外(因他們不具備理性)。如果我們按照康德所說的,把理性當成倫理考量的基準的話,那麼上述這些邊緣人就可能會受到如同我們對待未達此標準的非人類一般的待遇。例如,非自願而且很痛苦地被當成醫學試驗或實驗的對象、狩獵的對象、或被作成狗食。沒有人希望這種事發生。為了避免發生這樣的事,Singer(1975)和Regan(1983)主張我們必須把倫理考量的基準降低。如果它的定位低到足以包含這些邊緣人的話,它將也會包含一部分非人類的動物,Singer(1975)依據18世紀與康德同時代的人“Jeremy Bentham”的論點,主張要以感知能力(sentience)-對於痛苦和欣喜經驗的感受能力-來作為倫理身分的考量標準。
Goodpaster(1978)是首位從動物解放跨出,而進入生界中心(字面上指「以生命為中心」)環境倫理學的人。他主張: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感知能力並不是演化的目的,而是動物求生存的手段。因此,如果感知能力與道德之間有任何關聯性的話,那麼,演化出感知能力所要服務的對象(這裏指的是生命)豈不是更應該會有道德關聯性嗎?再者,如本文前面所述,所有的生命,有它自身的善,所以也存在有利益。依據Goodpaster(1978)所言,這些事實本身就應該讓我們賦予所有生命道德地位。
Taylor(1986)界定一個更極端的觀點,主張所有生命都具有同等的「內在價值」。撇開給予每一種生命同等的道德考量這種倫理上問題重重且實際上不太可能的工作,Taylor的純粹而極端的生界中心主義和保育生物學其實並沒有什麼關聯。保育生物學所關心的重點不在於個體的命運,而是整個的物種、生態系和進化過程的存續。
然而,在Rolston(1988)作了些修正之後,生界中心主義不但可以表達出保育生態學家所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成為一套可以實行的保育倫理觀。Rolston同意Taylor的說法中,所有生命都有內在價值(或原生價值)因而應該享有道德身分這個觀點。但是他不同意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觀點。在生物因其具有利益以及其自身的善,因而保有的內在價值的底線,Rolston又加了一條價值的「紅利」----具有感知的能力,然後他再加上另一條額外的價值紅利---理性和自我意識。因此,有感知能力的動物比沒有感知能力的植物擁有更多的內在價值,而人類又比有感知能力的動物擁有更多內在價值。Rolston的生界中心主義因而比Taylor所說的更能符合我們對價值體系的直覺。因Rolston的版本,人的生命比白尾鹿更有價值,而白尾鹿比北美短葉松有價值。而且如本章前面的章節所說的,Rolston也提供了內在價值或近似的東西-價值的「紅利」-給物種、生態系和它們的演化過程。因此,他主張,我們同時也有道德義務去保留它們。
生態中心主義
由於哲學上的清晰完整以及性格上的相近等理由,當那些對於非人類中心思想能夠產生共鳴的保育生物學家想要去尋求一套合適的保育倫理時,他們都被李奧波的土地倫理所吸引。李奧波本身即是一位保育生物學家。事實上,他也許可被稱為此一倫理原型的培育者(Meine 1992)。此外,李奧波的土地倫理,既非植基於宗教信仰,也不是傳統西方哲學倫理範式的外延,更確切地說,它是奠基於演化和生態生物學。因此,多數的非人類中心保育生物學家,不論其宗教或文化背景,都覺得和李奧波的土地倫理在智性上是意氣相投的。
在《人的由來》一書中,達爾文就是在處理演化的起源和倫理的發展等問題。在萬物的「生存掙扎」中對「行動自由的限制」怎麼可能經自然選擇而產生呢?(李奧波1949)達爾文(1904)簡單地回答如下:社會組織增進了許多種生物的存活和再生能力。在哺乳動物之中,父母和子女的親情擴延及於其他近親,於是個體因而結合成為小的社會單位,如夥、群和幫。當其中一種哺乳動物──智人──獲得反省和說話的能力時,有導向社會完整性和穩定性的行為被認為是「好的」而反社會的行為被認為是「壞的」。或如達爾文所寫的:「如果謀殺、搶劫、叛逆等行為司空見慣的話,沒有一個部族能結合在一起;因此,在同一部族的制約中這種罪惡會被永遠冠上敗德的惡名。」倫理一旦產生,便隨著社會快速地生長和發展。依據達爾文說法(1904):
「當人類文明進展時,小部落結合成一較大的社群,這一簡單的理由將會告訴每個個人,他必須延伸他的社會本能和同情到同一國家內的所有成員──儘管有可能是他並不認識的人。這個觀點一旦達成,阻止他的同情擴展至所有的國家和種族的只有一道人為的藩籬而已。」
在20世紀未葉,我們終於達到達爾文在19世紀中期所能想像的那樣,有一個普遍性的人權倫理,但同在20世紀,生態學上也發現(實際上是再發現,因為許多部落的人似乎以類似的用語來形容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人類並非只是諸多人類社群的成員之一而已──從我們所熟悉的部落到人類的大家庭──,同時也是生界社群的一員。
從達爾文那兒我們學到「所有直至目前為止所發展出來的倫理,有賴於一個前提,那就是:個人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各個部分所組成的社群中的一個成員」(李奧波1949)。而根據李奧波所說的,如今生態學「只是擴展社群範圍,使其涵蓋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整體的說:『土地』而已」。李奧波認為,在過去,每逢一個新的社群被認知,「每個個體應該延伸他的社會本能和同情心到這個新社群,其實是件顯而易見的事實」。因此,在現今,當生態學已經告知我們是生界社群的一分子時,這種 「顯而易見」也應該再次介入。
縱然在過去兩百年的西方道德哲學中已經完全遺忘了,但是,人的倫理觀一直是很強烈地具有整體觀的視野。那就是,人們覺得他們對其整體社群本身和社群中其他成員都具有責任和義務。關於這點,達爾文(1904)強調說:「野蠻人或原始人在判斷行為的是非對錯時,只是看這些行為是否顯然地會影響部落,而不是在於影響整個種群或部落裡頭個別的成員。這正好符合道德感原本是出自社會本能的信念,因為兩者一開始都是和社群有關。」
李奧波受了達爾文的影嚮,因而也賦予他的土地倫理決定性的整體觀。他寫道:「簡言之,土地倫理把智人由土地社群的征服者變成一個普通的成員和公民,它意味著尊重其伙伴成員也尊重其整個社群。」事實上,李奧波當時寫出土地倫理的「總結箴言」或「金科玉律」時,似乎完全忘了「伙伴成員」而只提到「社群」如下:「傾向於保留生界社群的完整、穩定和美的事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
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有嚴重個人主義特質的西方道德哲學的忠實擁護者批評土地倫理導致「環境法西斯主義」-把個體權益,包含人類個體,放在整體的利益之下(Regan 1983, Aiken 1984)。在關係到非人類動物的利益時,他們這樣的論點的確是成立的。例如,當野生的羊或兔子威脅到瀕危植物種群或生界社群的健康和完整性時,土地倫理將准許或甚至要求必須殺害這些動物。但李奧波追隨達爾文的思想,認為土地倫理只是我們長久以來人對人的倫理關係的一個「附加物」而已,並不是「替代者」。
人類近年來成為國家或國際社群的一員,並不意味我們再也不屬於更古老及界限較為狹窄的社會團體,如大家族;或表示從我們的家族,參與的黨派和公民聯盟等團體的所有道德義務和責任中解放出來。同樣地,我們明白自己本身是生界社群的一分子, 也並不代表可以從我們所參與的種種人類社群的所有道德義務和責任中解放出來。
這種對李奧波的土地倫理助長了環境法西斯主義的批判所提出的辯解,卻也遭到「紙老虎」──生態中心的環境倫理沒有牙齒──的批評。假如我們要完全地同時承認所有古老和現代人類義務與責任及最近發現的環境倫理的話,我們如何把犧牲人類的利益去保存非人類種群和生態系這事視為正當的呢?
幸好,並非所有人和環境的衝突都是生死攸關的事。我們極少須要面對殺人以保留生物多樣性這樣的抉擇。多數的抉擇是介於人類的生活型態和生物多樣性之間的抉擇而已。 例如,對日本人及其他取用鯨肉的人,並不是要他們捨棄生命去拯救鯨魚,只是要求他們改變飲食的偏好而已。去拯救森林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去自殺,我們可以藉少用木材和紙及回收使用紙漿木纖來保護它們。所有人類的權益並非平等的,為了其他生命形式的生存權益和生態的完整及健康,我們應有超越較不重要的人類權益的心理準備。
李奧波的土地倫理寫於廿世紀中期,那時的生態科學將自然描繪成趨向靜態平衡,且將擾動和阻礙(特別是人引起的)描述成不正常且有破壞性的 (Odum 1953)。但是,根據最近對於「生界社群」能夠不隨時間的變化而改變的質疑 (Brubaker 1988),再根據當代生態學的內涵向較為動態的典範變動 (Botkin 1990),以及承認將自然干擾結合入小地貌-和景觀-尺度的生態動力學 (Pickett and White 1985),我們不禁會認為李奧波式的土地倫理是否已經陳腐過時了?是不是生態學上的典範轉移已經從「自然平衡」轉變為「自然的變遷」而使土地倫理失效了呢?不是的。但最近生態學上的發展可能使得土地倫理需要作修正。
李奧波其實是警覺到環境的變遷,也對這些變遷非常敏感。他知道保育必須對準一個動態的標的。但是,我們要如何保育一個動態的、始終變遷的生界,尤其當我們使用保育和保存這些字眼-特別是和完整性及穩定性連結在一起時-豈不是意謂著阻止變遷?解決這個難題的關鍵在於時間上與空間上的尺度的概念。再回頭看李奧波的「土地倫理」可顯示他的確有這樣的線索,雖然他也許並沒發覺到自然界變動的尺度事實上是如此多的層次。
在「土地倫理」中的「土地金字塔」部份,李奧波寫道:「演化的變遷……通常是緩慢而且是局部的。人類發明了各種工具之後,終於能造成史無前例地劇烈、迅速和大範圍的變遷。」(1949)如前述的,李奧波敏銳地覺察到自然是動態的,但在廿世紀中葉平衡論的生態學的支配下,他所理解到的自然變遷主要是演化上的而非生態上的變遷。然而,當生態變遷加上演化變遷時,其尺度的考量是同等重要的;意即,當正常氣候擺盪和小地區變動被加進正常滅絕速率、雜交和分化一般。
如同李奧波(1949)所說:「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土地社群』中的『單純的成員和公民』。」因此,人為加諸於自然的變遷比起其他的變遷並不算是比較不自然的。然而,由於人類是道德的種群,能夠深思熟慮並作出有良心的抉擇,且演化上的血緣和生態社群成員這層關係又在我們所熟悉的社會倫理中加上了土地倫理,因此,人為的改變就要經過土地倫理的評估。但要根據什縻基準呢?那就是,適當尺度的基準。
時間及空間尺度的組合是直接評估人類對生態的衝擊的線索。遠在人類演化出來之前,大自然裡頭也經常發生激烈地變遷(Pickett and White 1985),而且,這種變遷至今依然存在,與人類所發動的作為並無關聯。火山用岩漿和火山灰把整座山的生界掩埋、龍捲風掃過森林、夷平樹木、颶風侵蝕海岸、野火燒遍森林及草原、河流淹沒氾濫區、旱災使湖泊和溪流乾涸。那麼為何人為的皆伐、海岸開發、水力的集中運用要被認為是環境上不道德的呢?如果這樣來看,它們應該不是。但我再次強調,這是一個尺度上的問題。一般來說,像龍捲風這樣經常發生的激烈的擾動,發生在小範圍而廣泛分佈的空間尺度;但是像旱災這樣在空間上影響廣大的災害,則比較不常發生。且大多數的擾動不論其強度或規模怎樣,都是突發且無法預測的。人為干擾的問題如企業化的林業及農業,市郊的開發,拖網漁業等種種,在於它們不論發生頻率、分佈範圍和經常性的發生等,都遠比非人為擾動來得大多了。其所造成干擾的時空範圍,也遠超過生態系在過去演化時間所經歷的。(Holling and Meffe 1996)
Pickett和 Ostfeld (1995)-生態學上新的自然干擾/小地區變動典範的倡導者-一致同意適當的尺度是倫理學上評價人為生態干擾的操作基準,他們提及:
自然變遷是一個危險的隱喻。此隱喻和其潛在的生態學典範可能會暗示一些輕率和貪婪之輩,讓他們認為,既然變遷是自然界的一部份,那麼,任何人為的變遷也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推論是不對的,因為自然界的變遷是有嚴格限制的。……人為導致的變遷的兩種特徵:飛快的速率和大範圍的空間,顯然是太過份了。
在眾多異常頻繁和廣佈的人為干擾之中,李奧波在其「土地倫理」一文中所苛責的包含了:在北美洲生界社群中全面性地除滅大型的掠食性動物、用馴化物種取代野生種的情形隨處可見、起因於人為「全球性大量植物相和動物相的塘化效應」及隨處可見的「水污染或用水壩阻斷水流」而引起的全球性的生態同質化。
然而,土地倫理的總結道德箴言也必須依據過去1/4世紀以來生態學上的進展作更新。李奧波承認自然環境變遷的存在和其重要性,但似乎只著眼於非常緩慢的演化時間尺度上。即便是如此,他還是把固有環境變遷的概念和其尺度上決定性的基準結合在土地倫理之中。根據新近生態學的進展,我們可以將氣候和生態的動態加入土地倫理的尺度基準之中。更動李奧波優雅的散文也許是不智的,但我們仍然試圖為土地倫理確立一條現代版的道德箴言如下
傾向於只在正常的時空尺度下擾動生界社群的事是正當的,反之則是不正當的。
結語
保育生物學是受到生物多樣性價值的推動而產生的。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看重生物多樣性呢?哲學家將兩種價值作出區分:工具性價值和內在性價值。生物多樣性的工具性價值包括:商品(如:實際或潛在的食物、醫藥、纖維和燃料等);服務(如:授粉、養分循環、提供氧氣);資訊(如:實際的科學知識、基因庫);以及心理-靈性的滿足(如:自然之美、宗教上的敬畏、純理論的科學知識)等方面,提供給本身具內在價值的人類使用。生物多樣性也具有內在價值──它本身就具有目的,同時又是達到人類福址的手段。其他形態的生命與我們一樣,都是自我組織的存有且具有本身的善。人類能夠為其他生命本身的緣故而看重它們,同時也為了它們所提供給我們的一切服務。
為了要把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其他東西的價值作比較,經濟學家嘗試將生物多樣性的工具性價值和內在價值貨幣化。哲學家也以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為基礎來建構保育倫理學。如果生物多樣性對人類只具有工具性價值,一個人為了追求私利而破壞它,可能會對其他人造成傷害-在這種情況下,破壞生物多樣性是不道德的。假如生物多樣性還具有內在價值,它的被破壞就加倍的不道德了。
聖經承認非人類物種的內在價值,(上帝宣告它們是「好的」)。因此,當代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學家建立起猶太-基督教管家的保育倫理學。其他許多各種宗教也都根據他們各自的經典和信仰傳統,建立起不同的保育倫理學。李奧波的土地倫理並不是以任何宗教信仰為基礎,而是建立在當代的進化與生態生物學之上。從演化的觀點來看,人類與其他生物具有親裔的關係;從生態學的觀點看,人類只是「生物社群」 社一個「普通的成員和市民」而已。根據李奧波的看法,從這些一般性的科學事實,產生出對「演化旅程中的同行的旅行伙伴」、「生物社群中的成員伙伴」、以及「社群本身」 等的倫理義務。雖然現代的生態學承認大自然的改變和干擾是正常的,如果我們把李奧波的土地倫理根據這種科學上新的亮光作出修正,它仍然會是保育生物學中指導性的環境倫理學的。
全文完
譯自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edited by Gary K. Meffe and Ron Carroll (Sunderland, Mass.: Sinauer Associates, 1997)
Chapter 2 : Conservation Values and Ethics 本文由柯倍德教授提供,內容涵蓋2000年8月間在台灣各地演講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