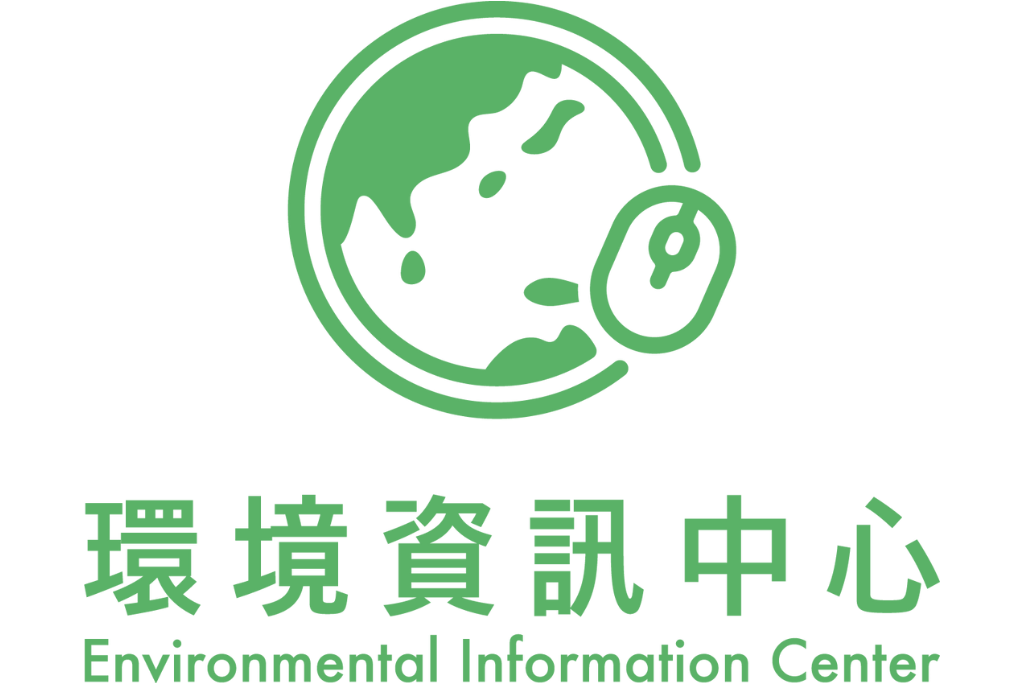年初,知名登山客G哥吳季芸獨攀馬博拉斯橫斷不幸墜谷失溫罹難,再次引發爬黑山論辯,山岳界團體積極投入與政府溝通山域管理議題,終促成政策大轉變。在10月21日「向山致敬」記者會上,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宣佈國家山林解禁政策,以「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及「責任」等五大政策主軸推動山林開放,並鬆綁81處林道,過去繁瑣的登山申請也將簡化流程,且預計四年投入6億3000萬經費整建山屋和步道,優化登山環境。登山者稱,終於盼到這一天。
12月11日迎來國際山岳日,而布農族作家沙力浪(Salizan Takisvilainan)月前推出新作《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扣合未來又將興起登山風潮,他想訴說仍被主流視野忽略、關於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那也是一個Bunun大腿從細長到粗壯、褲子只好換穿的成長歷練。

靦腆懵懂到內斂穩重,追隨領路人的腳步
沙力浪1981年出生於花蓮卓溪鄉中平nakahila部落,文學創作屢獲獎項肯定,為原住民新銳作家代表之一。回想寫作之路,他表示,家裡觀念也是學業要顧好的教育路線,以當公務員、老師為養成目標;因自己亦擅長體育,國小練田徑長跑,初始國中投稿《花蓮青年》、高中投稿《台東青年》等刊物,主要作為賺取零用錢來源;後來高中國文老師鼓勵「多寫族群相關東西」,開始書寫身邊的小故事,包括部落的、父親以前在山上或祖父開墾耕地的生活,「不過其實長輩少講遷徙的來由」。大學念元智中文系,因環境變化產生認同種種困惑,便自修習得布農族語羅馬字記音拼寫,展開身分認同的追尋。
彼時,學術團體常委請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巡山員林淵源(Nas Qaisul Istasipal)擔任嚮導,比如黃美秀教授自1998年投入台灣黑熊野外調查、林一宏的布農家屋調查,林淵源抓緊進山區出任務的機會帶著表弟Salizan認識山林。「2000年大一暑假第一次入山,參加林一宏教授〈八通關越嶺道東段四處駐在所遺址之研究〉。921地震後路很不好,走的還是鐵線橋。那次走了12天,協作不多,大家比較是純粹山上走走看看,尤其難忘途經大水窟,大哥停下遙指祖居地——馬西桑,說那是你祖父曾經住過的地方。」循此,拉庫拉庫溪的山跟Salizan有了族群的連結。

Salizan坦言,「大哥知道我想做文化記錄,減輕了我背負的重量,讓我可以記錄山林的故事。野外新手什麼都做不好也走得慢,但凡事跟著做,從找柴、認山頭學起。」同時,研讀清代、日治時期大分、喀西帕南事件至國民政府遷台等歷史材料,「空間」逐漸轉變成「有意義的事物」,再回到東部就讀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則嘗試運用學術方法闡釋拉庫拉庫溪流域語言、權力、空間的命名。
畢業後在外發展多年,雖然盡量擠出時間下田野,更深刻體認到「山林知識」乃建立在長年山上活動的累積,「像技術性的找路很難,每逢放假才能回部落複習,進步有限。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比如行進間不能停下問問題,晚上休息時才可趕快做確認,剛開始大哥頗不適應提問,習慣攝影機的存在後,反而會主動停下提醒我拍攝。大哥也讓我融入中正部落的高山協作圈,高山協作間多有親屬關係,彼此熟悉後對未來發展部落事務都會互相影響。」2015年Salizan決定回到原鄉,成立「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深耕布農文化,從文字工作者兼任高山嚮導、高山協作的工作,過去點點滴滴的口傳親授,滿是流露表哥提攜晚輩的傳承深意,豐厚了一書底蘊。

與山林為伍並不浪漫,但走在祖先走過的路上
一書分三大篇,分別為台灣原住民文學獎——報導文學2013、2015、2018年度獲獎文的修動補充,重心各有不同。首篇同書名〈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因為那正是一切的起源。
斷斷續續近20年,Salizan跟高山協作密切相處,由淺入深接觸其生活面貌:勞動條件雖艱苦,卻是一份少數能留在部落且跟傳統領域發生關係的職業。這份交往情誼促使他話說從「頭」,獻給曾經在這群山中工作的族人。透過兩次由林淵源領路的探訪行程:2012年清朝八通關古道調查及2013年日治八通關越嶺古道——祖居地馬西桑之行,以巡山員與背工為主題,重現歷史考掘並搭配真實的工作狀況,嚴謹爬梳文史之際亦生動得有血有肉。
布農族的祖先均採人力搬運來運送物品,故製作許多器具來協助背負工作,他解釋,原住民嚮導和高山協作上山一定會攜帶的物品之一的「頭帶(tinaqis),即為力量的意涵。」頭帶雖是背簍、網袋或背架的附屬器物,但背負重物時有了它頂於前額發揮固定效用或緩減承重,上山務農到打山豬,樣樣項項都可以放進去,便能「背越多、走越遠,象徵著用身體建設家園的布農精神。」

而被列為一級古蹟的清古道,乃一條從此改變布農人傳統生活的道路,闢建工程(1875)聘僱東埔布農族族人擔任挑夫,使原屬農、獵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背負工作進入有組織、有制度的「工作職場」。他認為,「當身體讓渡給政權,幫外族人造橋鋪路,頭帶的力量已不再為族人所用,卻是背起一段沉重的被殖民歷史。」
到了日治時期1915年發生喀西帕南戰役、大分戰役,後拉荷.阿雷率領族人退守玉穗,在在強化八通關越嶺道路(1919~1920)之興建,動用不同原住民族開鑿越嶺道,沿路衝突不斷,「經過抵抗之後,身體更是完全交給外來政權為日本人服務。」殖民者挾武力、金錢強勢入侵,政策從懷柔到高壓理蕃、槍枝收繳,布農族族人當嚮導、背工也起義抗日,形成既是抗拒又是協助的複雜角色。

高山協作員的隱身再現
據《台灣登山史》(2013)分類,戰後經歷「新山區探險階段(1946~1972)」、「百岳推廣階段(1972~1981)」兩大階段,然不管開發新路線或野外調查一樣高度仰賴原住民揹工的支撐,正式專業職稱為高山協作員,俗名包括挑夫、背工、苦力、腳伕等稱呼。近年來政府啟動原住民轉型正義,但協作市場化使得只有在血汗過勞的猝死、工傷發生時偶現一些改善勞動條件的呼籲,「原住民高山協作員」這具有百年歷史的命題為何無名失語如此?又能如何勾勒其當代定位?
Salizan表示,高山協作這一塊,一直沒有比較完善的制度,所以持續既有的工作條件,如一天25公斤/4000元左右的行情價、事前工作內容確認等等;近期相對有改善的則像是和山友對等的關係,或協作可視個人身體情況背負超過基本公斤數的計價協商。現在較有組織的有布農卡里布灣企業社、雲豹登山隊、嘉明湖天馬登山隊等團隊,維持10至20位協作,有比較明顯的路線,除了天候因素外,其實是一個穏定的工作,可以支撐一個公司或合作社。若山友路線規劃的是傳統領域,較少穏定的客源,為了養家活口或保險起見,仍須從事農事輔助。所以,「卓溪的組成不太一樣,大家互相介紹工作,接案以學術探勘為主,工作過程中常分享互動,不只是一次登山行而已,像跟林一宏、黃美秀較像夥伴關係。」

「背工專職化後,走同樣的路線並追求翻桌率,山友期待吃好的、拍美美的服務,新的協作對於布農族傳統文化較難以深化,走一般大眾路線、追求人的數量或服務品質之下,也較難與山友分享布農族的在地知識;另方面,協作年紀大了體力下降,如何延續山林的工作,說故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傳統領域結合學習及工作,可以讓協作延伸對歷史的了解,這些都可以當成說故事的材料。期待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在山林工作,沒有族人在山上活動的話,總有一天會被國家完全控管。」
他憂心重複大眾路線依舊與大自然異化或過度服膺市場趨勢,去年成立卓溪鄉登山協會擔任總幹事,希望滾動起讓族人願意留在山上的活水,「瓦拉米算親子路線不那麼需要協作,但如果族人增進自己的族群文化、歷史,帶出深度的旅程,才能走出卓溪鄉的一條路,並且說出我們的故事!」
他補充,可惜女性高山協作在這一本書未能處理到,還是有只是比較少,布農族能背很重,女性亦然。但受父系社會影響,其重要性被掩蓋,或多擔任山屋廚娘。無論如何,高山協作員因應外來需求,將其山林知識進行調節、適應,甚至轉化,默默成就眾多光榮,然越來越多山友具備基本山野技能之後協作還可擔當什麼要角?以山之名的巡查保育是否為一種納編?都是山林守護者如今面臨的多元挑戰。

百年殘酷,開展跟遺忘抗衡的行動
第二篇〈百年碑情〉,則是2015年大分戰役滿百年時一趟以族人為主的尋根踏勘,從南安登山口出發前往大分,同行16人來自不同氏族、部落,有喀西帕南事件的後裔,也有想回到外公曾居住過石板屋的Sai,耆老或青年為了尋找自己族群的歷史而來。因為「百年可能四、五代,就足夠遺忘一件事。那次很多第三、四代都是第一次回去大分,如果沒回去的話,終究會忘記,年輕人有機會回去一定要把握。」Salizan叮嚀,這也是待登山協會較有規模後將回饋尋根基金之期許,讓更多人返回祖居地。
本篇寫作方法等同,融合行程記錄,進行實地考察及文獻參照,時空交錯的追想百年前布農族反抗的心,但不忘非我族的共時遇難。日本人習慣在事件發生地點設置紀念碑,沿著八通關越嶺道路豎立一座座戰死地之碑,或石碑或石頭堆還有木頭製成,一路約莫有幾十座。

他表示,從紀念碑的名字中,除了刻上日本警察戰死的名字外,也有阿美族或平埔族隘勇的記載,可以看到不同族群曾在這個空間生活的歷史;我們常忘記其他族群的出現,一開始構思拉庫拉庫溪流域擴及其他族群的高山協作為主體,但阿美、平埔族隘勇的背景資料更少,只能從少量文字中推敲來建立整體想像,連結性弱了點兒是下筆時的侷限。交戰廝殺已遠,留存更多問題,要如何不忘且用什麼媒介穿越?
沙力浪再講到山下的紀念碑,像南安管理站前的八通關越嶺道開鑿記事碑,一行「職工人夫 仝 十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一人(人次)」,只有數字,看不到參與者的身份,又像自己村落的太平村建村頌德碑,隱藏的是族人集團移住的悲情。「人們往往去脈絡地選擇認知,比如喀西帕南殺了好多人,真那麼恐怖?布農族為何抗爭?當時被徵召當勞役的阿美族角色究竟是?石碑冷冷冰冰,刻在碑文上的人也是扁平的,反思石碑的故事性,前因後果對照文獻、口述,慢慢浮現活生生的人。」他企圖提供碑文更多不同族群觀點的理解,「讓後人能看到一段立體而全面的歷史故事。」

三石灶生起火,石板屋裡有人
2016年林淵源過世,Salizan一度以為山中的一切都將回歸大自然,沒有人會再回到祖居地,沒想到,第三篇〈淚之路〉卻湧出新生,人慢慢的走回去,漣漪迴響。
2017年,文化部和花蓮縣政府執行「再造歷史現場專案─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舊社溯源與重塑計畫」,中研院團隊著手進行佳心舊社的系統性調查,他因此接觸到重建佳心Istasipal氏族Banitul家屋修復工作,雖是傳統領域但在國家公園裡蓋石板屋?沒想過能發生的事,重新跟高山協作一起工作、圓夢,然後做更大的夢。筆調不同於前兩篇,除詳實記錄修復過程,更說明眾人如何耐心竭力克服內外各種壓力達致目標,那該是使命感的動態灌注,呼應歷史主體性的實踐確立。
1934~1936年間,布農族被迫遷徙至中央山脈接近花東縱谷處,舊社從此荒蕪,佳心族人大多遷居卓清村,Istasipal家族後裔張緯忠現為巡山員,過去常隨林大哥入山,亦醞釀尋根念頭,2014年在大哥的幫助下找到了家族石板屋,爾後公部門及部落經多次討論確定計畫第一年修復以Istasipal遺址家屋為主。然進入實際操作,包括基地大樹的移動、傳統建築的法規限制、建屋工法斷層、現代技術的使用拿捏、人力經費不足、耆老擔心工程打擾觸犯石板屋的靈等問題一一出現,跨部門跨領域不同團隊的磨合考驗直到趨向團結。

修復並非復原,最可貴的是,如此前所未有的「做中學」,對內喚起了參與建造的族人和高山協作,身為Bunun的山林智慧與身體記憶,對外則展現出蓋房的集體意志,去年底石板屋順利落成,今另有修復一座附屬建築的規劃。
Salizan表示,「大家都有變化,像搬運十噸木料、石板的年輕協作,身體再度為家屋所用,他們在工地跟工班閒聊,交換蓋屋心得。或像靈的溝通,我們入山、到營地都會做儀式自我介紹來對話,施工時盡量不要踩到室內亡者,祖先居住過的地方避免喧嘩,自然祖靈和諧。」他肯定這次工作極為重要,體現祖先留下來的智慧,無形中保留了文化資產,成果更是自信心的茁壯,希望佳心經驗有助於發想把年輕人帶回來、根留山上的永續機制,「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時間彈性從事文化工作來支持回部落在經濟生活的現實考量。對長輩的離開也較釋懷,時間終究帶走某些東西,每個年代有他要做的事,年輕世代會用自己的方式做文化復振。」

自2016年,沙力浪又多了一個身分:嘉明湖山屋管理員,對他來說,雖是不得不的生計平衡,卻也是走出書房舒適空間,積累生命經驗之必要篤實。「回部落做族語出版是艱困的,現在一個月十天在山上,收入較穩定。藉一串小米書寫自己、族群、部落的故事,工作方面則跟山發生關係,兩者共同點都回到山。創作來源唯有從山裡面,山是生命的延續、祖先走過的路,想要把這些文化化為文字。」
至於山林解禁,他不免批評,公聽會等會議邀請仍以山友為主聽取意見。「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及「責任」等五大政策,其實是政府面對主張開放的山友的回應,那政府要如何面對原住民族?除了尊敬聖山外,如何與原住民族管理的方式,則完成沒有提到。忽略原住民族的感受,政府不相信原住民共管的能力,也未研擬山屋、林木管理等項目可交由當地族人經營創造多元就業機會的可行性。期透過《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讓更多人知道高山上的行業乃至這塊土地被淡忘的血淚歷史,那麼實現原住民轉型正義才再進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