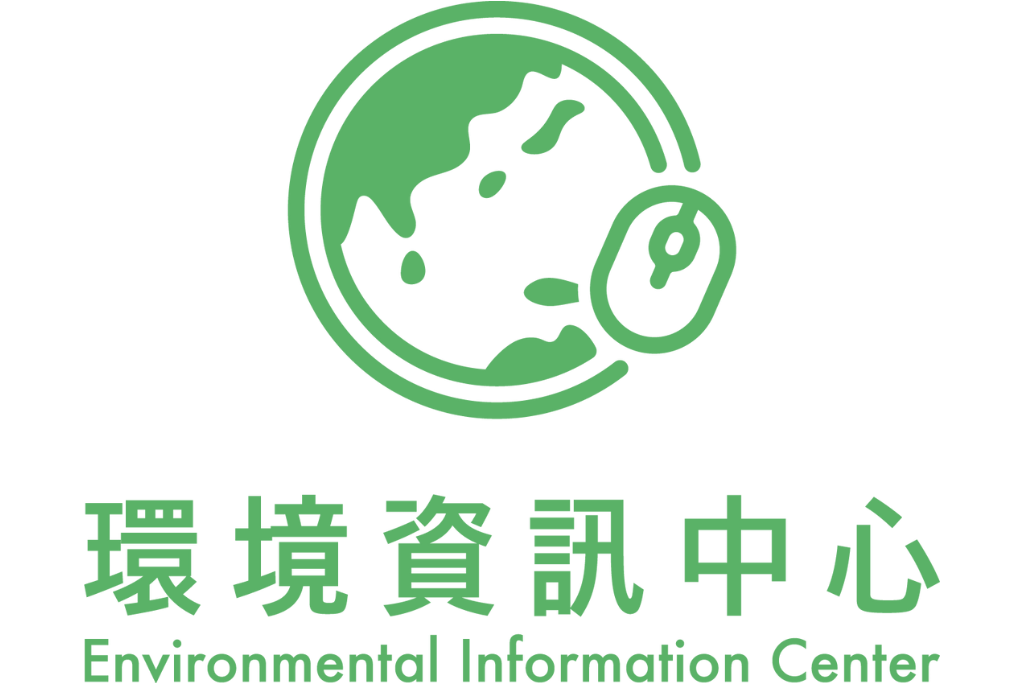李碩認為,《生物多樣性公約》談判應針對執行、專注度等實質問題發力,確保10月昆明大會取得成功。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讓原本定於本月底在昆明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下文簡稱《公約》)2020年後框架工作組第二次會議(OEWG-2)緊急改在義大利羅馬舉辦。這雖然給各方、尤其是主辦方中國,帶來麻煩(中國政府代表團將不得不從本土之外抽調人手參加),但對於昆明進程本身不會帶來實質影響。
與這一插曲相比,確保10月中下旬在昆明舉辦的《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取得實質性成果變得更為緊迫。本次會議肩負著謀劃未來十年生物多樣性保護藍圖的重任。隨著作為COP15成果雛形的「零案文」的發布,目前談判已進入實質性階段。然而,很多困擾《公約》多年的癥結尚未得到有效回應。呼籲系統性變革的「雷聲大」,但反映在實踐上卻「雨點小」。
《公約》誕生近30年積累的弊病,難靠昆明會議一次性解決。在COP15之前餘下的八個月中,處理好三組問題將有助於形成有力度且可執行的昆明成果。
首先,處理好目標設計與實現間的關係。 2010年制定的「愛知目標」已充分證明,生物多樣性有效保護無法只依靠一個「十年願景」而實現。與國際環境治理中具有標竿意義的《巴黎協定》相比,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略顯「骨感」。昆明進程的大部分時間將被用於對目標撰寫的拉鋸。這類似於在氣候進程談判中,只討論1.5°C目標,而不思考國內行動、忽略規則書、迴避資金問題。
為確保昆明大會的成功,執行機制和資源動員問題亟需得到各方更多關注。在此一項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昆明目標」達成後,各國應在最短時間內製定國內戰略,逐一回應兌現昆明目標的計劃。
如果「昆明目標」中設定全球陸地、海洋保護地百分比目標,各國都必須對應制定各自管轄範圍內保護地的百分比目標。這項工作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得以實現的基本前提,但卻沒有在「愛知目標」設定時發生,導致諸多目標成為「孤兒」。
在針對目標設計的談判中,各方不應僅專注於對各個目標撰寫的編輯性工作,而是應以此為契機,更多斟酌目標背後的權力結構,探究目標背後的「政治」,而非僅僅是「政策」文本。
其次,處理好專注度與涵蓋面的關係。 《公約》自誕生以來一直面臨一個尷尬的身份危機。這一危機表現在人們很難像描述《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那樣,說清楚《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焦點」。這一問題的形成,除卻與生物多樣性問題本身複雜、多元的特性相關,也和《公約》多年來「攤大餅」式的議程擴展不無關係。這導致《公約》在試圖應對生物多樣性破壞的不同驅動因素的同時,失去了專注度。
的確,當愛知大會設立20個「大而全」的目標時,它的有效性就難免打折。在下一階段圍繞「零案文」的談判中,各國代表或許應追問自己如下的問題:倘若一個目標難以量化,或其執行進展難以被評估,那麼是否還應設立此目標?如果是,那麼設定此目標能夠帶來什麼積極改變?
專注度與涵蓋面間的張力也表現在《公約》對其「分內」和「分外」議題的應對上。與《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不同,《生物多樣性公約》在國家戰略制定、訊息報告、設定國家目標等《公約》中應履行的「分內」義務上,仍存在各國的執行赤字 。在這種情況下,將有限的資源分散到動員非國家行為體行動等「分外」議題上雖然是有益嘗試,但不乏本末倒置之嫌。在昆明會議的征途上,各方應首先確保落實政府義務這一「必答題」高質量完成。在此基礎上,再去適當嘗試其他「選擇題」。
最後,處理好政治與政策的關係。在目前的昆明進程中,圍繞2020年後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的政策性討論都在緩慢推進。但各方對COP15的契機進行政治層面的動員還顯得準備不足。這首先體現在各方對COP15政治願景的不清晰,尤其是談判過程中尚沒有產出能夠證明昆明與愛知有著顯著不同的、具有說服力的「賣點」。
落到操作層面,隨著一些國家元首對COP15的關注,如何發揮領導人的作用也急需有效的策略。在2019年的一些多邊、雙邊高層外交場合,生物多樣性保護已被提及。但《公約》不應僅滿足於被提及。 2020年的高層外交具體需要解鎖哪些困局、《生物多樣性公約》COP15與《氣候變化框架公約》COP26如何在外交等層面呼應——這些問題都尚待進一步釐清。
綜上,昆明進程應避免點綴式的改變,而需針對《公約》的深層次問題,如執行、專注度等,有針對性地進行政治動員。這應是各國未來八個月的工作重點,也應成為COP15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留下最有效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