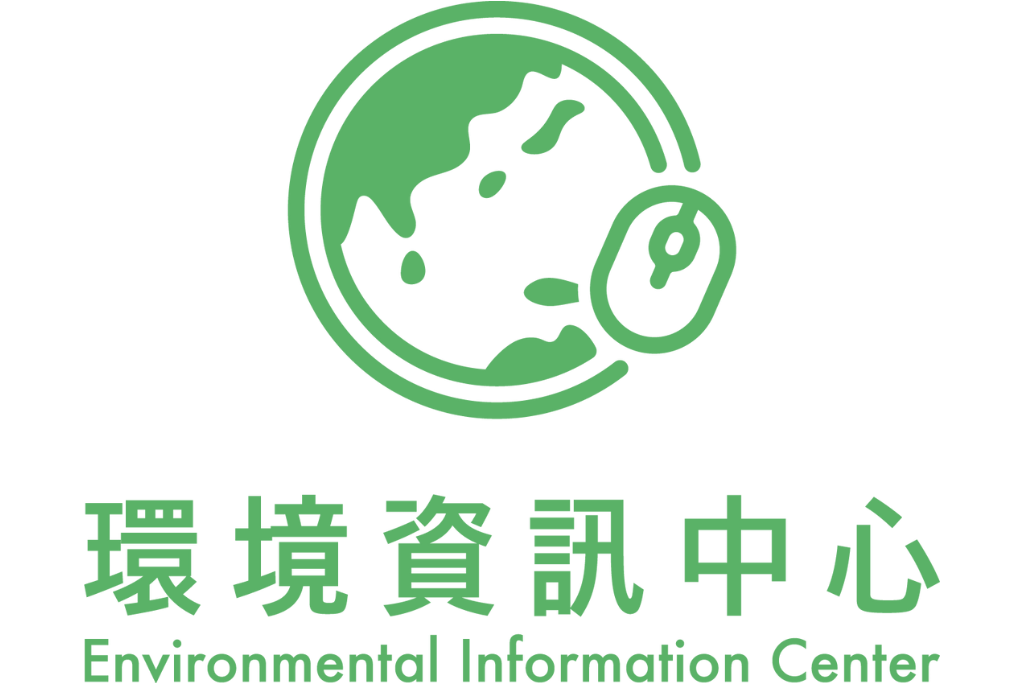劍筍、龍葵、過貓、輪胎苦瓜、珍珠洋蔥等樸素的野菜,不只是養生蔬食,更可能是調適氣候變遷、保障糧食安全的關鍵解方。由台灣大學人類系助理教授羅素玫(Alik Nikar)主講,芭樂人類學、TAAZE讀冊生活規劃的系列講座,第一場「當人類學遇上生物多樣性:阿美族與環境共處的智慧」昨(26日)於紀州庵登場。
傳統環境知識的前瞻性

長期在台東阿美族都蘭部落做田野的羅素玫,研究領域包括儀式、性別,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等課題,近年來更從文化人類學的觸角往生態學延伸,進行文化多樣性結合生物多樣性的跨領域探討,更從1998年開始成為都蘭部落年齡組織拉贛駿組的成員。
阿美族的野菜知識,作為一種原住民傳統環境/生態知識的研究方法,她先就人類學脈絡梳理之,說明「傳統生態智慧」(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Ecological Knowledge)根源於兩個研究取向,其一為「民族科學」,另一是「不同民族對自然過程的理解」。又因晚近這兩個研究取向和其他領域、當代問題整合之應用趨勢,例如生態保育、永續發展、環境資源管理等問題,使得傳統生態智慧愈發成為一個成熟的學科領域。
加拿大生態人類學家柏克斯(Friket Berkes)對傳統生態智慧的解釋——乃一個整合式社會生態體系的觀點,則包含世界觀、社會制度、土地與資源管理系統、土地與動植物的地方知識的層次套疊。此外,羅素玫主要以英國人類學者艾倫(Roy Ellen)的定義來介紹傳統生態智慧體系的特徵,比方殊異於普遍性科學的「在地性」——源自於特定的地方、具有一整體經驗,並且是生活在當地的人所生產出來的;礙難用書寫替代、必須以「口述」的方式做傳遞,或是用「想像」和「示範」的方式。
即便到了今天,野菜雖廣受消費者喜愛仍可能被誤讀成「貧窮食物」,又其知識系統非建構成如現代知識般的百科全書,一般人不容易學習,坦言「它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知識,因此,人類學的語言扮演一個中介。」正是羅素玫給自己置身學術研究、部落田野之間的轉譯定位。

草食民族:就是愛吃「苦」
話及十多年前初進田野,深受「苦」的味覺震撼,其實是一段研究「苦」的經驗,羅素玫笑稱。阿美族最擅長利用野菜,且嗜苦為樂,早期央託族人協助調查,卻常不得其門而入,原來採集野菜的地方屬於秘密基地,她們非常重視野生種源,原住民的環境智慧實際把文化多樣性扣連到生物多樣性,在日常生活裡充分運用在地知識,代代相傳守護。
羅素玫並補充幾個田野觀察,像45歲以上多具備一定的野菜知識,但不採神農嚐百草方法,乃承繼過去流傳下來的既有系譜;最重要的原則是絕不取而竭之,需要時才去拿,不排斥他人使用個人領域(對方通常回贈其他野菜或改良工具),一群人共同採集後無論多寡會再均分,若採多了則分享給親友或年齡階級組織等等文化習慣,在在顯現出「分享」的精神及實踐,蘊藏永續發展之思維。
不過,採集亦包括海洋的定義,她指出,「有趣的是,陸地跟潮間帶採集,都是女性的生態知識多過男性,但一到捕魚區,便又是純男性的領域,鮮少女性。」性別分工區隔分明,導致迥異的傳統環境知識系統。
再者,十年前吳雲月出版的《台灣新野菜主義》蔚為經典,時值今日對照,則可發現名稱、地方的差異性,野菜也有流動性,加上面臨外來種的入侵、原生種的消失,野菜復興不只學採、還可以種回來,歷經遷徙、綿延交換,「什麼一定要保留在園裡?」一塊塊生態農園彰顯著民族的飲食偏好,融入新作物之餘尚須保持生物多樣性,一個季節一小塊地平均至少50種以上植物,然「就算田裡已有山蘇,她們依舊外出採集山蘇,總是野外的比較好吃。」她形容。

土地到餐桌 搶救野菜文化承傳
原住民族主體認同的呼聲益發高昂,並積極文化復振,同時,耆老亦凋零迅速,「需要把傳統說得更清楚。」以前族人與自然關係緊密,能辨識食用的野菜超過200種,因求學、工作等因素人口大量外移,鬆脫了連結土地的臍帶,新生代認得的野菜頂多10幾種,「大家很有危機感,體認到再不藉由文字、影像等不同媒介來記錄,這些生態知識就沒了,而傳承如何發揮創意、活力卻仍保持原有的豐富性?」新工具與時俱進、新生代的參與,所可能造成的原貌改變,所有傳統存續面對的挑戰都一樣。
所以,需要對話、展開行動。比如自1995年起在豐年祭(kiluma'an)前辦理青少年、青少女訓練營(Pakalungay),即為社會文化與生態知識的合作,從中帶動各項文化研習,近年來新添野菜採集。
極端氣候之下,原生野菜也難逃受到影響,「很多植物種不好、種不出來。得做更多事情,除了保種,還要能適應未來環境條件。」最後,羅素玫提醒社會變遷演替,都蘭到台東市僅20分鐘車程,交通方便外來新移民踴躍,往昔土地資源部落共享、採集生態多元興盛,今整個山區幾乎私有化,削弱傳統生態智慧的累積,但新移民不乏友善農業,彼此應該多交流,「人與植物的邊界或關係,開放且通達,外來的因子如何留在生命裡,並嘗試同歷史扣合在一起。」共創都蘭的新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