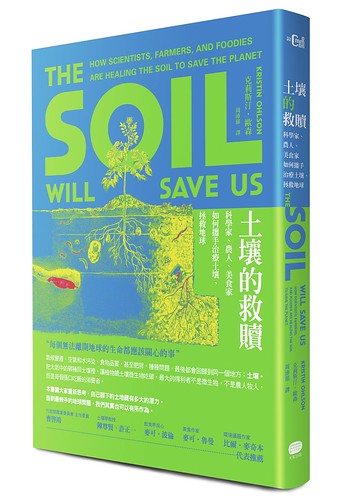我們很容易誤以為土壤碳流失是相對比較現代的災難,是窮國人口躍增、富國實行工業化農業的結果。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人類的生活方式一從狩獵採集演變成農耕,就開始改變土壤和大氣中二氧化碳的自然平衡。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類開始製造簡單的種植、收割工具。最早的工具只是挖掘用的木棍,不過在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河谷已經有人用動物來拉犁了。
犁田看似沒有害處,而且帶著撫慰人心的田園氣息,尤其是用牛或馬來拉犁的時候。不過拉爾在2000年的一場演講中指出:「由於在自然界中,沒有東西會定期、重複地翻起15至20公分深的泥土(犁田就會翻到這麼深),因此植物和土壤生物的演化中都沒有經歷這麼劇烈的擾動,也無法適應。」現代的機械化農業加重了這個問題:重型機具把土壤壓得更緊實,也就需要犁得更深,才能鬆動土壤。更多土壤被翻起、曝露在空氣中,土壤碳接觸到氧,結合成二氧化碳,散逸到上層大氣中。這些碳可能已經藏在地面下幾百或幾千年。

畜牧也打亂了碳的平衡。在人類馴養反芻動物之前,這些動物成群結隊在大草原上漫步,啃食草和其他植物的頂端,殷勤地撒下大量肥沃的糞便回報。牠們害怕掠食者,因此緊緊聚在一起,待在一個地點吃草的時間也絕不會太長。然而人類放牧這些牲畜的模式造成了劇烈的變化。動物不再持續在平原上遊蕩,而是被柵欄限制在一個地區,或在牧人與狗的保護下自在地吃草。在圍起的區域中,以及牧人機警的守衛下,牲畜會把地上的草吃得一乾二淨──既然已不再需要提防掠食者,牠們自然會在同一個地方晃,久到足以將植物的根拔起來。
然而,放任牲畜把草原吃成光禿禿的地面,會阻礙一種偉大的生物過程,也就是當初把碳大量儲存在地下的光合作用。植物吸取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把二氧化碳跟陽光結合起來,轉化成植物可以使用的能量,也就是碳基糖。不是所有的碳都由植物消耗,有些是以腐植質的狀態儲存在土壤中,這個穩定的碳分子網路能在土壤裡留存幾個世紀—拉爾指出,腐植質(humus)和人類(human)有相同的字根。土壤裡的碳有許多好處,包括讓土壤更肥沃,讓土壤形成蛋糕般的質地,內部含有許多小氣室。富含碳的土壤可以緩解乾旱或洪水:下雨的時候,水被土壤吸收、留住,而不是積成水潭或流走。健康的土壤也富含微小的生物(一湯匙裡的數目高達60億),可以分解隨著雨水滲入土壤的毒素和汙染物。拉爾認為農民不該只因為種植作物而得到報酬,由於健康的土壤對環境有益,所以他們也該因為種出健康的土壤而得到報酬。
除了光合作用,沒有其他自然的過程會持續從大氣中移除那麼大量的二氧化碳。人類若要用那麼大的規模來移除二氧化碳,不是所費不貲,就是無法保證安全。光合作用能調控建造生命的碳進入土壤的穩定循環,並產生我們許許多多的生命賴以維生的另一種氣體:氧氣,因此對我們星球上的生命而言,光合作用是最基礎的自然過程。
拉爾和他的同事發展出一種簡單粗略的方式,用來估計美國和全球土壤失去了多少的碳。我到87號樣區拜訪他的時候,他指著緊鄰試驗地一側的黑森林邊緣,說:「那片森林是我的基線。我們計算這個樣區和附近地區的土壤失去多少碳的時候,就是拿那片森林的土壤來比較。」
他得到美國環保局、農業部、能源部的經費,與世界各地的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合作,比較森林地區和農耕地區的碳。按他的計算,俄亥俄州在過去200年間失去了50%的土壤碳。不過世界上農耕了數千年的地區,土壤碳流失的量遠高於此,高達80%,甚至更多。總合來看,全球的土壤失去了726億公噸的碳。不是所有的碳都跑到天上去了,侵蝕也將一些碳沖進了水路。但即使現在,散逸到大氣的碳仍有30%是土地濫用的後果。
而大氣中二氧化碳的量已經達到十分驚人的濃度。2013年,科學家計算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達到400ppm,而許多專家認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應該比這數字低50ppm,才能有適合人類生活的穩定氣候。世界各地都設計、運用了許多乾淨的能源技術降低現代生活方式排放的二氧化碳,從化石燃料到風能、太陽能、生質能、海洋波能,甚至有個異想天開的計畫是利用人群體熱的能量去彌補發電廠不足的發電量。人類也用了許多策略來減少我們消耗的能量,包括提高天然氣汽車的燃料效率、建造產能超過耗能的住宅和辦公室。
然而這些措施都無法實際減少大氣中自古累積至今的二氧化碳含量。據說有因應方案,卻很昂貴—環保局有個計畫是捕捉大氣中的碳,注入深井中,每噸的花費是600到800美元。大自然之母有套低科技方案,在政策制定者眼中沒那麼迷人,不過不花一分錢,那就是光合作用,和隨著光合作用自然發展而成的土壤碳這是我們偉大的綠色希望。確實,我們必須繼續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用較不浪費能源的方式生活,但我們也得和光合作用合作,別再與光合作用對著幹,這樣才能拿回大氣中超量的碳。農人、牧人、土地管理者、都市計畫者,甚至有院子的人,都得盡力讓植物欣欣向榮,不要有大片光禿的土地,畢竟不毛之地無法進行光合作用。我們得照顧數十億的微生物和真菌,它們會和植物的根交互作用,將碳基糖轉換成富含碳的腐植質。我們還得保護那些腐植質,別讓風、雨水、不智的開發和其他擾動給侵蝕了。
拉爾說這辦得到,而最有機會的,就是耕作了數千年、消耗了最多碳的地區,也就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區、南亞和中亞,以及中美洲。他說:「土壤裡的碳就像一杯水,我們已經喝了半杯以上,但我們可以把更多水倒回杯子裡。有良好的土壤施作,就能扭轉全球暖化。」
良好的土地管理措施每在土壤中增加0.9公噸的碳,就表示大氣中減少了2.7公噸的二氧化碳。拉爾相信全球的土壤每年可以隔離27億公噸的碳,使得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每年下降3ppm。不過和我談過的其他人對改變的潛力遠比拉爾樂觀(尤其在我找的人離學術界愈來愈遠之後),他們說這目前還是新觀念,科學才剛碰到邊。
拉爾的研究中心和世界各地的試驗地合作(除了俄亥俄州,還有非洲、印度、巴西、波多黎哥、冰島和俄羅斯),針對除去空氣中的碳、重建土壤裡的碳,尋找不同氣候下的土地管理措施與土壤類型的完美組合。他和同事想出如何在全球各地的生態系重建土壤中的碳,其中甚至包括他早年的剋星,奈及利亞。由於世上有許多微氣候,各有不同的衝擊史、人類史或其他歷史,因此他們採用了各式各樣的方式。有件事放諸四海而皆準,那就是必須建立政治意願。由於種種因素,人類要改變很困難。
拉爾寫了幾百篇論文、幾本書,包括《美國農地隔離碳、緩和溫室效應的潛力》,這本書來到柯林頓總統以及聯合國京都議定書談判美國代表團的手中。拉爾6度在美國國會就此議題發表演說。單單在2011年,就出席了7場國際研討會,解說土壤和氣候之間的關聯。然而拉爾的構想在政策制定者之間並沒有激起多少後續行動。
拉爾說:「土壤的研究對政客沒有吸引力。我跟他們提25年的永續計畫,而他們關注的事每四年就會換。」
不過拉爾和其他土地利用先驅的想法,激發了許多遠見者的興趣和行動。我們目前正在經歷農業的文藝復興。人們開始關注健康、永續生產的食物,對這類食物的需求因此大增,美國的小農數量在大蕭條之後首次成長:2002到2007年之間,小農場的數量增加了4%。這些新的農人通常有大學學歷,採取的農法與畜牧法受到顧客認可。他們減量或不用肥料、殺蟲劑、殺草劑、荷爾蒙、抗生素和其他化學物質,並且讓牲畜吃草,也就是讓牲畜吃牠們演化以來就吃的食物,而不是硬塞其他食物。這些農人常常驚訝地發現土壤變了,顏色變黑了,碳含量也變高了。其中有些農人毫不在乎全球暖化,他們是受到「美國農業事務聯合會」的影響,這個跟產業相連的聯合會宣稱,七成的農民不相信人類造成氣候變遷。不過也有許多農民興奮地發現他們的腐植質有助於隔離大氣中過剩的二氧化碳,他們變成平民科學家,實驗「種植碳」的新方式,也成為創業者,努力思考這種新作物怎麼讓他們獲利。
環境團體也注意到土壤處理氣候變遷的潛力。2010年,世界觀察研究所提出40頁報告,說明土壤和氣候之間的關係。美國野生動物聯盟將全球暖化視為對野生動物最大的威脅,並在2011年提出一份報告,主題是能夠緩和氣候變遷而「對未來友善的農業」。關心環境議題的社群擔心一旦藉著土地利用管理來對付全球暖化,要求能源業與製造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壓力可能就減弱了,因此還有顧忌。不過人們對全球暖化和土壤碳之間的關聯已愈來愈了解,這些知識正讓環境運動發生變革。
這些知識也改變了我和我對土壤的看法。我的祖父輩是農民,父母熱衷園藝,我小時候常聽到他們在討論自己和別人的花園,那是我成長的背景音。我們每次開車出去,都會停下來幾次,到路邊欣賞某戶人家的九重葛或瓶刷樹。每次去州裡其他地方,都會繞道幾次,去他們最愛的果園(「派蒂的完美桃子」,你們還在嗎?)。不論我父母住哪裡,總是有精心照顧的花床、一大片菜園,還有成堆的堆肥。我母親都90出頭了,但若有客人把茶包丟進垃圾桶,她都還會驚慌地從椅子上掙扎起身,說:「我們是這樣做的。」其實那時我父親已過世幾年,已經沒有「我們」了。她會把茶包的線拉開,挖出茶渣,然後把茶包放進她收在水槽下的陶罐裡。她住在老人公寓,有一塊0.27平方公尺的土地,她還會為那塊地做堆肥。她在臨終的前幾天一言不發,家人試圖和她交談都徒勞無功,直到我兄弟戴夫喊道:「媽,我剛種下我的番茄!」她用手肘把自己撐起來,喃喃說:「黑櫻桃番茄嗎?」之前我從農夫市集買了一籃黑櫻桃番茄回家,她從此迷上這個品種。那是她的最後一句話,幾小時後她就過世了。
所以我的出身使我重視土壤,以及和土壤打交道的人。我最早是從一位名叫柯林斯的農夫那裡聽到拉爾的事,他採用拉爾和其他科學家的想法,改造了他的土地,接著成為土壤碳的傳道者。我和柯林斯通電話的時候,他聽起來總是上氣不接下氣,一部分是生理因素──他通常正把他的牛隻從一片牧地移到另一片,或是在處理柵欄,然後跑進來接電話。不過一部分是興奮──自己和其他人竟這麼巧發現了對世界真正重要的事,而他們最好加快腳步,讓大家聽他們說。
但願我能質疑全球暖化,說精確一點,應該是全球氣候變遷,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地球的大氣溫度雖然確實升高攝氏8度,不過並不表示各地都變暖了。其實各地的氣候都變得更反常,極端氣候(例如豪雨和乾旱、洪水和火災)發生的次數增加。我渴望成為所謂的「氣候變遷否認者」,但科學不讓我如願。幾十年前,科學家就開始追蹤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增長。數值節節上升,環境學者兼作家麥吉本2012年在《滾石》雜誌發表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他寫道:2012年5月是「記載中北半球最溫暖的5月,全球溫度已經連續327個月超過20世紀的平均,而這純屬偶然的機率只有3.7 × 1099 分之一,分母的數字遠遠大過宇宙星球的數目」。
不過拍桌定案這件事卻很可悲。讀到北極熊因為結冰的海面逐漸消退而淹死,或聽見氣象學家一季季預報颶風增加了、年復一年宣告當年是有記載以來最熱的一年,總是令我心驚。異常溫暖的冬日或異常寒冷的春天讓我開心不起來,總覺得四季的更迭瓦解了。或在小說、電影裡看到氣候變遷的情節,我都會深深嘆口氣。既然需要重大的政策改變,而政策制定者似乎無法做出果敢的決定,那何必去想呢?一般人的作為顯得微不足道。
不過從25年前我第一次讀到全球暖化的報導以來,我第一次覺得有希望。土壤可以拯救我們。我真的相信。
──摘自《土壤的救贖:科學家、農人、美食家如何攜手治療土壤、拯救地球》
土壤的救贖:科學家、農人、美食家如何攜手治療土壤、拯救地球
作者:克莉斯汀.歐森
譯者:周沛郁
出版社:大家出版
出版日期:2016-08-03
ISBN/ISSN:9789869296168
每個無法離開地球的生命都應該關心的事
人類數千年來的農耕及畜牧,特別是現代的工業化農業,已經導致八成的土壤碳流失到大氣中,即使我們今天就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地球仍會繼續暖化。而現在有許多人,越來越多的人,從科學家到碳農、碳牧人,從碳權交易巿場到環保團體,紛紛放下宿怨,共同走向同一個目標:把碳種回土壤裡,將大氣中的碳轉換成對土地、對所有地球生物都有利的土壤碳,而這還有可能扭轉全球暖化。同時還能賺到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