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輩子感激安吉麗娜.維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輩子!其他人的妻子也來了,但是她們不能進醫院,只有他們的母親和我在一起。沃洛迪.帕維克(Volodya Pravik)的媽媽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換。」負責骨髓移植手術的美國人蓋爾醫生安慰我:有一點希望,雖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線生機,因為他們都還年輕力壯!他們通知他所有親戚,他的兩個姊妹從白俄羅斯過來,在列寧格勒當兵的弟弟也來了。年紀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14歲,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的(沉默)。我現在可以講這件事,之前沒辦法,我十年沒講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們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斷然拒絕,他說:「我寧可死掉。她那麼小,不要碰她。」他的姊姊露達(Lyuda)當時28歲,本身是護士,很了解捐贈骨髓的過程,但是她願意捐,她說:「只要他能活下去。」我透過手術室的大窗觀看手術過程。他們躺在並排的手術檯上,手術一共歷時兩小時,結束之後,露達看起來比他還虛弱,他們在她胸前刺了18個洞,麻藥幾乎退不掉。她從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現在也體弱多病,一直沒結婚。我在他們的病房間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裡,沒有人可以進去。
他們有特殊儀器,不用進入帷幕就可以幫他注射或放置導管。帷幕用魔術貼黏著,我把帷幕推到旁邊,走到裡面,坐在床邊的小椅子上。他的情況變得很糟,我一秒鐘都離不開他。他一直問:「露德米拉,妳在哪裡?小露!」一直問。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員都由士兵照顧,勤務工因為沒有防護衣物,拒絕照顧他們。那些士兵端衛生器皿、擦地、換床單,什麼都做。他們從哪裡找來那些士兵?我們沒問。但是他……他……我每天都聽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諾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錘敲在我腦袋上。
他一天排便25到30次,伴隨著血液和粘液。手臂和雙腿的皮膚開始龜裂,全身長瘡,只要一轉頭,都可以看到一簇頭髮留在枕頭上。我開玩笑說:「這樣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不久後他們的頭髮都被剃光,我親手替他剃,因為我想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話,我會一天24小時都待在他身邊,我一刻也閒不下來。(沉默許久)我的弟弟來了,他很害怕地說:「我不讓妳進去!」但是我的父親對他說:「你以為你能阻止她嗎?她不是從窗戶,就是從逃生口爬進去!」
我回到醫院,看到床邊桌上擺了一顆柳丁,很大,粉紅色的。他微笑說:「我的禮物,拿去吧。」護士在帷幕外對我比手勢說不能吃。已經擺在他的身邊好一陣子,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連碰都不該碰。「吃啊。」他說:「妳喜歡吃柳丁。」我拿起那顆柳丁,他閉上眼──他們一直替他注射,讓他入睡。護士驚恐地看著我。而我呢?我只希望盡可能讓他不想到死亡。至於關於他會死得很慘,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記得當時有人說了這段話:「妳要知道那不是妳的丈夫了,不是妳心愛的人,而是有強烈輻射,嚴重輻射中毒的人。妳沒有自殺傾向,理智一點。」我發狂似地說:「但是我愛他!我愛他!」他睡覺時,我輕聲說:「我愛你!」走在醫院中庭:「我愛你。」端著托盤:「我愛你。」我記得在家的時候,他晚上都要牽我的手才睡得著,他習慣一整夜握著我的手睡覺,所以在醫院裡我也牽著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萬籟俱寂,四周只剩下我們。他專注地看著我,突然說:「我好想看我們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們要替他取什麼名字?」
「妳自己決定。」
「為什麼我自己決定?我們有兩個人。」
「這樣的話,如果是男孩,就叫維斯里,如果是女孩,娜塔莎。」
我當時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樣!甚至感覺不到心臟下面小小的心跳,儘管那時我已經有6六個月身孕,我以為寶寶在我身體裡很安全。
醫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護士讓我進去的。起初他們求我:「妳還年輕。為什麼要這樣?那已經不是人了,是核子反應器,妳只會和他一起毀滅。」但是我像小狗一樣在他們身旁打轉,到門口站好幾小時,不斷懇求,最後他們說:「好吧!不管妳了!妳不正常!」早上8點,醫生開始巡房前,護士會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個小時。早上9點到晚上9點我有通行證。我的小腿腫脹,變成藍色,我實在累壞了。
他們趁我不在的時候幫他拍照,沒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蓋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換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來,他的皮膚黏在我手上。我告訴他:「親愛的,幫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盡可能撐著,我幫你理順床單,把皺的地方弄平。」床單只要稍微打結,他的身上就已經出現傷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會不小心割傷他。沒有護士可以接近他,他們需要什麼都會叫我。
他們替他拍照,說是為了科學。我放聲大叫,把他們推走!捶打他們!他們怎麼敢這麼做?他是我一個人的──是我的愛,真希望可以完全不讓他們接近他。
我離開房間,走向走廊的沙發,因為我沒看到他們。我告訴值班護士:「他要死了。」她對我說:「不然呢?他接收到1600侖琴的輻射,4百侖琴就會致人於死,妳等於坐在核子反應爐旁邊。」都是我的……我的愛。他們都死掉之後,醫院進行「大整修」,刮掉牆壁,挖開地板。
到最後……我只記得零星的片段。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8,我跟他說:「我去散個步。」他睜開眼睛又閉上,表示他聽到了。我走到宿舍房間,躺在地板上,我沒辦法躺床,全身都好痛,清潔婦敲我的門說:「快去找他!他像發瘋一樣一直叫妳!」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諾克拜託我:「陪我去墓園,我沒辦法自己一個人去。」維特亞.克比諾克(Vitya Kibenok)和沃洛迪.帕維克要下葬,他們是我的維斯里的朋友,我們和他們兩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張照片,我們的丈夫都好英俊!好開心!那是另一種生活的最後一天。我們都好快樂!
我從墓園回來後,馬上打電話到護理站問:「他怎麼樣?」 「他15分鐘前死了。」什麼?我整晚待在那裡,只離開3個小時!我對著窗戶大叫:「為什麼?為什麼?」我朝天空大喊,整棟樓都聽得到,但是沒有人敢過來。然後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樓,看到他還在生物室,他們還沒把他帶走。他臨終前最後一句話是:「露德米拉!小露!」護士告訴他:「她只離開一下子,馬上回來。」他嘆了口氣,安靜下來。我後來再也沒有離開他,一路陪著他到墓地。雖然我記得的不是墳墓,是那只大塑膠袋。
他們在太平間問我:「想不想看我們替他穿什麼衣服?」當然想!他們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沒辦法穿鞋,因為他的腳太腫了。他們也必須把衣服割開,因為沒有完整的身體可以穿,全身都是……傷口。在醫院最後兩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覺骨頭晃來晃去的,彷彿和身體分離。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從嘴裡跑出來,他被自己的內臟嗆到,我用繃帶包著手,伸進他的嘴裡拿出那些東西。我沒辦法講這些事,沒辦法用文字描寫,甚至覺得好難熬。都是我的回憶,我的愛。他們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讓他赤著腳埋葬。
他們當著我的面,把穿著制服的維斯里放進玻璃紙袋,再把袋口綁緊,放入木棺,然後又用另一層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紙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後他們再把所有東西塞進鋅製棺材裡,只有帽子放不進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來了,他們在莫斯科買了黑色手帕。特別委員會召見我們,他們的說辭都一樣:我們不可能交出妳的丈夫或你的兒子的遺體,他們都有強烈輻射,要用特別的方式──密封的鋅製棺材,上面蓋水泥磚──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們要簽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議,說想把棺木帶回家,他們會說,死者是英雄,不再屬於他們家了,他們是國家的英雄,屬於國家。(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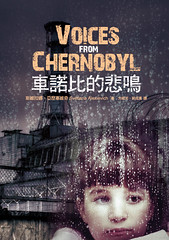 書名:車諾比的悲鳴(Voices from Chernobyl)
書名:車諾比的悲鳴(Voices from Chernobyl)
作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
譯者:方祖芳
出版社:馥林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14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6076220
定價:280元
※不適用CC授權條款,請勿任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