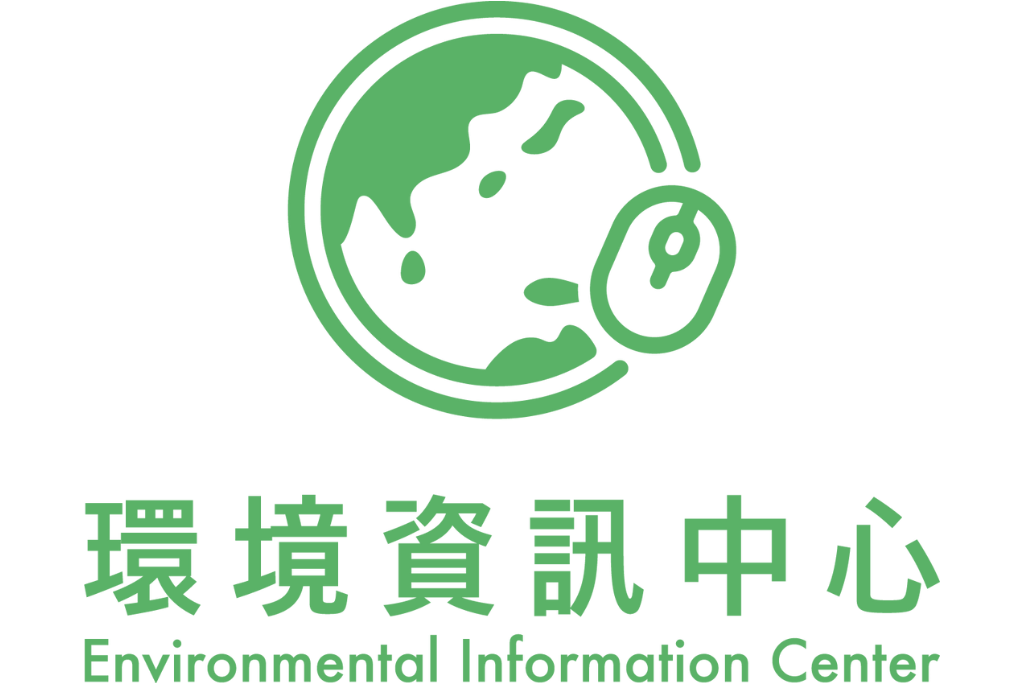環境資訊中心於去年(2018)舉辦黑熊系列講座,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邦卡兒·海放南(以下簡稱邦卡兒)主講「原住民文化中的人熊關係」,並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張君玫教授與談,從保育與原住民傳統文化兩種不同視角探討狩獵議題。兩位講者與現場聽眾擦出許多火花,本文將該場講座重點內容整理如下。
邦卡兒從一張合照作為演講的開場,指出照片中一位叫做「海粟」的前輩(漢名林淵源),他是一位資深的布農族獵人,協助黃美秀教授從事黑熊野外調查,前後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黑熊野外調查依賴繫放的方式搜集黑熊活動的資料,但調查之始,台灣並沒有太多關於「抓黑熊」的資料,於是黑熊調查工作便仰賴布農族獵人以「布農族的方式」進行。在黃美秀的調查中,一共抓過12隻熊,全數都用布農族語命名。
台灣黑熊多半出沒在中央山脈海拔 1000~3000 公尺的山區,邦卡兒說明,台灣黑熊的棲息地剛好和住在高山的布農族、泰雅族,和鄒族等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重疊。其中,布農族是台灣垂直分佈最廣的民族,生息在崇山峻嶺之中,他們熟悉地理、植物特性、動物習性,長久以來便在山林中開展出獨特的狩獵文化與生活智慧,也與黑熊交疊出深遠的共同生活經驗。
布農人看黑熊:友伴、同盟、尊敬、恐懼
邦卡兒出身於布農族巒社群,24歲就進入玉山國家公園任職,玉山山脈、雪霸、太魯閣的山脈他大都爬過,「剛開始進入以前祖父、爸爸、叔叔口中的山,我們也覺得很陌生,」

「我們從來沒有把黑熊當作食物。」邦卡兒開宗明義地說。黑熊之於布農族,就像精靈一般的存在,並不是山羊、山羌一類「看到就可以打」的動物。經過多年研究發現,黑熊獨愛玉山國家森林公園一帶,尤其喜歡在布農族祖居的大分地區出沒。
因為世世代代都和黑熊有所交集,在赤手空拳、獵槍和配刀並不充足的狀況下,布農族自然地發展出對於黑熊又敬又畏的態度。儘管布農族有不同的社群,但是受過嚴正傳統教育的族人們,對身形巨大、力大無窮黑熊所抱持態度是一致的敬畏和禁忌。

在布農族語中,對黑熊有四種不同的稱呼:Tumaz(督瑪斯)、Tutumaz(督督瑪斯,原意為「英雄」)、Dahdung(達動,黑色的意思)、Hanidu(哈尼度,泛指神、鬼、精靈等來無影去無蹤的靈體)。透過這些稱號,大致可以看出布農族對於黑熊的敬畏,「遠遠聽到黑熊的聲音,大概就是要趕快先跑了,絕對不是跑去看熊或是去獵捕牠。」族人聽說黑熊出沒,通常不敢輕易靠近,而且「有熊的地方,通常也沒有東西可以吃了,」邦卡兒說。
熊的身影反覆地出現在布農族的神話傳說、禁忌、家族教誨裡頭,人熊之間的故事在族人之間世代流傳著,遠遠多過其他原住民族。傳說中,布農族人也曾和黑熊一起生活,關係就像夥伴或兄弟一樣,向黑熊學習分食等智慧。
「懶媳婦與小米」就是一個廣為流傳的寓言故事。傳說中,布農婦女只需要用一粒小米就能煮出一大鍋飯,有個婦女懶得只取出一粒米,直接將整把米倒在鍋子裡面煮,沒想到小米飯越煮越多,幾乎塞滿了房舍。眾人配蜂蜜或者其他食物,都吃不完眼前海量的米飯,後來搭配著熊肉吃,才把這麼多的小米吃完。這個故事警惕布農族人:婦女要勤於家事,別為了一時懶惰釀成大禍;而東埔地區的布農族人,也曾傳說因為熊肉太好吃,配著小米卻忍不住將糧食都吃光的故事,因此族人一直把獵捕黑熊視為貧窮的象徵。
因為黑熊兇猛,部落也流傳黑熊吃人的傳說,族人不但恐懼,也相信黑熊是一種禁忌,很多人把獵熊視為不吉祥或麻煩的事情。族人也相傳,如果在種植小米到結穗期間獵到熊,小米結果之後會變黑,像燒焦了一樣。若真的獵到了黑熊,熊肉也不能直接帶進家裡,要放在房子外面,否則以後就會諸事不順。
山林生活發展出深厚且複雜的人熊關係
邦卡兒分享他聽說過的狩獵經驗,據說黑熊是非常聰明的動物,被陷阱夾到之後,牠會躲藏在陷阱周圍,等待獵人回來查看,再趁機將獵人打死、吃掉作為報復。因此獵人對黑熊向來敬而遠之,放陷阱時也格外戒慎。有時,黑熊甚至會觀察獵人設置的陷阱,並且把陷阱當成是現成的「便當」,把落入陷阱的動物吃個精光。

狩獵不僅是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是自我表現、 爭取社會認同的方式,更是文化、祭典的重要象徵。即便部落有獵熊的禁忌,但因為黑熊兇猛且數量稀少,不易捕獲,打到熊又被當作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認為獵熊是英雄的表現。邦卡兒由此點出,早期的原住民族一方面視熊危險而盡量迴避, 另一方面也視獵熊為英雄行為,山林生活經驗使得黑熊和布農族的關係顯得非常複雜。
狩獵文化其實只是「一起生活」的一部分
布農獵人出門前,從不張揚,也不敢做任何像是「我要打五隻山羌、三隻水鹿」之類的目標設定,邦卡兒說,在傳統文化中,打獵的成果是上天給的,心中不能帶任何盤算,就是把自己交給山林、交給祖靈,安靜地出門打獵。姑且不提狩獵的危險,僅僅是出門一趟,就必須經過許多道關卡:出發前做了不好的夢,出發時放屁了,或看見某一種鳥從天邊飛過,也或者是出門後有人打個噴嚏,又或是被什麼東西刺到,按照傳統習俗,都要立刻返家,不能繼續入山。
與談人張君玫回應,布農人原生的知識,視其他生命與自身是相互關連的,在意的是對自然資源的適度利用,非常符合整體生態的概念。在狩獵文化之下,人與動物的關係就是人和不同的生命共同生存於生態系統裡頭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狩獵文化下和在肉品生產線下,動物所過的生活,是非常不一樣的。「然而,原住民文化卻常常成了生態女性主義或動物保護倡議者的代罪羔羊,狩獵被視為『殺生』或是不尊重生命的行為。」她提出反思。

近年也有人對於原住民祭儀「走調」提出批判,認為某些豐年祭活動流於形式或是傷害動物。張君玫認為,「評判他人」這件事情,在台灣社會中經常發生,身為動保倡議者,她認為「吃肉」本身不一定是件錯誤的事。人類祖先利用動物的生活方式由來已久,而「吃肉」之所以成為環境負擔,根本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系統下肉品的生產方式。她認為,過一個合乎「生態合理」的生活、與其他生命共存,或許是更務實的思考方向。
如何在現代生活傳承傳統狩獵文化?
幾位講座參與者對於傳統狩獵文化的傳承表達關切:現在漢人和原住民處在同一個教育和生活環境中,該如何傳承祖先和自然共存的傳統智慧?
邦卡兒說起自己的生命歷程,「從小不敢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只想要把國語說好、把學科學好,以免被貼上『山地人』的標籤」。直到年,他才發現「啊!原來獵人很重要,原來我的文化很重要。」現在政府推動原住民實驗小學、族語認證、加強文化傳承等措施,他認為已經為時太晚。他舉自己改回傳統姓名為例,當他將名字恢復成「邦卡兒・海放南」之後,便遇到許多困難,「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才完全將和姓名有關的事情改過來,包含身分證、職章、護照、存摺、戶籍資料......」,光是改名字已經這麼繁複,更不用說是悠遠又複雜的狩獵文化了。

回復狩獵文化的議題,首先是為時已晚的困難,同時也會面臨來自其他領域的壓力,諸如宗教團體、動物權團體等等。再者,若要讓孩子學習原民傳統文化,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壓縮「正規」教育的時間,父母難免會擔心孩子跟不上一般學生。面對主流社會,如何不讓傳統成為現實生活的負擔,至今還在拉扯著。
張君玫認為,原住民族的知識系統確實帶給人們很多啟示,然而,另一個陷阱是把原住民文化浪漫化──一旦認為原住民族有義務要體現、維持傳統生活的樣貌,便形同是一種物化。傳統與現代互動,勢必會不同於以往,而歷史結構的不正義、個人主義式的競爭都會對原住民族的生活造成莫大的影響。從文化多元主義的觀點出發,她特別提醒:不同民族必須有意識地保持「一起生活」的覺知。
過一個「生態合理」的生活
「如果原住民持有更強大的工具,例如火槍等等,是不是會改變布農族對於黑熊的敬畏?」邦卡兒回應,打到黑熊這件事情在布農族中不是沒有發生過,但他舉出布農族打到黑熊的「後果」還可能會讓家族女性不孕,造成斷子嗣的後果。一旦不能傳宗接代,就等同是家族的滅絕,他認為即使擁有進步的工具,布農族還是會把打到黑熊視為禁忌。
科技和自然科學發展帶給人類的另一個反省就是「當你知道越多,你就會發現自己不知道的其實更多」。布農族害怕黑熊,其實也可以視為原住民知識的一部分。有機會退一步看未知與不足,才能和其他生命共同生活著。
在原住民社會中,黑熊不只是是受到敬虔、禁忌的動物。黑熊也存在於原住民無形的空間之中,在文化裡頭,在古老的傳說中。演講最後,邦卡兒以一首詩作結:
黑熊是原住民生命中的一部份, 牠是神話中的生命文學, 牠被視為與人甚至比人更高一級的生命體,不敢去獵捕,也不敢正視牠, 牠帶有不可侵犯的靈形, 牠像風一般的遊走在山林中, 進入那濃霧的氣息, 牠隨時會出現在 石頭、 枯樹、 岩石或是樹梢上, 牠深邃的眼眶看透你的動向, 在你刀鞘移動剎那, 牠已離開好遠好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