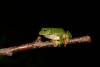新冠疫情敲響了人與自然關係失調的災難性警鐘,但旨在修正這一關係的「全球性框架」,在疫情影響下卻步履維艱。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因新冠疫情推遲至2021年5月在昆明舉行。各國還有8個月的時間,來決定2020後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昆明大會將制定一份未來十年的藍圖,確定203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和方向。
目前最新一版草案(0.5版)令外界普遍有些失望。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國際政策副總裁蘇珊・利伯曼(Susan Lieberman)告訴中外對話:「所有國家政府都說他們想要一個有雄心的東西,但開始談判後,雄心卻了無蹤影」。她指出草案並沒有提到保護區的有效管理,新冠疫情和野生動物貿易也沒有得到應有重視。
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OEWG)共同主席之一巴西爾・範・阿弗爾(Basile van Havre)對中外對話表示,在疫情威脅人類自身生死的問題面前,生物多樣性危機很容易被忽視。
談判進度不如人意,自然將人們的期望導向主辦國——中國。這是中國第一次主辦如此高規格的多邊環境會談。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UNSDSN)執行主管吉多・施密特-特勞布(Guido Schmidt-Traub)告訴中外對話,中國無疑會在昆明行程中扮演一個中心角色,但主辦COP15對於中國也是一個風險——就像每一個快速發展中的國家,中國面臨著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巨大挑戰。 「儘管如此,中國依然同意主辦,這足以表明中國對生態文明的承諾。」
2015年,法國作為主辦國促成了歷史性的《巴黎氣候協定》達成。 2021年,中國可以為生物多樣性進度注入什麼樣的政治動力?
目標:兼具雄心與實際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從1992年公約誕生起,已經走過了將近30年。雖然各國的政治承諾、資金投入和努力從未停止,但全球生物多樣性還是在急劇喪失。巴西爾・範・阿弗爾強調,昆明大會的里程碑意義在於其是對人類保護自然的路線進行一次「總修正」。但他同時提醒,對於今年的談判,要考慮到疫情給外交造成的困難。隨著會議一個個取消和延期,像往年那樣的各國代表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也沒了。
在距離昆明大會開幕這8個月間,只剩下一場討論草案的OEWG會議和兩場技術性會議。這些會議最終是否能如期召開,還要視疫情而定。然而各締約方對昆明目標的訴求,仍分歧重重。
談判核心在於平衡體現公約三大目標,即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永續利用和惠益分享。由英國、哥斯達黎加和芬蘭等國創建的全球海洋聯盟(Global Ocean Alliance)支持到2030年保護30%的海洋,即「3030」目標。但一些國家對此持保留態度。目前,全球僅有7.45%的海洋面積受到保護。
「科學結論是很清晰的,我們需要保護至少30%的海洋。當然我不會說,我們知道了所有東西。但是,目前所知已足夠讓我們採取行動。——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國際政策副總裁蘇珊・利伯曼(Susan Lieberman)」
除了「3030」目標這樣的明星議題,公約三大目標下還有一些具體議題難以達成共識。例如,關於生物基因資源的獲取和惠益分享,一些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核心爭議點在於遺傳資源的衍生物(如基因序列數據)是否應納入惠益分享。綠色和平東亞區全球政策高級顧問李碩認為,這不是COP15所能解決的問題,締約方很可能會在昆明通過一個程序性決議,留待以後繼續談。
外界認為,作為主辦國,中國有著巨大空間來發揮影響力,以促成強有力的「昆明目標」。在2019年11月中國和法國聯合發表的《中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遷北京倡議》中,雙方宣布要在吸取上一個十年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制定和通過一個兼具雄心和實際的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而兼顧「實際」的潛台詞,就是中國對一些核心議題仍持保留態度,尤以海洋「3030」目標為代表。生態環境部自然生態保護司副巡視員、COP15談判代表劉寧在7月末的一場網絡會議中表示:中方正積極參與海洋保護目標的全球磋商,具體目標需要先完成科學論證,目前的研究結果還不充分。
「我認為科學結論是很清晰的,我們需要保護至少30%的海洋」,蘇珊・利伯曼說,「當然我不會說,科學研究已經完結,我們知道了所有東西。但是,目前所知已足夠讓我們採取行動。」
全球海洋有61%是國家主權管轄範圍之外的公海,設定具有雄心的全球海洋保護目標,勢必觸及公海海域管制這一棘手問題。中國作為主辦國,將以何種姿態影響海洋「3030」目標的最終產出?無疑是昆明大會的一大重點。 「如果只有一個目標是在昆明最後24小時需要解決的,那就是『3030』目標。」李碩說。
資金和執行
除了目標,在資金和執行層面,各方訴求也是「眾口難調」。開發中國家提出需要更多資金。在今年2月的羅馬OEWG會議上,巴西就提出要求增加資金,作為對其保護亞馬遜雨林的補償。非洲國家要求建立一個專門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基金,作為對現有資金機制的補充。
但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到底能動員多少資金,前景不容樂觀。況且資金從來是所有環境治理機制的痼疾。蘇珊・利伯曼希望人們不只是看哪些資金用於投入保護,還要看哪些資金流向生態破壞——比如漁業補貼。 「如果能停掉這些破壞性資金,本身就是很大的保護行動了。」她說。吉多・施密特-特勞布則一直在呼籲將氣候和生物多樣性議題協同解決,他認為,當前氣候領域動員到的很多資金,可以惠及生物多樣性保護。
作為慣例,COP主辦國往往會自掏腰包設立一個東道國基金,來促成COP目標的達成。德國在COP9之後投入8億歐元支持了30多個子項目的實施。日本在COP10《名古屋議定書》談判陷入僵局的最後時刻,拿出主席國提案,承諾出資10億日元建立「日本生物多樣性基金」,還另外增資10億日元幫助開發中國家進行能力建設。專家透露,目前中國正在醞釀東道國資金方案,並已就其開始徵求意見。

但生物多樣性公約最大的軟肋在執行。吉多・施密特-特勞布向中外對話分析,公約執行弱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在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管轄之外,比如農業、工業、城鎮發展和氣候變遷,需要跨部門協調政策,這樣一來治理機制就會變得冗雜低效。另外,公約只有全球層面的20個目標,從未像《巴黎氣候協定》一樣在一個溫控目標下要求各國設定國內目標。於是,締約方最終提交的各自的國家行動報告,就像蘋果、香蕉和桃子,完全沒有可比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一旦昆明目標達成,每個國家就要基於所有目標,一一制定國內目標。這樣最終才能把各國行動整合到同一頁紙上。」李碩說。
但吉多・施密特-特勞布認為,這在昆明不會發生,剩下的談判時間不夠了。在他看來,不要過於具體地去圍繞執行機制進行談判,因為這就會觸及國家主權和知識空白。 「我們並不確切知道如何解決生物多樣性危機,還是需要很多創新『來解決問題』。」他認為,應在昆明製定出強有力、清晰的目標,至於執行,則不是公約現有框架可以解決的。
領導力:東道主的考驗
舉辦一次成功的COP,對東道主的考驗體現在三個層面:政治意願、外交能力和後勤實力。沒有人會懷疑中國的後勤實力。 「這不是一個小任務。辦好會務,對於促進磋商非常有用。」 巴西爾・範・阿弗爾說,「在我看來,毫無疑問中國將會把會務安排得很好。」
COP15的主題是「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這恰可以體現中國由內而外的政治驅動力——「生態文明」自2007年首次在中共「十七大」被提出,後來被提升到國家戰略。而2020年是中國「十三五」收官之年,意味著生態文明示範體系得以全面構建。可見COP15對於中國來說,有著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重大意義。
但領導力體現的關鍵,在於如何在外交上合縱連橫,讓196個締約方最終能夠達成共識。
一位正在跟進公約談判的資深觀察員向中外對話表示:「中國有了一個很好的主題,但至於中國想要全世界196個國家一起達成的東西是什麼?我們還沒看到答案。」比如說,歐盟最近發表的「2030生物多樣性策略」,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歐盟的目標和雄心。
不只是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國在環境外交上一貫保持著「低調」風格。在以往的「客場」談判進度中,中國很少提出自己的創見。但這次做主場,繼續「低調」,有可能被認為主席國缺少雄心。
外界期待中國可以更加清晰地去表達自己的立場。而生態環境部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研究人員朱爭光告訴中外對話:「中國不輕易表態,所以你只能從一些公開發表的蛛絲馬跡中了解到新進展,不然大家也不會在不同場合去試探中國的觀點。」
中國對於昆明成果的現實性考量,除了自身的一些保留外,還包括對其他締約方立場的照顧,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關於資金和義務的關切,一位參與協調中國與其他締約方交流的專家告訴中外對話。
謹慎的姿態,也源自中國的履約機制和能力。中國為昆明會議專門組建了COP15籌備機構,涉及20多個部委。協調立場並清晰地向外界傳遞中國的想法是一件充滿挑戰的事。一些參與和接近COP15籌備的人士普遍認為,展現東道國的領導力需要能力和技術支撐。雖然參與籌備的每個部委都有專人負責履約工作,但形成合力需要更多努力。
朱爭光曾代表中國參與過《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談判,他告訴中外對話:「我們還需要動員更多人員和機構,壯大中國履約團隊,更好地發揮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作用。」 對此,蘇珊・利伯曼認為,非政府主體,如NGO等可以彌補這一點。
巴西爾・範・阿弗爾建議,中國可以展開像法國在巴黎氣候大會之前類似的「外交攻勢」,而且「必須是部長級別以上的、非常高層的外交。」 他認為,「作為主辦國來說,一個優勢正是他們可以從現在開始,在談判進度外影響別的國家。他建議,中國可以考慮與一些關鍵的國家直接接觸、來創造政治雄心和一個容易合作的國家聯盟。即將到來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和IUCN世界自然保護大會就是很好的機會。
「我認為中國在外交上處在一個獨特位置」。巴西爾・範・阿弗爾說,中國的一個明顯優勢是能更容易說服一些仍持保留態度的開發中國家。
留下中國印記
除了外交斡旋外,專家認為作為主辦國的中國還可以為進度貢獻獨特的創新。
吉多・施密特-特勞布說,中國的國土空間規劃體係是解決生物多樣性執行困境的創新性思路。今年7月,他與生態環境部下屬科研院所、中科院以及來自加拿大、哥倫比亞等國的研究人員共同發表的論文認為中國的國土空間規劃體係與其中的生態紅線制度,非常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有一個國家能夠提供保護生物多樣性領域(跨部門)融合的範例,那就是中國。」他說。
他認為中國的國土空間規劃,是可以同時實現氣候、生物多樣性和荒漠化治理目標的一個融合工具(integration tool)。其邏輯是,無論是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還是荒漠化,問題產生的根源都在於人類對地球空間的利用。對一塊土地施行何種管理,既可能實現生物多樣性和減碳的協同增效,也可能顧此失彼。只有進行整體考慮,才會在永續發展目標下、實現土地管理的最大環境效益。
目前中國劃定的生態紅線約佔國土面積的1/4,且一旦劃定,只能增加、不能減少。除了生態紅線,中國還有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兩條空間規劃「紅線」,通過恪守這些不可逾越的控制線來夯實永續發展的基礎。
作為中國「十四五」規劃(2021-2025)的一部分,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從生態、農業、城鎮、工業、基礎設施等方面對中國未來的土地利用進行戰略規劃。這個框架由自然資源部單獨負責。因此對於生物多樣性治理機制來說,這個工具有很高的可執行性,有助於解決其跨部門協調成本高、效率低的問題。
「據我所知,只有中國在這麼做。」吉多・施密特-特勞布說。他建議中國宣布將生態紅線制度和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納入中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並且也在生物多樣性和防治荒漠化公約下提交這些文件,從而為其他國家學習和效仿。他還希望,中國能鼓勵「一帶一路」合作夥伴和主要大宗商品供應國在上述公約下,採用類似的土地利用規劃框架。
此外,與對海洋「3030」目標的謹慎態度形成對照的是,近年來中國對海洋保護的投入力度顯著提高。 2016年國家海洋局發文要求海洋生態紅線區面積佔沿海各省(區、市)管理海域總面積的比例不低於30%。近期,中國將海洋保護的政策拓寬至公海,首次在西南大西洋和東太平洋兩個區域實行公海休漁三個月的政策,以保護和恢復魷魚資源。
「這說明中國已經開始使用『其他有效的地區保護措施』(OECM)來參與海洋保護。「朱爭光告訴中外對話。海洋保護區是保護海洋的核心工具,而OECM是除海洋保護區外、也能帶來保護效益的工具。目前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還在探索OECM的路徑。 「中國正在努力用OECM貢獻中國智慧。」他說。
「其他有效的地區保護措施」是指「保護區以外的地理定義地區,對其治理和管理是為了實現生物多樣性就地養護的積極、持續的長期成果,並取得相關的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以及在適用情況下實現文化、精神、社會經濟價值和其他與當地相關的價值(《生物多樣性公約》,2018)
在距離昆明大會還有8個月、新冠疫情仍肆虐全球的關鍵時刻,生物多樣性進度需要一個堅定、有雄心的領導者。 「我現在最希望能讓中國大聲說出昆明應該產生什麼成果。」蘇珊・利伯曼說:「全世界都會聆聽的。」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中國能否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進程貢獻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