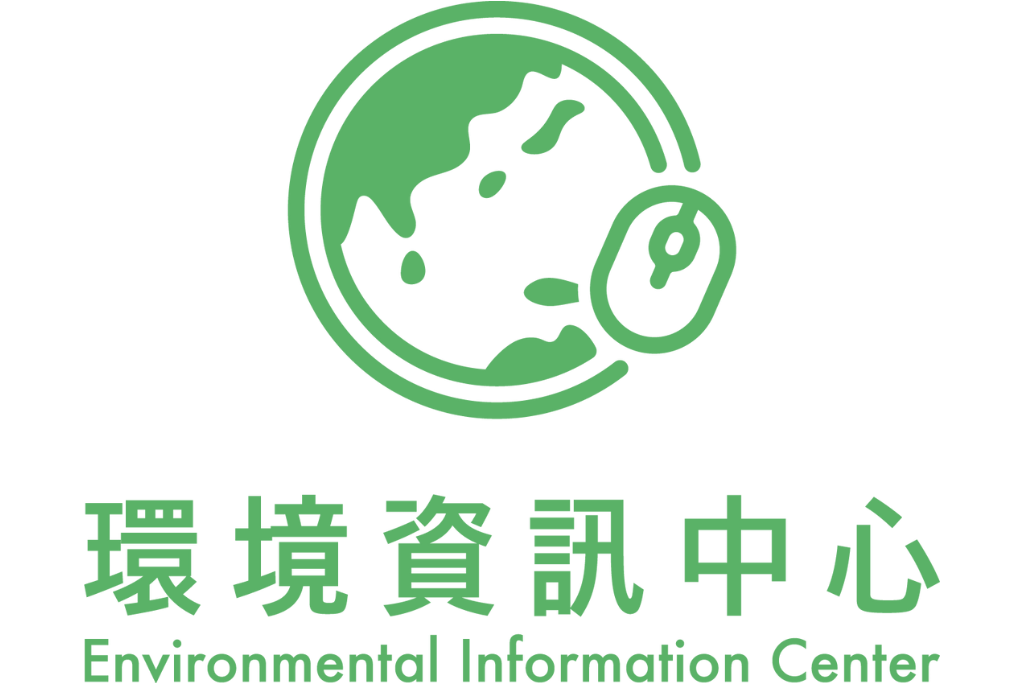編按:氣候變遷議題炒得如火如荼,幾乎成了全民常識,但與其重要程度不相上下的生物多樣性卻乏人問津,原因何在?2010年5月,聯合國發布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正式宣告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失敗;當月,科學家則成功利用人造基因,做出了細菌細胞。人類科技的進步對生態保育來說究竟是福還是禍?清大生命科學系的吳文桂教授在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七月時舉辦的《生物多樣性講座》上,提到應找出生態系統的「具體」價值,不禁讓人思忖: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究竟能不能使用共同語言來找出對話空間?
因此,自本週開始,生物多樣性專欄將以數篇專文,和您一起探討生物多樣性的真實價值。
關心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會點頭說:「是的,我們的地球遭到很大的破壞,每個人都有義務保護我們美麗的地球!」但是,環境保護與經濟效益的衝突一再上演,有多少聲稱要愛護地球的人挺身站在地球這一邊呢?只要牽涉到經濟,就好像踢到鐵板,讓環保人士只能扮演與所謂「經濟發展」敵對的角色,少了許多進行抗爭的正當性。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的吳文桂教授提出了這個問題,從他做研究的經驗當中發現,生物多樣性有「非常大的價值」,他引用了今年(2010年)7月8日《自然》雜誌上的報導說明,生態環境系統的價值是隱而不顯的,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從小範圍開始,找出生態系統的「具體」價值。這樣將可大大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說服力。

窺見一斑:研究蛇毒的發現
吳文桂老師原本是一位物理學博士,後來的專長則是生物物理、醣生物學以及細胞膜學。回國之後做蛇毒的研究,因此發現蛇毒的種類其實多得驚人。即使同樣是眼鏡蛇,台灣西岸的眼鏡蛇與東岸的眼鏡蛇具有不同的蛇毒,甚至隨著北、中、南的分布也有差異,陽明山的蛇又自成一格,和東岸與西岸都不相同。更令人意外的是,連生物學方面的專家都不知道蛇毒有那麼大的差異性。
「光是東岸的眼鏡蛇,就有二、三十種蛇毒!每一種毒的結構不同,目標不同,可能在獵物身上的作用也不同。以眼鏡蛇來說,光是心臟毒蛋白就有六、七種之多!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種功能類似的毒同時存在?爲什麼蛇會需要那麼多種不同的毒?我們不知道。但是能夠在演化過程中保留下來,必然有它的作用,只是我們對這個部分所知仍然少得可憐!」只不過是一個物種當中一小部分的分子結構,都蘊藏這麼驚人的多樣性,更不用說是整個生態系統了,就算用宇宙的浩瀚來比擬也不為過。

了解一滴水≠了解一座海洋
「我們人類對分子生物的領域還是很陌生,對生物體的分子功能了解得很少。」這不是吳文桂老師獨有的喟嘆,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也有同感。
在今年六月的《自然》雜誌上另外有一篇報導,提到歐洲青蛙受到一種真菌的感染,一位西班牙的演化生物學家試圖在馬約卡島上把一個池塘的水放乾,對蝌蚪施以藥劑,希望可以徹底清除病原體。但是他卻發現,雖然隔年感染病原體的青蛙數量少得多,卻仍然有青蛙受到感染。在嚴密的監控下,病原體是如何存活的?它們的哪一種基因造成傳染性的變化?青蛙的身體對這種病原體又如何反應?科學家也只能說:「我們不知道。」因為在分子生物方面,無法掌握的因素實在太多了。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實例,告訴我們生物多樣性的內涵仍是一塊近乎空白的邊疆地帶。
但是,現在的生物科技不是已經進步到可以複製生物體了嗎?不是已經可以製造出人造細胞了嗎?就在今年五月,美國科學家才宣布成功製造出第一個人造細胞,所有的基因全部都是合成的。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期望將來或許有一天,人類可以將已絕種的生物再製造出來,如此一來就不用擔心物種滅絕的問題了不是嗎?
在上個世紀科技烏托邦的想像中,只要擁有完備的知識,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複製任何相同的生物群落及生態系統,因此人類可以在地球環境瀕臨危機的時候移民到月球或火星上去。但是目前已知的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的知識距離完備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撇開研究倫理的問題不談,參與研究的科學家也表示,人造細胞的實驗只是證實了體外合成基因是可行的。人類已經可以做到確保基因的序列正確,以及控制細胞壁的種類,但是對細胞內部基因的互動還是完全不了解。
重新評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前面所述的各項研究都指出我們在分子生物的層面上所知極為有限,是不是有很多複雜的生態互動在被我們了解之前就因環境破壞而消失了呢?只要提出具體的證據,說明保存這些尚未被發現的寶藏有多重要,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環保經常被企業和政府視為經濟展的阻撓,白海豚必須為國光石化轉彎,農民必須為科技園區開發案放棄生活耕作一輩子的土地。對環境極度漠視的粗糙思維來自對生物多樣性價值的盲目。如果要與政府或企業家對話,就得用他們能聽懂的語言。光談生物多樣性的學術價值與精神價值是沒有用的,必須把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估計為有形資產,才能掌握更有力的談判籌碼。(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