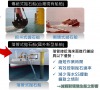安迪‧史特靈(Andy Stirling)教授專訪
拿掉標籤偏見,才能好好談能源

對綁著率性馬尾的史特靈教授來說,科技選擇背後的政治運作不僅無須迴避,還是他的研究興趣。自1980年代參與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能源倡議運動,到走上科技與社會的研究之路,他從未遠離能源政策的領域。在學術本業之外,他參與過歐盟能源顧問委員會(EU Energy Consultative Committee),並在2018年加入由獨立能源專家施耐德(Mycle Schneider)領軍的《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撰寫團隊。去年底,這份報告也被譯介到台灣,引起不少討論。
聽到台灣核能擁護者將報告團隊貼上反核團體標籤,他並不感到驚訝,帶著笑容回應:「《2018年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對核能是批判的,我個人的態度也是,但我不是原則上反對核能科技。身為30年的能源學術研究者,我的研究讓我看到這個能源選項真的不甚理想,因此有所批判。這不代表我想把核能從所有的場合中抹去,而是表示我對核能有疑慮。」
而他的疑慮之一,便是核能辯論常存在「核能至上」的偏見,以貼標籤的方式來壓縮理性討論各種能源的空間。
「當你的研究對核能提出疑慮,就會被貼上『反核』的標籤,因為你沒有說『核能是唯一解方』。」他感嘆道,在英國的能源辯論中,光是提出問題,就可能會被稱作「反核」,在決策中被邊緣化。這讓相關學者只敢討論「我們需要多少核能」,卻不敢問「或許我們可以完全不要核能」。
「將能源辯論定義成擁護或反對某種能源,就表示討論走向有些問題。」他提醒,關於能源的辯論,就像關於其他科技的辯論,應該是檢視「多種」科技的可能性,找出「什麼是生產永續、零碳能源服務的最好方式」,而非侷限於「擁護」 或「反對」某一特定能源。
貼標籤的手段在核能爭議的歷史中並不罕見。他認識不少能源經濟學者曾因對核能成本的估算比核工業預測得更高,被貼上反核標籤,但後來證明這些學者其實還低估了核能的真實成本。「因此很有趣地,這些當初在英國或其他地方被稱為『反核』的人,現在回頭看其實對核能還很友善、太過樂觀。」
他認為,要跳脫標籤口水戰、找出關於核能最可信的說法,可以比較不同立場過去對核能的宣稱,與今日事實的差距。
「如果回顧核工業自己的歷史紀錄(track record),你將屢屢發現,當初核能產業信誓旦旦的宣稱,最後證明是錯的。」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支持十年前核工業或核能支持者提出的論點,因為不管是在核廢料處置、興建速度和費用、低碳表現、經濟效益、核武器擴散等面向,當初的承諾及預測一再跳票。
相比之下,儘管《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也有需要修正的時候,但仍是關於核能產業最具權威性的描述。就連前世界核能協會(the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資深主管Steve Kidd也不得不承認:「像《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這樣經過充分研究、對核能復興之說——尤其是核能緩解氣候變遷扮演重要角色——提出的批判,已經越來越難被忽視」。

根據去年底出版的最新《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全球50座興建中的核電機組裡,至少有3座無法如期完工, 15座過去一年裡傳出進度再次落後。而原本計劃於2017年啓動的16座機組中,僅有4座機組順利與電網併聯,另有多國的新建計劃被取消,或受到延宕。相對於2017年全球核電發電量僅增加1%,風力發電增長了17%,太陽能更大增35%。與10年前相比,非水力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力已經成長超過3兆度,與衰退的核電新增電量呈明顯對比。
全球市場訊號:核電昂貴,缺乏經濟可行性
如果擔憂這份報告或任何核工業的主張帶有立場偏見,他建議讀者可以直接參考無能源偏好、獲利至上的商業投資分析。在此,核電的經濟表現也遠遜於再生能源。不但Google和蘋果等龍頭企業紛紛加入RE100(100% Renewable Power)倡議,商業媒體彭博社發表的《2018年新能源展望》報告也預估,2018到2050年間全球將有8.4兆美元投資在風力與太陽能,遠高於水力及核能等其他低碳能源科技的總投資額 (1.5兆)。若加上預估5480億美元的電池儲能投資,未來「再生能源可望吃下更多燃煤、燃氣與核能的既有市場。」
相較於核能成本因電廠工期不斷延宕、經費不斷追加與核廢料處置預算難以估計,而逐年上漲(如下圖),「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為再生能源成本快速驟降的發展感到驚訝,特別是離岸風力,這重塑了能源辯論。因此,目前關於核能的爭議,已經不太需要再去爭辯核廢料儲存或是風險的細節,因為當今核能的成本已明顯至少是離岸風力的兩倍以上,而且不管你對興建速度的假設為何,核電廠的興建速度確實在放緩。」

「今日核能的主要問題是成本太高,太過昂貴。」史特靈教授表示,目前核電價格通常沒有包含核廢料的處理成本,就算核工業宣稱已解決核廢料問題、做到零處理成本,核電成本競爭力仍然遠遠比不上再生能源。
他認為,依照目前全球市場訊號,核電退場的壓力不斷上升,而新的分散式能源系統正在迅速崛起。就算不刻意廢除核能,核能也越來越難跟上能源轉型的潮流:從經濟可行性來看,嗅覺敏銳的資本家已站在再生能源這一方;而從多元與能源安全的角度來看,再生能源涉及多種科技,更不用擔心「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問題;論能源多元組合,核能無法快速升載且機組龐大,不易融入再生能源的彈性電力系統;從電網管理效益來說,廠網分離已成趨勢,連向來保守的英國國家電網公司也放棄了「基載」的陳舊概念,擁抱不太「適核」的智慧電網。因此,核電的發展在許多國家陷入困境並不令人意外。
例如荷蘭政府雖然不廢核,但 2012年能源公司提出的新廠興建計畫即因財務危機、成本過高、且電力市場供給過剩等原因中止。而荷蘭境內唯一座核電廠(Borssele)近年虧損連連,讓投資及營運公司相繼陷入財務危機。若要讓核電廠轉虧為盈,電價可能必須上漲一倍。2018年,精打細算的荷蘭政府為了減少民眾的電費負擔,並考慮電廠設施的長期投資報酬率,決定以大型離岸風電計畫來淘汰煤電。[註]
在台灣,儘管民眾對於核電廠預算不斷追加的現象並不陌生,核電成本被低估的批評也沒少過,核電便宜及再生能源昂貴的宣稱依然非常普遍。
但跨國企業、全球市場、和許多國家的政府已經以投資行動推翻這樣的過時印象。如今市場訊號如此清晰,「台灣能夠自外於這些世界趨勢嗎?」史特靈教授問。(系列專文1/3,繼續閱讀下篇)
※ 註:荷蘭政府的目標是將現有 1GW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在2030年前提升到11.5GW,比台灣的離岸風電發展目標(2025年達5.5GW)更具野心。
※ 本文原刊於關鍵評論網